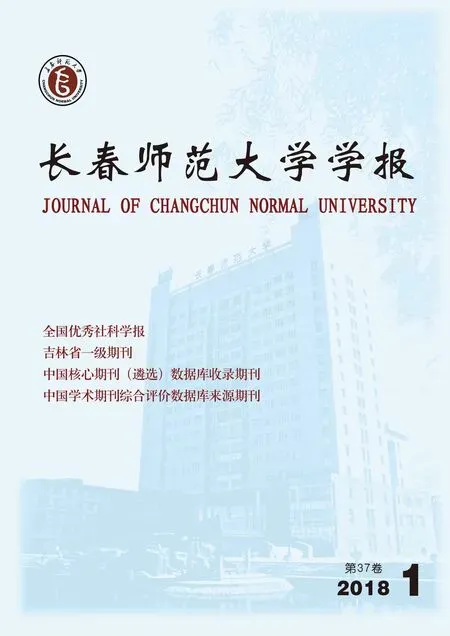葉芝詩歌“Sailing to Byzantium”四個中譯本評析
李國玉
(中山大學新華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東 東莞 523133)
“Sailing to Byzantium”是詩人葉芝晚年所做的一首詩,大概寫于1927年,收在1928年出版的詩集《塔堡》里。它是葉芝最負盛名的長詩之一,也是象征主義的代表作。詩歌借一位老人之口,討論了靈與肉、衰老與青春、生命與死亡、自然與藝術、短暫與永恒等話題。詩中的老人不滿自己所處的國度,因為那里的一切都沉溺在感官的享受之中,忽略了理性的偉大成果,而自己日漸衰老的身體也變得毫無價值,于是決定通過航海駛向想象中的圣地——拜占庭。老人希望能在拜占庭找到教會靈魂歌唱的圣賢,讓他超脫物欲、擺脫肉身的束縛,擁有像藝術品一樣的永恒生命。
“Sailing to Byzantium”自面世以來,就以其嚴整和諧的節奏、意蘊豐富的象征、深刻的主題吸引了很多評論家和翻譯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陸續有一些譯者將該詩譯成漢語,如正式出版了袁可嘉、周英雄、查良錚、裘小龍、余光中、傅浩等所譯的多種版本。其中,流傳較廣的四個譯本分別為查良錚[1]、余光中[2]、袁可嘉[3]和傅浩[4]所譯。本文從詩歌的形式、語言風格和意義三個方面,對這四個譯本加以分析,以期對這首象征主義的經典詩歌有更好的理解。
一、形式
葉芝創作詩歌時,一向講究傳統、典雅的形式。學者對他作品的現代性有很多爭議,但他的詩歌形式遵循傳統卻毋庸置疑。葉芝強調了形式對詩歌的重要性:“一首詩是普通語言的節奏以及節奏和深刻感情結合的精工巧作。像讀散文一樣地讀詩,不習慣詩歌的聽眾也許會覺得容易理解,但這卻讓詩變成了低劣的華麗散文。”他的詩歌形式一向嚴整,“Sailing to Byzantium”這首詩也采用了傳統的詩歌形式。
詩歌原文為形式工整的八行體,一共四節,每節八行,每行大概十個音節,大致組成五步抑揚格。每節的韻式均為ababcc。以第一節為例說明(加黑部分為韻腳):
That is/no coun/try for/old men./Theyoung
In one/ano/ther’s arms,/birds in/thetrees
—Those dy/ingge/nera/tions, —at/theirsong,
The sal/mon-falls,/the mac/kerel-crow/dedseas,
Fish, flesh,/or fowl,/commend/all sum/merlong
Whate/ver is/bego/tten, born,/anddies.
Caught in/that sen/sual mu/sic all/neglect
Monuments of unagingintellect.
四位譯者都注意到了原詩的形式特征,并試圖在譯文中復制。他們的譯文都是四節八行體,并大致遵循ababcc的韻式。其中,余光中和查良錚采取了“以頓代步”的方法來再現原文的節奏,均將原文的五步抑揚格轉化成中文的每行五頓的形式,如余光中譯本的第一節:
那/不是/老人的/國度。/年輕人
在/彼此的/懷抱中;/鳥/在樹上
——那些/將死的/世代——/揚著/歌聲;
鮭/躍于瀑,/鯖/相摩于/海洋;
泳者,/行者,/飛者,/整個夏季/頌揚
誕生,/成長,/而/死去的/眾生。
惑于/感官的/音樂,/全都/無視
紀念/永生的/智慧/而立的/碑石。
袁可嘉和傅浩兩位譯者則放棄了原詩節奏,將詩行譯成了自由體,僅保留了尾韻。
除了以上所說的特征,葉芝在這首詩里還使用了頭韻來增強節奏,比如下面幾行(斜體部分為頭韻):
Fish,flesh,orfowl, commend all summer long
Whatever isbegotten,born, and dies.
Soulclap its hands andsing, and louder sing
For every tatter in its mortal dress,
Nor is theresingingschoolbutstudying
Monumentsof its ownmagnificence;
在四位譯者中,只有余光中在譯文中試圖再現這些音韻效果。他使用相同的或同音的字眼,對應原文的頭韻。如他將押頭韻的“Fish, flesh, or fowl”譯為“泳者,行者,飛者”,將“lords and ladies”譯為“貴族和貴婦”,將“past, or passing, or to come”譯為“已逝的,將逝的,未來的種種”。譯者的這些努力增加了譯文的節奏感和韻律感,跟原文在形式上更加接近。
由此可見,四個譯本中余光中的譯文在形式上與原文最接近,最具有傳統詩歌的節奏和韻律。
二、語言風格
“Sailing to Byzantium”大約作于1927年,屬于葉芝后期的詩作。與早期典雅考究的語言風格不同,葉芝晚期詩歌語言更加簡練平實。他在1912年談到自己的創作時寫道:“首要原則:尋求藝術不是通過語言分析或在夢境之中,而是要過一種有激情的生活,以簡單有節奏的語言表達情感。字詞應當是自然閃現的字詞,暗示著它們從中浮現的環境。”葉芝晚期的創作一直遵循這個原則,有意識地使自己的語言更加簡單、接近自然。“Sailing to Byzantium”這首詩的語言也是這樣的,用詞通俗平實、洗盡鉛華,句法更加接近普通語言。譯文能否再現這種語言風格是評價譯文質量的一個標準。下面試舉幾例來分析四位譯者的譯文是否做到了這一點。
原詩第一節中有一個非常普通的短語“(birds)at their song”,就是一個表示狀態的介賓短語,沒有任何修飾。四位譯者中,余光中將其譯為“揚著歌聲”,多了一個描述動作的“揚”字,或多或少比原文多了一些動感,這是原文所沒有的。查良錚將其譯為“從事他們的歌唱”,袁可嘉譯為“在歌吟”,是比較符合原文簡潔、平實的風格的;傅浩譯為“婉轉放歌”,多了原文所沒有的修飾語“婉轉”和動詞“放”,與原文風格偏離較遠。
原文第一節有“the salmon-falls, the mackerel-crowded seas”這兩個詞組。其中,salmon指的鮭魚,屬于溯河洄游性產卵的魚類,溯河產卵洄游期間,它們越過小瀑布和堤壩,到達產卵場。mackerel指鯖魚,常以族群狀態出現。詩人使用這兩個意象,是為了突出在他離開的那個國度里萬物繁衍的活力,感慨物質世界的繁榮;而精神世界豐富、身體卻很衰弱的老人在那里是“無用”的,以此突出那個國度里精神世界的貧瘠。這兩個詞組非常簡潔,沒有任何多余的形容詞或動詞,但表現力很強。“Salmon-falls”指由鮭魚組成的瀑布,可見鮭魚之多、之活力。“crowded”讓人聯想起鯖魚出沒時成群成窩的繁榮景象。四個譯者中,查良錚的選詞在字面上和內涵上都最接近原文:“魚的瀑布,青花魚充塞的大海”。袁可嘉的譯文“有鮭魚的瀑布,有鯖魚的大海”,加了兩個“有”字,意義差了很遠,表現不出魚的數量和活力。傅浩譯文“鮭魚溯洄的瀑布,鯖魚糜集的海河”雖然意義上跟原文接近,但加了“溯洄”和“糜集”,語言風格就遠了。余光中的譯文“鮭躍于瀑,鯖相摩于海洋”,則帶著譯者再創作的痕跡,在語言風格上與原文相差最遠。
從以上兩例可以看出,余光中使用了詩化的語言,在翻譯過程中進行了創造性的加工。全文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余光中將“aged man”譯為“衰頹的老人”,自行加了“衰頹”二字,而其他三位均譯為簡單的“老人”或“年老的人”;“louder sing”這個簡單的詞組,其他三位譯者相應譯為“唱得更響亮”“大聲唱”“愈唱愈響”,只有余光中譯為更詩化但離原文風格更遠的“俞歌俞激楚”;“out of nature”,其他三位譯者相應譯為“脫離了自然界”“超脫自然”或“超脫凡塵”,而余光中則譯為“蛻化”。
在語言風格上,查良錚、袁可嘉和傅浩三位譯者都注意到原文簡潔、樸實的用詞,并努力在譯文中再現這種風格。余光中對原文進行了再創作,將原本自然質樸的語言風格譯得典雅考究,使譯文風格與原文相差較遠。
三、意義
意義的正確理解對詩歌的翻譯至關重要。詩歌語言通常比較凝練,在選詞和句法上通常與散文語言有一定的差別,如詞義內涵豐富、省略或倒裝較多。“Sailing to Byzantium”這首詩也有這些典型特征。對特殊詞語和句法的分析是正確理解其意義的第一步。下面通過兩個例子來考察四位譯者對原詩意義的理解是否到位。
第二節的一個句子:“Unless/ Soul clap its hands and sing, and louder sing/ For every tatter in its mortal dress”。四位譯者的譯文如下:
查良錚:“除非靈魂拍手作歌,為了它的/皮囊的每個裂綻唱得更響亮”
余光中:“除非/ 靈魂拍掌而歌,俞歌俞激楚,/為了塵衣的每一片破碎”,
袁可嘉:“除非是他那顆靈魂拍手來歌吟,/為人世衣衫的破爛而大唱”,
傅浩:“除非穿著凡胎肉體的靈魂為全部/破衣裳拍手歌唱,愈唱愈響”;
四位譯者對該句中的“mortal dress”的理解分歧較大。結合上文“An aged man is but a paltry thing,/ A tattered coat upon a stick”這一句可知,“mortal dress”延續了上面的比喻,指的是老年人的身體,而“every tatter”則指這具肉身的衰頹老死的種種跡象。余光中將“mortal dress”譯為詩化的“塵衣”,失去了與上文的關聯,比喻意義變得不明確。袁可嘉將其譯為“人世衣衫”,偏離了它本來的意思。傅浩的譯文對整句的結構分析有誤,意義的傳達有重大的失誤。查良錚將“mortal dress”譯為“皮囊”,呼應了前文的比喻,并且特地保留了原文的人稱代詞“its”,保證在意義上與原文高度契合。
再看一例:“Nor is there singing school but studying/ Monuments of its own magnificence”。四個譯本如下:
查良錚:“可是沒有教唱的學校,而只有/研究紀念物上記載的它的輝煌”
余光中:“沒有人能教歌,除了去研讀/為靈魂的宏偉而豎的石碑”
袁可嘉:“世界上沒有什么音樂院校不頌吟/自己的輝煌的里程碑作品”
傅浩:“所有歌詠學校無不研讀/獨具自家輝煌的豐碑樂章”
對“Nor is there singing school but studying the monuments of its own magnificence”這句話,譯者們出現了較大的分歧,對句子結構和“monuments”一詞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解。美國詩人和詩歌評論家Robert Pinsk曾化用這句詩給自己編著的詩歌創作教材取名“Singing School”,解釋這句話暗含的意思稱:“If you want to learn singing, you must study…monumental examples of magnificent singing.”由此可見,該句是一個雙重否定的結構,意義相當于“Every singing school studies the monuments of its own magnificence”,其中monuments應理解為“里程碑史的作品”,而不是“石碑”。從以上譯文可見,查良錚和余光中對這句詩的理解有誤。事實上,兩位譯者的這句譯文本身不太通順,也可佐證該句的理解偏差。
由此可見,對字詞和句法的理解會對意義的傳達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對象征主義的作品來說,意象承載著內涵豐富而深刻的意義。因此,能否準確地再現原文的意象也影響著意義的傳達。
四、結語
四位譯者中,余光中作為擁護中國傳統文化的詩人,對詩歌的形式非常敏感和重視,在翻譯同樣擁護傳統詩歌形式的葉芝的詩歌時,能在形式上做到高度契合。但在詩歌的語言風格和意義的傳達上,余光中加入了太多自己的個人特色,不僅忽略了葉芝后期詩歌通俗簡練的語言風格,而且在意義的傳達上對原文有一些過度引申,因此在風格和意義的傳達上是四位譯者中離原文最遠的。查良錚、袁可嘉、傅浩三位譯者在形式上做得不如余光中那樣完美,但在語言風格和意義上與原文較為接近。其中作為現代主義詩人的查良錚對現代主義的詩歌語言有更高的敏感度,他的譯文雖在意義上有一點小錯誤,但整體而言與原文最為契合。
[1]查良錚.英國現代詩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余光中.英美現代詩選[M].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
[3]袁可嘉.英詩經典名家名譯:葉芝詩選[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
[4]傅浩.葉芝評傳[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