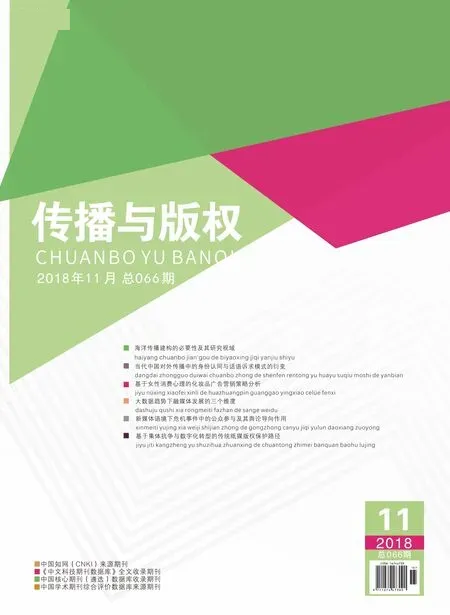從融合出版視角探析跨媒體出版運營策略
——以浙版數媒“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為例
邵凱
移動互聯網隨著數字技術的升級而迅速發展,大眾對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快速從傳統紙質媒體遷移到了數字媒體,從線下環境延伸到了線上空間,這一巨變預示著文化產業不可逆轉的多元化發展趨勢。而出版業作為文化產業的核心組成部分,如何整合自身資源,實現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優勢互補,并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占領文化陣地、履行文化職責,是每個出版人都迫切需要思考與探索的問題。
本文以“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為例,從融合出版的視角探討與分析了跨媒體出版運營的策略及其創新模式。該平臺是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自主研發并運營的出版服務平臺,平臺基于融合出版理念,為作者和內容商提供了涵蓋紙質書、POD短版書、電子書、有聲書等多形態出版物的跨媒體出版服務。
一、“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運營情況
“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是由浙江出版集團數字傳媒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上線的出版服務平臺。浙版數媒通過對傳統出版模式的重塑以及新興數字技術的應用,對內將該平臺打造成面向出版社的全流程在線出版業務系統,對外將其構建為面向作者和內容商的跨媒體出版服務平臺,以建立適應于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型出版模式。
浙版數媒在平臺運營過程中始終堅持融合出版的理念,創建了跨媒體出版服務模式。該模式在版權資源方面,兼顧個人作者、出版社、圖書工作室、版權代理機構等不同內容源;在出版物類型方面,支持紙質書、POD短版書、電子書、有聲書等不同類型出版物;在銷售渠道方面,打通傳統書店、線上網店、主流海外平臺等多種銷售渠道。在上述模式運作的基礎上,平臺還構筑了全流程數字化管理與采編審體系、全格式出版物制作與封裝體系、全渠道作品發布與營銷體系以及全平臺銷售數據統計與結算體系,實現了一站式作品投送、簽約、編輯、審核、制作、發布與結算等功能,真正建立了一個跨越多種媒體的在線出版社。
截至2017年12月,“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已入駐作者和內容商500余家,包括一線作者、圖書出版社、期刊出版社、圖書工作室及國內外版權代理機構;出版作品3900余個品種,除國內以外,部分作品還在全球51個國家銷售,作品累計購買量達3165萬余次,并處于逐年上升的趨勢。平臺榮獲由浙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頒發的2017年浙江省數字出版網絡視聽新媒體創新大賽“行業創新二等獎”、小米閱讀頒發的“戰略合作伙伴獎”、亞馬遜Kindle中國頒發的“kindle先鋒獎”及美國OverDrive頒發的“藍天獎”。
二、“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運營策略探析
“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是國內少有的以國有出版單位為依托的互聯網出版平臺。除運用最新的數字技術以使其符合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方向外,基于融合出版思維的運營策略是該平臺運營成功的重要原因。浙版數媒在運營過程中,采用資源融合、流程融合、數據融合、服務融合等策略,探索互聯網時代跨媒體出版服務模式。
(一)深度融合出版資源
數字出版的發展離不開傳統出版資源,無論是圖書資源、作者資源還是渠道資源都是開展跨媒體出版業務的基礎。以圖書資源為例,浙版數媒在平臺研發初期就認識到其重要性,通過開發核心出版資源庫、組建數字化加工團隊等形式逐漸梳理并整合歷史書目,為跨媒體出版業務的開展奠定了資源基礎。核心出版資源庫目前收錄了浙江出版聯合集團1950年至今的存量圖書資源,并持續更新每年的新書品種。作為跨媒體出版的基本策略,出版資源的整合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首先,圖書進行數字化整理入庫后,具有數字版權的品種可優先進行出版與運營;其次,作者資源作為無形資產,對其的整理工作很大程度上能使后期優質選題的開發受益;最后,對渠道資源的整合是開展多渠道出版物運營的重要前提,也是后期結算的關鍵依據。在完成上述工作后,紙媒與數媒資源將在出版單位內實現共享,平臺初期出版資源匱乏的問題將有效得以解決。
(二)巧妙融合出版流程
在數字出版的流程構建方面,通常會聯想到要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出版體系。這一策略確實能夠創建出適用于數媒的業務流程,然而由于該體系與紙媒出版的交匯點甚少,最終會造成多種問題。譬如,在圖書加工環節,由于傳統出版印前工序所產生的數字文件無法直接轉換成電子書,數字出版物加工人員需根據主流電子書標準,如EPUB標準[1]來重新進行排版與編校;在版權運營環節,數字出版物運營人員因不了解選題的版權狀況,進而需向紙書版權簽約部門追溯,數字出版物的數字版權亟須進行管理[2]。上述情況無形中增加了業務鏈的長度,降低了出版效率,影響了出版質量。為此,浙版數媒改變策略,巧妙地從流程升級的角度出發,在傳統出版的編校、加工、版權運營、銷售結算等環節為數字出版預留業務接口,既保證傳統業務線不受影響,又能確保每個環節均能最大限度與數字出版進行銜接。平臺構筑的全格式出版物制作與封裝體系優化了圖書加工流程,使作品終稿能同時生成符合紙書印刷要求與數字出版要求的電子文件,顯著減少了工序冗余與人工工作量。同時,平臺構筑的全流程數字化管理與采編審體系建立了集團內跨社信息互通機制,通過平臺出版的作品,其選題、版權、銷售等業務信息能準確反饋到相關業務部門,為同一作品的跨媒體出版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適時融合出版數據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最大特征就是大數據的產生,對大數據的管理和分析必將對各個行業產生深遠影響[3],而運用出版大數據來指導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則是跨媒體出版運營的基本方式。然而在此之前,一個相對重要的策略就是盡快積累并整合出版數據。目前,國內絕大部分出版單位已擁有服務于紙書出版的信息系統,并積累了編務、發行等數據。相對于紙媒出版,數字出版業務現階段并無成熟的信息系統可供出版單位選擇,導致其在開展數字出版業務過程中缺乏平臺支持與數據積累。例如,某一作品在收益統計環節,紙書銷售數據能夠通過信息系統導出,而電子書的銷售數據卻因各渠道的結算周期、報表形式、分成模式等差異,往往無法得出明細報表,為其業績評估與結算帶來了影響。針對上述問題,浙版數媒在平臺研發階段采用出版數據追蹤與整合技術,構筑了全平臺銷售數據統計與結算體系,實現了多渠道出版數據的標準化采集與整合,保證了后期跨媒體出版業務的順利開展。平臺上線至今,除傳統紙書出版數據外,平臺存儲的數字出版數據覆蓋了國內22個主流銷售渠道及國外51個國家。在此基礎上,運營人員可全面了解每個作品在各渠道的銷售情況,并及時開展“紙轉電”“電轉紙”及“紙電同步”[4]等跨媒體出版業務;每個與平臺簽約的作者與內容商可定期查詢其授權作品在各渠道的銷售業績、渠道名稱、銷售時間、購買量、定價、分成比例、銷售收益、結算賬期等詳細信息均可通過平臺進行自主查詢。出版數據的融合一方面為出版工作者提供了大數據參考體系,為其運營工作提供了數據支撐,另一方面通過透明化的出版數據拉近了出版社與作者和內容商的距離,讓其收益有據可尋,亦提高了其對未來出版合作的積極性。
(四)全面融合出版服務
出版工作的服務對象是作者和內容商,如何留住內容方,盡可能使優質IP資源匯入出版單位,是出版服務層面需要探討的問題。除分成比例外,集成化的出版服務是吸引作者和內容商的重要因素,是跨媒體出版的關鍵策略。該類出版服務的提供不僅可為內容方節省出版時間,也極大地降低了出版成本,從而收到單次投入、跨媒體出版、多渠道收益的效果。浙版數媒通過技術優化構筑了全渠道作品發布與營銷體系,為內容方提供一站式紙質書、POD短版書、電子書及有聲書等出版服務,在大幅縮短出版周期、降低出版成本的基礎上,給予內容方更為便捷的出版通道與更高的出版回報。
三、“BookDNA”出版服務平臺運營的重要啟示
(一)出版服務的平臺化是出版行業的發展方向
數字出版產業在國內興起初期,一些出版單位嘗試以內容銷售商的角色自建銷售平臺來開展出版業務。然而,由于自建的銷售平臺在知名度、產品品種、用戶體驗等方面遠不及互聯網技術商運營的銷售平臺,導致用戶逐漸轉向內容更為豐富、體驗更為優質的第三方渠道。2012年12月亞馬遜Kindle Store在中國悄然上線[5],國內主流互聯網技術商亦紛紛建設了數字內容銷售平臺,標志著以互聯網技術商為主導的數字內容銷售體系基本形成。在這樣的格局下,現階段出版單位因主動改變策略,抓住出版服務類平臺稀缺的機遇,將出版服務的平臺化建設放在移動互聯網出版戰略的重要位置,以出版服務提供商來定位自己,并通過前端對接作者資源,后端對接主流銷售渠道的方式來運營出版產品。
(二)融合出版的落實與應用是跨媒體出版的客觀要求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每個行業都面臨著新舊業務模式的整合問題,出版行業也不例外。“BookDNA”在建設過程中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從資源、流程、數據、服務等方面開展融合出版的落實工作,建立了連接紙媒與數媒的橋梁,并以在線出版平臺的方式加以具體應用。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融合不僅僅是新舊業務模式的優勢互補,它還帶來了作者和內容商的集合、現有出版產品線的整合以及出版大數據的聚合,所有這些都為跨媒體出版業務的開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新興數字技術的運用是融合出版的強大動力
在宏觀層面,融合出版是兩種出版模式的結合,而在微觀層面,融合出版工作的推動與開展要求出版單位能夠在生產工具、生產行為及生產模式等方面進行優化與升級。這就必須依托最新的數字技術來梳理并構建合理的軟硬件環境,從而打破現有的壁壘,建立相應的互通機制,讓數據流、業務流、信息流能夠在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之間流動起來,形成與移動互聯網生態環境相契合的業務體系。因此,培養與建設核心技術團隊、掌握核心自研技術、把握最新技術動態是長期且不容忽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