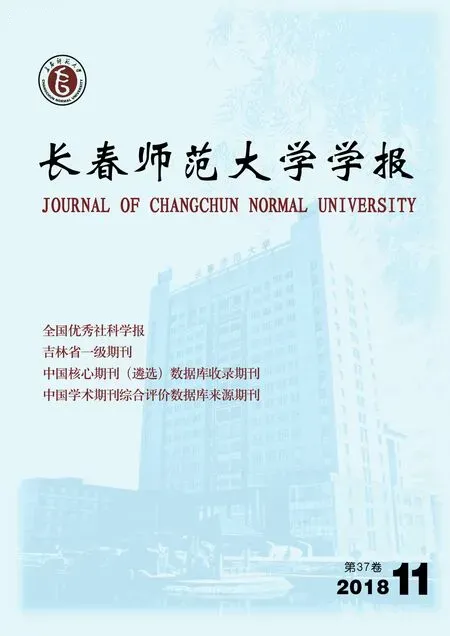從語言順應論看《生死疲勞》的翻譯
申 丹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 天河學院,廣東 廣州 510540)
順應論從認知、社會和文化的綜合功能視角描述和闡釋了人類使用語言的各種現象和語言運用的實質,該理論被視為“一個非常具有解釋力和應用價值和發展前途的語用學理論”[1],為語用學和翻譯學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用于文學翻譯的分析和研究中,順應論的核心“順應性”強調翻譯是對源語語境和語言結構作出動態順應的過程,這表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忠實于原文,但在具體的翻譯策略和技巧選擇上也是可以靈活處置的。
一、順應論簡介
維索爾倫(Verschueren)于1987首次提出語言順應理論,并于1999進一步完善該理論。他創造性地結合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和語言的實際應用,以一種新的視角來考察語言的使用。他認為語言使用是其使用者在語言的結構層面和策略層面不斷作出選擇以達到交際目的的過程,選擇過程是語境與語言相互適應的動態過程。在Verschueren的理論中,“變異性、協商性和適應性”[2]是層次相關的關鍵概念,這是研究或理解語言選擇過程的需要。變異性是語言的屬性,確定了作出選擇的可能性范圍。適應性是語言的一種特性,使人類能夠從各種可能性中作出可協商的語言選擇,從而達到滿足交際需要的目的。從語用角度看,順應性可以從語境關系順應、結構客體順應、順應的動態性、順應過程的意識突顯性四個角度來研究來,選擇是手段,順應是目的,二者形成一種辯證關系。
二、順應論在《生死疲勞》中的應用
《生死疲勞》(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是莫言于2005年創作的文學作品,其英文版于2008年出版。在該小說中,莫言站在新歷史主義的角度去解構過去的現實主義,借鑒古典小說和民間傳統敘事方法,使小說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小說中話語直接引用的表達方式、隱喻的修辭手法和大量文化負載詞的使用也體現了這部作品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葛浩文(Goldblatt)對莫言小說的英譯,無疑為莫言及其作品獲得國際聲譽及至諾貝爾文學獎做出了不菲的貢獻。本文擬從“語境關系順應”“結構客體順應”“順應的動態性”“順應過程的意識突顯”這四個方面來分析《生死疲勞》英譯本中的翻譯現象,以探討該理論對文學翻譯的闡釋力和可行性。
(一)語境關系順應
Verschueren(1999)認為語境包括交際語境和語言語境,交際語境包括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語言語境即上下文。語境關系順應指翻譯過程中的語言選擇必須要聯系語境,做到語言順應,忠實貼切地傳達源語意思[2]。比如文中通過歸化策略將“妾”翻譯成“concubine”,使目標語讀者在其自身社會語境中就能理解人物之間的社交關系,并體會小說中人物的心酸感受。
在另一段迎春和洪泰岳之間的對話中,迎春最開始從年齡的角度稱洪為“洪大哥”,但洪對這個稱謂很生氣,認為地位比他低的人一定要叫他的官名,才能顯示自己的威望。于是,迎春立即改口稱他為“書記、村長、公安員”,以示對其尊重。葛浩文在翻譯中相應地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將這些官名如實翻譯成“Party secretary, village chief, security officer”,以顯示源語語境中人們對社會階級的關注和社交關系中人物地位的差異性,以達到交際的目的。
要實現語言語境順應,就必須通過文本中連詞、前指、互指、省略、數目、標識、重復、代替和結構相似等方式來考察語篇上下文的語義相關。如“護身符”一詞,譯者就結合了上下文的語境,直接翻譯成了“the letter”,說明這封信是縣長給藍臉要求單干所批寫的一封信。此外,第十五章西門金龍為勸藍解放入社時所說的話:
一字一頓地說:“你入社不入社?!”
“不……我不入……”[5]
首先,作為國有企業開展好思想政治工作能夠對企業發展起到良好的引領作用,使企業員工具有明確的努力方向和意義,能夠有效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創造力,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能推動企業發展。其次,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員工在思想覺悟水平上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1]。因此,通過開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從整體上提高員工整體素質與職業水平,推動物質生產與精神文明實現共同進步。最后,國有企業開展好思想政治工作,將國家黨政方針和企業文化等不斷向員工進行宣傳,使廣大干部員工增加改革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促進國有企業創新發展。
“Are—you—going—to—join—or—aren’t—you?”
“No…never join…”[6]
葛浩文通過增加破折號把這個句子的每個詞間斷,以體現出西門金龍咬牙切齒、一字一頓的說話語氣,十分生動,完全達到了語言語境的順應。
(二)結構客體順應
結構客體順應是譯者對語言各個層面如詞匯、句法和語篇的結構和建構做出選擇,以適應譯語讀者的思維層面[7]。在宏觀上要順應不同文化的社會政治制度、歷史淵源、經濟體制、時代背景、地理環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等。如原文本當中提到的“大躍進”“三面紅旗”“紅衛兵”“文革”“四清運動”“入社”等詞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政治經濟背景,葛浩文按照字面意思分別翻譯為“the Great Leap”“the Three Red Banners”“Red Guards”“Cultural Revolution”“Four Clean-ups campaign”“join a commune”。這些詞看似達到了詞匯層面的順應,但由于具有特定的內涵,如果采用加注的方式予以解釋,將更有利于目標語讀者的理解,實現語義上的順應。另一組例子剛好與此相反,譯者采用意譯的方法達到了譯文語言結構順應。如第十八章中關于楊七販賣皮衣的描寫:
楊七獐頭鼠目,眼珠子骨碌碌亂轉……
楊七巧舌如簧……[5]
Yang Qi, a repulsively ugly man with shifty eyes……
Smooth-tongued Yang Qi……[6]
“獐頭鼠目”和“巧舌如簧”是漢語成語,通過比喻的修辭手法用具體的形象來描繪楊七的特征。譯文中采用意譯的方法,在詞匯層面雖不對應,但勝在簡明清楚,實現了譯文對目標語讀者在思維和文化層面的順應。
在微觀層面上,語言結構應與語言選擇、代碼選擇、風格選擇和話語結構選擇相適應。如《生死疲勞》中每章的標題都模仿了章回體小說目錄的形式和風格,字數相同,結構相似,對仗工整,既概括了每一章的主要情節,又彰顯了語言的形式美。葛浩文在翻譯時采用直譯的方式,盡可能保留了標題的語言結構和風格,如將第十八章目錄“藍解放叛爹入社,西門牛殺身成仁”[5]翻譯成“Lan Jiefang Betrays Father and Joins the Commune, Ximen Ox Kills a Man and Dies a Righteous Death”[6],原標題主語分別是藍解放和西門牛,叛爹和入社、殺身和成仁為二組并列的動賓結構,譯文中用“and”分別連接了“betrays father”和“joins the commune”、“kills a man”和“dies a righteous death”,英漢句在意義和形式上都實現了語言結構的順應。
句法層面的順應主要體現在對英漢二種語言句法結構的轉換上。漢語是意合型語言,英語是形合型語言。因此,譯者必須順應譯語的語言特點、表達習慣和語法規約,采用諸如增譯、詞性轉換、正否句反譯、被動/主動句變化等方法來實現順應。
語篇結構層面的順應主要側重于句子的組織、語篇的銜接和連貫以及對信息結構、句子順序和語篇類型等的選擇,譯者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譯文的語篇模式、合理安排語篇結構。在譯本中,葛浩文模仿了原文本的章回體語篇寫作方法,基本保存了原文本的語言和文體風格。但在某些句段的具體處理上,則采用了刪減的手法。如第三十三章,從西門豬在“圍觀電視的人群后待了約十分鐘時間”[5]這一段開始,譯者在翻譯時直接省譯了六段半,但由于省譯部分剛好是西門豬的回憶片段,因此即便刪減了,也并沒有影響譯文語篇的整體銜接和連貫,也基本不影響譯語讀者的理解。
(三)順應的動態性
動態順應是順應論的核心,強調譯者對譯文語言的選擇要動態地順應,反映交際原則和策略在選擇和協商中的運用,達到“信達切”的翻譯標準。
既要應付游擊隊,又要應付黃皮子。[5]
I had to taken over the guerrillas and the puppet soldiers.[6]
上例中,“黃皮子”在原文語境中指偽軍,翻譯時用借用了英語中慣用的詞語“puppet soldiers”來翻譯,達到了文化層面的順應。另外,文中對“活寶”一詞的翻譯,其字面意思是指活的生物,常用來表示逗趣、令人開心的人。該詞最初是一個貶義詞,現在既可指貶義也可指褒義。“cutup”主要用于美國的口語,指喜歡炫耀或滑稽、幽默的人,可做中性詞。此句中用“cutup”翻譯“活寶”,實現了文化等值。此外,譯文中對“赤貧農”的翻譯也很有特色。葛浩文巧妙地順應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將其直譯成“redder-than-red poor peasant”。“紅色”在這里不僅是一種顏色的表現,也是革命的象征。這一改編適時地再現了土地改革時期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這三個譯例不執著于原文,采用了動態靈活的翻譯方法,不單達到了詞匯順應,也實現了文化順應。
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還采用省譯的方法來實現譯文的動態順應。詞匯上的省譯,如“斗大的福字”里省譯“斗大的”,“瓜蔓親戚”里省譯“瓜蔓”等;句子層面的省譯,如第三章的俚語“螃蟹過河隨大溜”、“識時務者為俊杰”,第十四章的“博山的瓷盆——成套成套的”;段落層面的省譯,如第十三章的順口溜前半部分“單干是座獨木橋……拔掉窮根栽富苗”,第十六章中墻頭小孩唱的歌謠“藍臉大,藍臉小……”等,這種省譯并沒有過多地影響譯語讀者的閱讀和理解,是譯者為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和目標語讀者的可接受性而作出的選擇。但是,對于原著而言,這種順應讀者的省譯不可避免地有損原文的內容和風采。
(四)順應過程的意識突顯
在順應論中,“突顯”的概念被許多翻譯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闡釋。突顯是語言使用的一種特征,但其本質上是一種功能,是對語言使用所涉及的意識的操作。如:
他是我從關帝廟前雪地里撿回來的孩子。[5]
He was an orphan I would found in the snow in front of the God of War Temple and brought home with me.[6]
在漢語文化中,“關帝”即關羽,通常被看作忠誠的化身,成為忠、信、仁、智、勇的象征。中國讀者熟悉關羽,而目標語讀者可能對關羽一無所知。因此,Howard將“關帝廟”巧妙地翻譯成“the God of War Temple”,使西方讀者能夠對“關帝”這個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意象和精神產生更加直觀的聯想和理解,充分體現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實現文化順應的意識。
三、結語
通過從順應論視角對《生死疲勞》譯本的分析,可以得知翻譯過程中的順應是多層次、多角度的。譯者作為連接源語和目的語的橋梁,要保證譯文對原文的忠實性和對讀者的可接受性。譯者必須靈活運用各種翻譯策略,具備較強的跨文化意識,使譯文在語言結構和語境上實現動態的順應。
ABriefAnalysisontheTranslationof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intermsofAdaptationTheory
SHEN Dan
(Tianhe College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540, China)
Abstract: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is one of Mo Yan’s representative works, its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Mr. Howard Goldblatt extends global fame of the original works and its author, and also sheds huge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s popularity also indicates the language choice and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have adapted to the target readers’ need and target culture, on which Adaptation Theory focu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rete operation of linguistic choices and dynamic adap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by series of exam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dynamics of adaptability and the salience of adaptation process.
Keywords: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 Adaptation Theory; linguistic choices; dynamic adap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