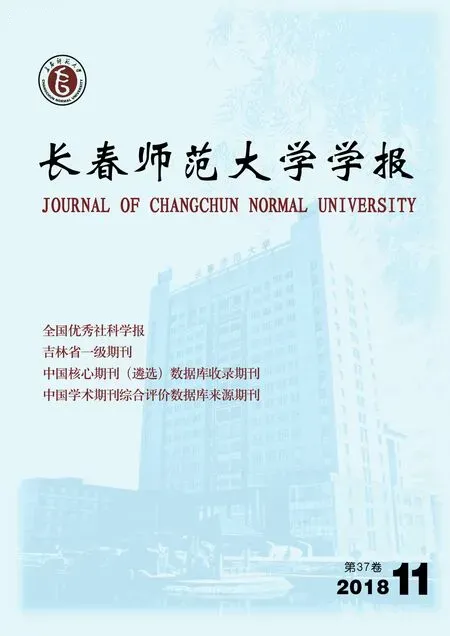五四時期白話與文言的話語轉向
李宗雙
(通化師范學院,吉林 通化 134000)
五四文學革命中,文言向白話的話語轉向,蘊含著服務于社會、時代的歷史背景。欲了解這種變化與轉向,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在于厘清文言與白話的源流及關系。五四時期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其蘊含的內容是多面的:傳統與現代的論爭,古體與今體的變革,時代與歷史的發展,文言與白話的轉向。其中文言向白話的話語轉向,是語言自身話語方式的變革。文學話語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會呈現出一定的不同步性。這種不同步性既體現在文言向白話的過渡當中,又外化為啟蒙者與反對派的論爭。反對派有以林紓為代表的守舊派,也有以梅光迪、胡先骕、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更有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其中反對派與學衡派的論爭最值一提。學衡派的代表人物都曾留學歐美,學貫中西,在論爭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對白話文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一、文言與白話的淵源及其關系
談及20世紀的中國文學,首先要對文白之間的淵源及關系進行梳理。1915年胡適在美留學時,便已主張使用白話文。隨后,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發表《文學革命論》,正式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大幕。文言與白話的論爭是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尤其是應資產階級的變法運動而生的。雖然我們不能將20世紀的中國文學簡單地理解為“活白話”與“死文言”這兩種文學話語方式的交鋒,但在五四文學革命背景下,這種交鋒代表著時代的變革、權利的轉向。其中文白的交互關系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文言文在中國文學中有根深蒂固的物質基礎,存在一定的相對性。一方面,文言文對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有重要的傳播作用;另一方面,文言文為文言向白話的過渡提供了現實可能。舉一簡單例子,在白話文運動中無論是梁啟超、陳獨秀還是胡適,皆具有深厚的文言功底,因而他們能站在比較高的起點上審視文言本身的不足與缺陷。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文言與白話的交鋒,不僅體現了文學話語自身的變化,更是一種可以折射時代變化的價值轉向。正是文言自身的變革與優化,才能為白話文的發展創造先決條件。“死文言”雖陳腐,卻是“活白話”發展的重要基礎。白話文在此基礎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得以登上歷史舞臺。這既是一種時代的巧合,更有其內在規律,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二者是一種互相補充、推陳出新的關系。
其二,文言與白話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融合與創新。與文言相比,白話文與時代的變革有更為密切的聯系。一是白話文繼承了文言中的妙用之法,循理而舉事。二是白話文打破了八股文的固定模式,更具創造性。只有明確二者的淵源,才能于用中見體,獲得新的變革與發展。當然,這既需要通暢豁達的繼承,又需要簡潔明了的創造。這既是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濫觴于世的原因,更是二者關系的微妙之處。
其三,文學話語的轉向是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因而在“死文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活白話”更具社會化價值。在五四文學革命中,文言與白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轉化,當然這種轉化是建立在二者漸趨融合而白話已然成為話語主流基礎之上的。對于20世紀初文言與白話的內在轉化,我們不能僅將其理解為文言與白話的相互雜糅。它既是一種生不離死、于死中見活的話語轉向,更是一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內在變革。所以,對“活白話”與“死文言”內在關系的考量,既表現為文言與白話發展的內在張力,又內化為文白變革的根本動力。
二、“活白話”取代“死文言”的原因
白話文成為當代中國文學中的主流話語,與晚清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體運動有必然聯系。我們不妨拋開時代和政治因素不談,單從文學革新與語言發展的角度分析為什么白話文能取代文言文。
在五四文學革命前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早期文學革命家就在晚清白話文報刊上開始了這種實踐。據史料記載,晚清以來直到1918年,各地創辦的白話報刊多達170余種,較有影響的有《演義白話報》《平湖白話報》《無錫白話報》《通俗報》《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等,其中以陳獨秀創辦的《安徽俗話報》最具代表性。梁啟超等人最先提出“新文體”寫作,他的《少年中國說》雖然被人認為是“近代文言散文”,但這種新文體在當時已經起到啟蒙大眾的作用。無論是晚清文人的倡導還是白話期刊的創辦,對白話文的發展都起到了促進作用,使白話取代文言成為必然趨勢。
五四文學革命中期,陳獨秀、胡適等人又將通俗易懂的白話文與固步自封的文言文相互對照,彰顯出白話文內在的發展活力。當然這并非對傳統文言的全盤否定,白話文發展本身也沒有盡棄文言文的優勢。白話文是啟蒙思想、教化民眾的工具,追求的是語言的革新與文學觀念的轉變。從文學革新角度看,傳統的文言文缺乏創新精神,而白話文除卻宣傳作用外更有利于展現復雜的社會生活與豐富的人文情感。白話文通俗易懂,貼近生活實際,抒情敘事自然貼切,相較于文言文受到的束縛更小。
從中國語言發展角度來看,文言文日趨僵化、保守,個別字句紛繁復雜,不易理解,傳承下去存在一定困難。雖然晚清文言文逐漸過渡到新文體,但也難以跟上語言發展的實際步伐。語言本身是一種交流工具,它每時每刻都需要填充與創新,因而適應這一需要的白話文應運而生。它既可啟迪民智,又可傳承語言,具有很好的情感表達作用。可以說,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在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三、對“死文言”與“活白話”的現實考量
文言與白話固然有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但骨子里也有一種相生相克的弊端。文言與白話的矛盾關系在五四前后的文學革命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隨著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深入,文言與白話已然形成對立趨勢,即文言的發展已無力回天,而白話的發展蒸蒸日上,這是文言與白話在發展形勢方面的對立。同時,它們在敘事方面存在對立。文言在變革前擁有自己獨特的話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壓抑了人們的現代性需求。
白話想要發展,就必須擺脫“死文言”的束縛。在五四文學中,“死”不再是人生最大的恐懼。魯迅先生主張藐視茍活的古訓,認為茍活是人們恐懼并極力淡化死的一種自我意識。五四時期,作家開始在新的層面上對白話文進行肯定。當然,這種肯定是雙面的:一方面,文言的“死”代表了一種歷史的終結,是任何人也無法超越或否定的客觀現實;另一方面,對白話而言,是一種“循理而舉世,因資而立權”的引導。文言的“死”,迫使白話文盡可能地以有限的發展空間創造無限的文學價值。“死文言”本身是與白話文相對存在的,任何外來的推力都取決于其內在的現實需求,更來自時代發展的客觀趨勢。“死而后生”是這代人身上所具有的共同品質,也是時代賦予他們的重要使命。
四、結語
文言的積淀與整合使白話文有了新的發展空間。二者相輔相成、相生相克的辯證聯系促進了中國近代白話文學話語方式的形成。二者既融合又創造,在五四文學浪潮中進化演變,成為文學革命中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