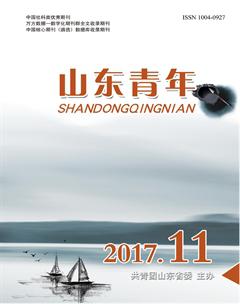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分析
尹衛兵
摘 要:公共外交在上世紀60年代興起以后,媒體在外交中的角色日漸凸顯。隨著社交網絡技術的普及,世界各國進入社交媒體社會。社交媒體成為影響全球政治的重要推力,它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共外交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它的行為主體、過程和目的都跟傳統外交有了較大的區別,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也隨之改變。
關鍵詞:社交媒體;公共外交媒體;外交社交網絡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全球社交媒體高速發展,臉書等社交媒體平臺在一國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與傳統媒體相比,社交媒體具有及時、互動、開放、溝通高效等優勢,如何使其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的公共外交戰略,構建和提升國家形象,成為中國外交界和媒體界探索和實踐的重要課題。媒體在公共外交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在社交媒體時代,公共外交有什么樣的新特點?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是什么?本文將一一剖析以上問題,為國內媒體運用社交平臺提升國際傳播能力、進行公共外交提供決策參考。
一、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一般認為,公共外交作為國際關系領域中一個有特定含義的術語,其首次出現是在1965年的美國。1965年,塔夫斯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院長埃德蒙·古利恩提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公共外交”概念,將其定義為“一個政府在其他國家境內培植輿論、該國國內的利益團體與另一國利益團體在政府體制以外的相互影響、外交官和媒體記者之間的溝通聯系,以及通過這種過程對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務處理造成影響的活動。”[1]古利恩對公共外交的界定比較寬泛,泛指一國政府對另一國公眾的外交。此后,美國學術界掀起了研究公共外交的熱潮,出現了多種多樣的解讀。但各種解讀及概念演變都沒有離開以下幾個基本要素,即公共外交必須是一國政府或其支持的行為體主導的外交活動,它的對象是其他國家的公眾,以大眾傳媒為主要手段,目的是贏得他國公眾對該國的認同、支持甚至喜歡,從而推進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和不同文化間的理解交流。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各種傳播技術的普及,媒體與國際政治的互動越來越頻繁。傳播學和公共外交學中常引用的一個例子是“CNN效應”。從1990年的海灣戰爭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對戰爭的現場直播以及外交和軍事權威人士的分析比各國正式的外交與情報管道都更為迅速翔實,連美國總統和中東國家領導人都通過CNN 向對方傳達信息、了解戰況。CNN 成為重大事件的報道者和外交活動的重要通道,各國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也開始更加重視媒體外交的重要性。冷戰結束以后,媒體與外交的聯系互動更為頻繁密切。“媒體外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研究。某種程度上,這要歸因于公共外交在全球范圍的崛起。媒體外交被視為公共外交的一種實現形式和組成部分。”[2]公共外交是指政府或有政府支持的行為體與其他國家公眾的外交活動,媒體外交則是指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行為體通過大眾傳媒與其他國家公眾的外交活動。媒體是公共外交目標實現的主要介質和工具,一國公共外交政策實施往往要依賴媒體發揮的積極作用。“國際傳播是公共外交的核心載體,是決定公共外交成敗的重要因素。沒有傳播,就沒有公共外交。”[3]
進入新世紀以后,社交媒體的興起給公共外交帶來了更大的施展空間。公共外交強調公開透明、平等交流和開放包容,社交媒體打造的自由、互動和去中心化平臺正好契合了公共外交的上述特性。美國總統特朗普是位名副其實的“推特總統”,作為“推特控”的他憑借社交媒體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截至2017年11月底,特朗普的推特粉絲數量超過4200萬,位居該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第21位。特朗普依靠社交媒體贏得大選,還在大選后開展讓他毀譽參半的“推特治國”,通過推特來向外傳遞信息。“當選美國總統以后,特朗普更是推行‘推特治國,通過推特指點江山,發表有關內閣人事、商業活動、貿易外交等方面的信息、看法。在轉發量超過1萬的316條樣本中,外交相關議題56條,占比約17.7%。”[4]社交媒體并不是國家間交往的正式官方平臺,但是卻可以便捷的向全球傳遞特朗普本人的想法,它還可以為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投石問路。在一些重大且敏感的外交議題上,特朗普往往一反常態,不是先通過秘密外交或者職業外交來解決問題,而是一開始就捅到社交媒體上去,然后通過推特評論和輿論反饋來掌握民意和各方態度,為接下來的政策調整、政府間談判交易鋪路搭橋。
二、社交媒體時代公共外交的特點
國際電信聯盟發布調查報告稱,截至2016 年底,全球網民總數約為35 億,占全球人數的47%。截至2017年6月,社交媒體平臺臉書的全球月活用戶數達20億,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體量,較互聯網使用人數的一半還多。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截至2017年8月,有67%的18歲以上美國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一些新聞。社交媒體不但提高了普通公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熱情,也為外交的廣泛開展提供了動力和便捷的通道,公共外交也因此呈現出了新的特點。
1、非國家行為體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增強
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機構在信息采集、信息發布和信息審查等環節具有權威壟斷性,普通公眾等非國家行為體往往只能以面對面的人際傳播方式來開展公共外交,受時空制約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其參與人數、交往規模與頻度、持續時間等存在一定的局限。而社交媒體大大提升了非國家行為體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公眾在信息發布、議程設置和政策影響力方面的作用日漸凸顯,越來越多的個人、企業、公司和民間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借助輿論杠桿而成為外交的實踐者和親歷者。在此背景下,各國爭相重視和發展社交媒體公共外交。
2010年12月中旬,突尼斯街頭一次城管暴力執法引發的自焚事件迅速席卷中東北非地區,這場媒體所說的“阿拉伯之春”導致該地區局勢突變,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也門總統薩利赫相繼被流放、下臺受審或被擊斃。在很多學者看來,這是一場由美國國務院和中情局操盤的“社交媒體革命”。抗議期間,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平臺成為了美國使館工作人員與抗議者之間溝通過的工具,那些被認為是“烏合之眾”的底層民眾被這些社交媒體組織起來,短時間內就獲得了抗衡政府、甚至是讓政府倒臺的巨大力量。這場“社交媒體革命”讓全世界瞠目結舌,非國家行為體在社交媒體助力下的巨大威力也讓各國政府不得不重視。
2、公共外交從獨白式“喊話”到注重雙向交流
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和他國公眾進行有效溝通,影響公眾的態度,從而塑造本國良好的國家形象,推進外交政策的實現。“學術界和實踐者達成了共識,即向民眾‘喊話會制造敵意,傾聽并與民眾交流在道德上更受推崇且在政治上更加有效”。[5]單向信息傳遞很難改變公眾既有的成見和刻板印象,而傾聽并與公眾交流能夠更高效地接近外國公眾,這樣的外交政策也會更有效。在社交媒體時代,公共外交已經日漸成為雙向交流、而非單向度的傳播。傾聽和交流在公共外交中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傾聽和交流意味著對于目標國家公眾主要觀點的接納和分析,也可以通過創造環境、道德、法律問題等極具合作空間的公眾議題來實現。
在美國公共外交史上, CNN和美國之音等媒體扮演過重要的“傳聲筒”角色, 但是現在社交媒體開始取而代之,逐漸成為美國政府與外國公眾溝通、贏取“民心”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吸取了之前重意識形態、輕對話合作的教訓之后,美國公共外交逐漸轉向雙向對話。美國奧巴馬政府非常重視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2009年5月,白宮開始在臉書、推特等主流社交媒體網站上開設賬號和主頁供全球公眾瀏覽獲取信息。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更是將“推特外交”發揮到了極致。2017年11月訪華前后,特朗普共就自己的“中國行”發出8條“推特”,并更換了兩次封面。這些推文中包含來訪前的期待,有對中國盛情接待的感謝,也有對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的積極評價。在經過中國主流媒體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轉載以后,特朗普這些與中國行有關的推文迅速拉近了與中國公眾的距離,并引發大的反響,是一次較為成功的社交媒體公共外交。
3、外交的目的不再過分利益化
傳統媒體時代,現實主義學者僅僅把公共外交看作鞏固權力政治的補充,認為外交追求實現國家利益和執行外交政策的單一目的。但在社交媒體時代,公共外交更側重于溝通情感、打破文化隔閡、塑造認同。政府通過社交媒體提供關于外交活動的真實情況,與他國公眾進行真誠溝通互動,以信息互換和平等交流的姿態贏得國際公眾的“民心”,因此社交媒體時代的外交更側重于在國家利益之外贏得情感和政治認同。學者趙可金曾指出:“在價值原則上,將從強調單一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導向轉化為網絡外交兼顧多元社會利益與人類共同利益導向并重。外交越來越借助網絡世界的一體化而變得日益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人類共同利益至上的價值原則必將得到弘揚。”[6]比如說,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提出的“地球一小時”接力,為表達對恐怖主義的憤慨而發起的“我是查理”運動,為揭發反對性騷擾的“我也是”運動,社交媒體在推動解決全球性難題的解決、促進人類共同發展上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
過去十幾年里,全球社交網絡全面崛起,并日益取代傳統媒體成為新聞傳播和信息溝通的主渠道,利用社交媒體來開展公共外交已成為各國通用的做法。和以往相比,外交活動呈現出了很多新特點,這些新特點也使得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概括而言,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如下:
1、從精英的傳聲筒到公眾的輿論場
傳統媒體時代,精英群體控制著話語權,一國公共外交的開展往往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即通過大眾傳媒左右他國精英群體的認識和態度,精英群體再通過自身的影響力來左右公眾的認識和態度。所以傳統上,影響一國外交決策的主導力量通常是本國政治精英。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外交模式受到了顛覆式的沖擊。信息生產的個性化和信息表達的互動化使得精英的話語權、輿論控制權逐步瓦解,來自底層的輿論可以迅速傳遍全網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聲音也能匯聚起強大的輿論場。社交媒體時代公眾參與政治和外交的熱情高漲,個人可以比較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推動政治議程的解決。“公眾對公眾”的直接溝通模式已經確立,民意從未像今天一樣得到決策者的高度關注。在這樣一個時代,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精英的傳聲筒,而是公眾的輿論場。
2、從單向傳播者到心靈溝通者
傳統外交重在宣傳和說服,而社交媒體時代的外交重在溝通和交流。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公共外交并沒能得到普遍的認同,更沒有以一門學科的面目出現,而一直被視為是一種“宣傳”的手段。傳統意義上的公共外交脫胎于戰時宣傳,手段比較單一,媒體在公共外交中更多扮演的是單向傳播者的角色。然而,社交媒體時代的的公共外交“依托于平民化的社交網絡工具,更加強調平等基礎之上的政治對話和心靈溝通,而不是單純依賴國家之間的信息落差進行思想灌輸與政治抹黑。”[7]社交媒體以其開放性和互動性成就了自己在公共外交中心靈溝通者的角色。美國學者杰弗里·考恩和阿米莉亞·阿瑟諾曾提到:“公共外交有三個層次,即獨白、對話和合作。有效的公共外交要求國家和個體行為主體從獨白過渡到對話,再到合作,這既符合國際傳播環境變化的趨勢,也順應了傳統外交向公共外交發展的潮流。”[8]與傳統媒體相比,社交媒體更加強調公眾之間的交流、對話和合作,在公共外交中其心靈溝通者的角色愈發凸顯。
3、從讓人生厭的利益代言人到文化交流的使者
“實施公共外交也不能過分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其核心詞是‘公共的,強調提供公共產品,贏取公共支持的合法性基礎。如果片面強調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公共外交和傳統外交就沒有什么區別了。”[9]社交媒體不同于傳統媒體,它的開放、多元、互動和去中心化等特性改變了信息的傳播方式,傳統上的議程設置和國際輿論操作空間都被大大壓縮。因此在社交媒體時代,一個國家通過媒體來操控其他國家輿論、過分追求國家權力和利益的外交政策比較難實施。美國之音(VOA)的公共外交歷史是媒體公共外交的一個典型案例,檀有志在《美國對華公共外交戰略》一書中提到,美國之音的發展歷程中經歷多次政策調整和角色轉變,分別扮演過“反擊法西斯的‘無形利劍”、“反蘇搞演變的‘破城之椎”、“肩負新任務的‘亂國之音”、“為政府補臺的‘反恐先鋒”等角色。美國之音曾犯下不少或煽風點火、或推波助瀾,有時甚至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等“前科”,其在外國聽眾中的公信力自然不免會走下坡路。[10]事實上也是如此,2011年美國之音關閉了對華短波廣播,將其主體業務和戰略資源轉向網絡,并開始采取措施來逐漸改變其以往讓人生厭的利益代言人形象。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也開始重視社交媒體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比如說,印度開展了影像公共外交,定期拍攝和錄制有關國家社會生活的各種影像,然后放置于社交媒體平臺,供世界各國公眾自由下載、觀看和評論。從根本上說,公共外交所承擔的理論使命是溝通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裂痕,架起不同國家民眾超越文明和文化隔閡的橋梁。而這種文化之間的交流需要一個“支點”,社交媒體就可以起到這個“支點”的作用。
四、結語
有學者認為,外交史上有兩次很大的轉型。第一次轉型是從秘密外交到公開外交。目前正在發生的轉型就是第二次轉型,即從職業外交到公共外交。社交媒體的出現將加速公共外交的這次轉型。社交媒體時代的公共外交呈現出了很多新特點,非國家行為體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增強,公共外交從獨白式“喊話”到注重雙向交流,外交的目的不再過分利益化,等等。這些新特點也意味著媒體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以前是精英的傳聲筒,現在要做公眾的輿論場;以前是外交政策的單向傳播者,現在要做讓人理解認同的心靈溝通者;以前往往是讓人生厭的利益代言人,現在則要努力讓自己成為文化交流的使者。
[注釋]
[1]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任海、徐慶超:“媒體外交:一種軟權力的傳播與擴散”,《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4期.
[3]葉皓:“公共外交與國際傳播”,《現代傳播》,2012年第6期.
[4]趙路平、于泓洋、葉超:“特朗普怎樣使用推特——對特朗普推文的大數據分析”,《新聞記者》,2017年第7期.
[5]James Pamment, New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c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Press, 2013.
[6]趙可金:“網絡外交的興起:機制與趨勢”,《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5期.
[7]董青嶺、孫瑞蓬:“新媒體外交:一場新的外交革命?”,《國際觀察》,2012年第5期.
[8]趙啟正主編:《公共外交戰略》,海南:海南出版社,2014年,第197頁.
[9]韓方明主編:《公共外交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0頁.
[10]檀有志:《美國對華公共外交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第135頁.
(作者單位:中央電視臺,北京 10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