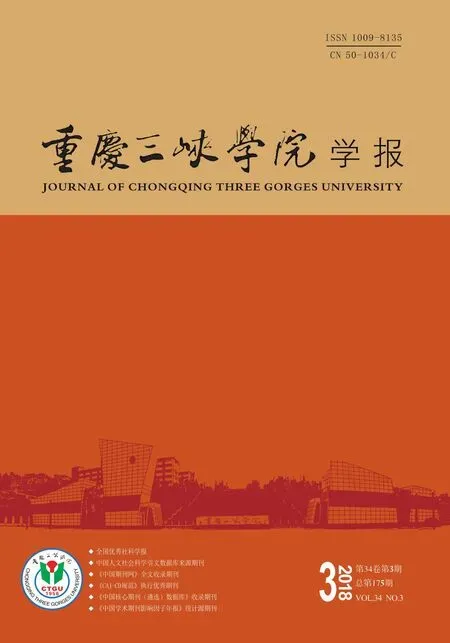《文心雕龍》“文之樞紐”新探
(山東外事翻譯學院國學研究所,山東濟南 250031)
劉勰(約 466—532)在《文心雕龍·序志》中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
很明顯,他是把《文心雕龍》前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作為“文之樞紐”來設置的。而所謂“亦云極矣”,是說達到了極致,至尊、至重、至高、至大,無以復加,更不可移易。由此不難看出他對這部分內容的高度重視,以及這部分內容在全書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何謂“樞紐”?“樞”,《說文》:“樞,戶樞也。”戶樞即門軸,沒有門軸,門戶就無法開合;用來比喻事物重要的、中心的、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紐”,《說文》:“系也。一曰結而可解。”本義為綁束,后稱提系器物的帶子為紐帶,用來比喻控制事物的機鍵、系結事物的中心部分。在比喻義上,二者是相同的。兩者組成一個合成詞,通常用以喻指事物的關鍵部位或相互聯系的中心環節。但用于指稱一部學術著作的關鍵部分,大概是劉勰的獨創。現代漢語中“樞紐”一詞除了廣泛應用于交通或水利工程之外,鮮有用于指稱學術著作結構者。今人按照當代學術著作的構成慣例,一般將劉勰所謂“文之樞紐”稱作《文心雕龍》全書的“總論”[1]164“總綱”[2],也有稱之為全書“導言”[3]的。就是說,研究者大都認識到了前五篇在全書中居于綱領地位并且是一個整體;與此有關的論著不勝枚舉,除了范文瀾(1893—1969)《文心雕龍注》把《諸子》篇拉入總論而把《辨騷》篇割裂出來作為文類之首劃入文體論[4]、牟世金(1928—1989)以為《辨騷》篇雖屬“樞紐”但不屬總論而屬文體論[1]168之外,學界對此大多不存異議。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共同認識還只是初步的、粗淺的。因為“樞紐”與“總論”“總綱”或“導言”相較,不僅是古今用語的不同,在含義上也存在某種差別。對這種看似細微的差別如果缺乏精確的認識,就可能導致對全書理論體系的把握和對劉勰文學觀的認識上出現很大的問題。而事實上,這樣的問題早已出現,并且眾說紛紜,愈演愈烈,由最初的“失之毫厘”,已經達到“謬以千里”的程度,乃至形成了若干學術公案。因此,有必要對其加以認真辨析和進一步闡說。
一、一個還是多個:對“樞紐”的總體把握
在筆者看來,劉勰之所謂“樞紐”與現代學術著作之“總論”“總綱”或“導言”的差別在于:“總論”“總綱”或“導言”是全書的概要,可以包括若干并列的、有某種邏輯關系的條目,分別用來統領全書的不同部分;而“樞紐”,則無論包括了幾篇文字,卻只能是一個結構緊密的整體。我們知道,多中心即無中心,同理,多樞紐即無所謂樞紐矣。
探討《文心雕龍》的“文之樞紐”,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它的前五篇是五個“樞紐”,還是一個“樞紐”?在同一特定語境中,作為“樞紐”,能多個并存嗎?
據筆者理解,在劉勰的設置中,它們只是、也只能是一個“樞紐”。看似并列的五篇文字,其實只是構成這一樞紐的不同構件。而在這些構件中,必定有其核心或主軸。這一核心或主軸,不僅統領其余四篇,而且也對全書起到統領作用。其余四篇,只不過是核心或主軸的附屬物,是圍繞核心或主軸來設置并為其服務的,并不要求每一篇都對全書起統領作用。如果像某些研究者那樣,認為“文之樞紐”部分的五篇文章是并列關系,且為由主到次的線性排列,即彼此分別是不同的“樞紐”,就會在不同程度上偏離劉勰的本意。許多年來,不少研究者對此書的誤讀,以及由此引發的諸多爭論,往往是由于在這一點上出現了偏差。
“文之樞紐”的核心或主軸是什么?揆諸劉勰的寫作意圖,顯然應為在五篇里處于中間位置的《宗經》篇。因為“宗經”是他主要的文學思想,并且貫穿《文心雕龍》全書。《通變》篇中“矯訛范淺,還宗經誥”八個字,可以視為他對全書作意最簡潔有力的表達。而核心或主軸既經認定,其余四篇的附屬地位也就可以確定了。當然,這些附屬的篇章,劉勰也無一不是精心結撰的,里面也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讀者不可因其“附屬”地位而予以輕視。作為單篇文章,它們也各有其表達的中心,不過相對于《宗經》,卻只能是“次中心”;它們主要是分別從不同側面為突出《宗經》的核心或主軸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
這一點,其實并非筆者的新見。近人葉長青(1902—1948)在其 1933年印行的《文心雕龍雜記》中就曾經指出:“原道之要,在于征圣,征圣之要,在于宗經。不宗經,何由征圣?不征圣,何由原道?緯既應正,騷亦宜辨,正緯辨騷,宗經事也。舍經而言道、言圣、言緯、言騷,皆為無庸。然則《宗經》,其樞紐之樞紐歟!”①葉氏原書為其授課講義,由福州職業中學印刷廠印行,引文轉見詹瑛:《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頁。在認定《宗經》為“文之樞紐”之核心或主軸的地位上,這是筆者所見到的最為明確的論述。劉永濟先生(1887—1966)也有類似見解,他在解釋《宗經》時說:“舍人‘三準’之論,固已默契圣心;而此篇‘六義’之說,實乃通夫眾體。文之樞紐,信在斯矣。”[5]5盡管他的論述只是著眼于“三準”和“六義”,沒有顧及到全書,但他指出《宗經》篇才是真正的“文之樞紐”,則是很有見地的。如果不是對全書的理論體系和劉勰的思維脈絡有精準之把握,就不可能做出此種論斷。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以經典為“樞紐”的觀念,還表現于《議對》篇。他說:“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采故實于前代,觀通變于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盡管這里的“樞紐”已經活用為動詞,為緊密聯系、不得脫離(經典)之意,與《序志》篇作名詞用有所不同,但名詞活用為動詞之后,其本義仍然保留,在本句中,以經典為“樞紐”的涵義顯然還是包括在其中的。
當然,由于劉勰把前五篇總稱之為“文之樞紐”,我們不妨在當下的討論中將《宗經》篇看作其核心或主軸,以避免在用語上與原文抵牾。
二、“宗經”何以會成為劉勰主要的論文主張
劉勰之所以會把“宗經”作為其主要的文學主張,就其自身說,實際出于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出于他對儒家經典發自內心的崇拜,其二則是出自他對當時文壇弊端的不滿。這可通過《宗經》《序志》等篇中劉勰的一再表白而清楚了解到。
For the sake of clarity,taking the 7-DOF manipulator shown in Fig.1 as an example,the optimal locked angle of the fault joint is solved as follows.
在《宗經》篇里,劉勰寫道: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于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者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不難發現,在劉勰心目中,五經是那樣的盡善盡美,實在是作文的最高典范。他認為,依托五經來進行創作,就如同找到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所以,為文必須“宗經”。
不僅如此,劉勰還認為,自五經以后文學的發展,開始出現了嚴重的流弊,即所謂“楚艷漢侈,流弊不還”(《宗經》)。到了近代,則愈演愈烈,達到了“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的程度。而要“正末歸本”,使文學發展回到健康的大路上來,必須“矯訛翻淺,還宗經誥”(《通變》)。他的認識是否完全正確,宗經主張在當時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我們今天應該如何評價,可以另作別論,但他之宗經確系出于至誠,則不庸置疑。
除此之外,劉勰選擇“宗經”作為矯正文壇弊端的利器,也和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或內在規律直接相關。那么,這種基本性格或內在規律是什么呢?現代新儒學大師徐復觀先生(1904—1982)對此有過很精辟的論述:
五經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正如一個大蓄水庫,既為眾流所歸,亦為眾流所出。中國文化的“基型”“基線”,是由五經所奠定的。……中國文學,是以這種文化的基型、基線為背景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所以中國文學,彌綸于人倫日用的各個方面,以平正質實為其本色。用彥和的詞匯,即是以“典雅”為其本色。我們應從此一角度,去看源遠流長的“古文運動”。但文學本身是含有藝術性的,在某些因素之下,文學發展到以其藝術性為主時,便會脫離文化的基型基線而另辟疆域。楚辭漢賦的系統,便是這種情形。其流弊,則文字遠離健康的人生,遠離現實的社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便常會由文化的基型基線,在某種形式之下,發出反省規整的作用。《宗經》篇的收尾是“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正說明《宗經》篇之所以作,也說明了文化基型基線此時所發生的規整作用。[6]387-388
徐先生站在思想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對五經在中國文學和文化發展中的作用予以精到的揭示,可謂獨具慧眼。由此我們也可以豁然開朗: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之所以會一再出現形形色色的所謂“復古”運動(或稱“古文運動”),個中緣由,原來在此。而齊梁之際,如劉勰所說,已經“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正是到了文化的基型、基線該出來發揮作用的時候了。當然,此種基型、基線要發揮作用,必須借助于作家作品,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于是自覺地、也是歷史性地承擔起了這份責任。
三、“文之樞紐”何以用了五篇文章來完成
既然“宗經”可以確定為《文心雕龍》統帥全書的主導思想,那么,按說有了《宗經》一篇列于卷首就可以了,劉勰為什么要用多達五篇的文字來加以論述呢?
細加推究,可以發現,這是由于在劉勰的意識中,覺得僅用《宗經》一篇尚不能充分、完整地表述他的宗經思想。諸如為什么“文必宗經”,經書的偉大究竟有什么根本依據,與經書有密切關系的其他前代著作是否也在應“宗”之列,等等,這些都還需要作充分的闡發和必要的辨正。因而他在《宗經》前后又分別寫了兩篇文章來作為鋪墊或附論。這樣的內在理路,可以通過前后各篇與《宗經》的關系來加以揭示。
先來看《原道》《征圣》與《宗經》之間的關系。
在劉勰看來,之所以“文必宗經”,因為五經是由圣人制作的;而圣人之所以要制作五經,是用來昭示“天道”的。只有把這種道—圣—文三位一體的關系徹底地揭示出來,才能使讀者充分認識經書的偉大,進而更好地認同他的宗經主張。《原道》《征圣》篇的寫作因此便有了必要性,他的這一思維路徑應該是不難體察的。盡管我們看到的文本,是由《原道》到《征圣》再到《宗經》,是循著“道沿圣以垂文”的關系,呈順流而下之勢,而在劉勰的構思和寫作中,其實是由《宗經》到《征圣》再到《原道》的,是循著“圣因文而明道”的方向,呈逆流而上之勢。他所要達到的效果,是讓人們認識到五經是天道通過圣人在人間的具現,具有至高無上的神圣性,因之其宗經的主張便具有了“天經地義”的穩固地位。明確了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原道》篇盡管居于全書卷首,但并非“開宗明義”,也不是用來統領全書,而主要是用來為《宗經》張目的。至于《征圣》,則是《原道》和《宗經》之間的必要過渡。究其實,《原道》和《征圣》,都只不過是《宗經》的鋪墊而已。其在“文之樞紐”中的地位,只能是附屬的構件。如果離開了《宗經》,而在前兩篇中抓住某一個或幾個片言只語索求所謂的“微言大義”,就難免走向歧途。例如,把本來只是一般敘述語言的“自然之道也”視為劉勰所本之道、把本來只是一個比喻句的“銜華而佩實”當作劉勰論文的最高標準,就是典型的個案。
劉勰的這一思路和前三篇事實上不同的地位,前賢已有揭示。1970年代,徐復觀先生曾撰文指出:“《原道》、《征圣》,實皆歸結于《宗經》,所以這三篇實際應當作一篇來看。”[6]385祖保泉先生(1921—2013)也曾正確地指出:“‘體乎經’才是‘文之樞紐’的核心,‘宗經’思想乃是《文心》全書的指導思想。”他還指出:“‘道’是靠圣人的文章來體現的,圣人也只有靠文章來闡明‘道’。……一句話,‘道’和‘圣’離開了‘經’,那便成了毫無實際意義的空話。”“從‘言為文之用心’角度看,劉勰抓住了歷來為人們所崇敬的‘文’(六經),把它說成是創作的范本和評論的最高標準,于是撰《宗經》篇。‘經’是‘圣人’撰述的,于是在《宗經》之前,加上《征圣》;圣人之所以為圣人,就因為他能‘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于是在《征圣》之前,又冠以《原道》。其實,論‘文’而要‘原道’、‘征圣’,都不過是為‘宗經’思想套上神圣的光圈而已。”[7]這是很有見地的。其他學者的類似見解還有一些,茲不具引。所可惜者,幾十年來,他們的見解并未引起應有的重視。人們更多的還是孤立地去看待“樞紐”中的各篇文章,而極少有能以《宗經》為制高點俯瞰整個“樞紐”和《文心雕龍》全書者。
再來看《正緯》《辨騷》與《宗經》之間的關系。
通過《原道》《征圣》的鋪墊,《宗經》的主張已經成功地凸顯出來了,按理說劉勰應該自信不會再有人懷疑其“文必宗經”的正當性了。但是,回顧楚漢以來文學發展的實際,他覺得還有一些問題必須厘清,否則人們在踐行“宗經”主張時仍然會遇到問題。
首先是曾“前代配經”的緯書。自西漢后期產生的緯書,至東漢乃大行其道,與經書并行。用劉勰的話說,就是“至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那么,“宗經”的同時,是否也要“宗緯”呢?對此,劉勰的態度十分明確,答案是否定的:“經足訓矣,緯何預焉!”為了申明這一立場,他專門寫了《正緯》篇,用主要篇幅指出緯書的“四偽”,并援引了前賢桓譚(約前23—56)、尹敏(東漢初期人,生卒不詳)、張衡(78—139)、荀悅(148—209)等人對緯書的否定性意見作為論據支撐。當然,由于劉勰是“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序志》)的,他對緯書的價值并未完全否定,而是指出其“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可以“酌”取其“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的成分用于寫作實踐。但這只不過是附帶論及,《正緯》篇的主旨,則是告訴讀者:緯書不是其所“宗”之“經”,“宗經”時是不能將緯書混同其間的。
然后是歷來“詩騷并稱”的《楚辭》。《楚辭》與五經的關系不像緯書那樣密切,但它作為純文學作品卻有很高的成就,曾受到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漢宣帝劉詢(前91—前49)及揚雄(前53—18)、王逸(東漢中期人,生卒不詳)等人的高度評價,認為其“依經立義”“體同詩雅”,“與日月爭光可也”。其中的《離騷》又曾被稱為《離騷經》,劉安還曾為其作《傳》。那么,《楚辭》,特別是其中的《離騷》,是否應該屬于所“宗”之“經”呢?劉勰認為亟有加以辨析的必要,為此而又作《辨騷》篇。他認為“(劉安等)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屬于“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就是說,把《離騷》比擬為經書是褒、揚過分;而說《離騷》全不合經傳,則是貶、抑過當。通過對《楚辭》主要篇章和內容的辨析,他指出楚辭作品與經書有“四同”“四異”,換言之,與經書相比,還是存在差距的,此即所謂“雅頌之博徒,辭賦之英杰”;其作者當然也并非圣人。這樣辨析之后,包括《離騷》在內的楚辭作品,能否作為其所“宗”之“經”,答案就在不言之中了。清人紀昀(1723—1805)批語謂“詞賦之源出于《騷》,浮艷之根亦濫觴于《騷》,辨字極為分明”[8],正是有見于此。當然,《楚辭》作為《詩經》變異、發展的產物,劉勰對其成就是有足夠評價的,但對其流弊也有充分的認識,所謂“楚艷漢侈,流弊不還”(《宗經》),就是他最基本的評斷。與此同時,劉勰深知后世的文學創作已經不可能無視《楚辭》的存在,作者們也不可能不在某一方面受其影響;為了避免其“流弊”,尤其是擔心后來作者因羨慕楚辭的“驚采絕艷”而忘記了宗經,他諄諄告誡作者們在寫作時務必要“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①“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二句乃分承上二句“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而來,“奇”“華”指的是“楚篇”,“貞”“實”指的是雅頌。。研究者如果明確了《辨騷》與《宗經》之間的內在聯系,就不致誤認為劉勰對楚辭的總體評價高于五經,也不會誤以為“《辨騷》是以二十一篇文體論的代表者的身份列入‘文之樞紐’的”[1]168了。至于劉勰對《離騷》及其他楚辭作品的評價與現代通行認識是否一致,則是另一回事,今人正不可因對楚辭的喜愛而去曲解劉勰的本意。
進行了這樣一番“辨”“正”、明確了緯書和楚辭非其所“宗”之“經”之后,劉勰覺得“宗經”的大旗才算真正牢固地樹立起來了。所謂“文之樞紐,亦云極矣”,正反映出了他此時的喜悅和自信。
而這,就是劉勰要把“文之樞紐”寫成五篇的內在緣由。其中不僅道、圣、經是三位一體的,道、圣、經、緯、騷也是五位相關的,缺其一則意義失于完備。其用心之良苦、立論之堅實,在古代文論中罕有其匹。
四、《序志》所述與篇名用字之比較
為正確把握“文之樞紐”的準確內涵,有必要對《序志》篇“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與各篇標題中的用字——即“原”“征”“宗”“正”“辨”的異同進行對比研究。筆者認為,彼此兩者盡管指涉篇章相同,但并非簡單的變文避復,而是在不同語境中,由于立足點不同而進行的精心措置,因此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異。具體來說,就是:
《原道》之“原”,是推原,即把以五經為典范的文的根源推原到神秘的天道;“本乎道”之“本”,是說他的論文是以天道為本原的。
《征圣》之“征”,是征驗,即揭示作為文章典范的五經都是出于圣人之手;“師乎圣”之“師”,是說他的論文是以圣人為師法的。
《宗經》之“宗”,是宗法,即倡言以圣人傳道的五經作為為文的最高標準;“體乎經”之“體”,是說他的論文是以五經為體式的。
《正緯》之“正”,是辨正,即辨正緯書中存在“四偽”,雖曾“前代配經”,但并非其所“宗”;“酌乎緯”之“酌”,是酌取,即可以吸取緯書中有益于文章的成分。
《辨騷》之“辨”,是辨別,即辨析楚辭與五經的異同,指出其地位次于五經,也并非其所“宗”。“變乎騷”之“變”,是變通,即可以借鑒楚辭中文學發展的經驗。
綜合以觀,《序志》中的用詞,完全是從《文心雕龍》全書寫作的需要或所把握的基本原則來措置的;而各篇的標題,則是暫時脫離了全書寫作的需要,緊扣該篇的主要內容和五篇間的內在聯系另行命名的。作者的立足點和所要表達的意思,其實存在微妙的變化。相比之下,可以發現,前三篇對應的字眼,即“本”與“原”、“師”與“征”、“體”與“宗”之間,均為正相關關系;而后兩篇對應的字眼,即“酌”與“正”、“變”與“辨”之間,則因所持的角度不同,存在著棄與取的差別,并非正相關關系。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筆者認為劉永濟先生所說“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論文要旨,于義屬正。后二篇抉擇真偽同異,于義屬負。負者箴貶時俗,是曰破他”[5]10,盡管不無偏頗,但并非全無道理。盡管在我們看來,后二篇是正負兼具、有棄有取的,但與前兩篇相比,角度及立意均有差別,則無疑義。因此,在閱讀理解中,應當兼顧這兩處表述的細微差別,以期全面把握劉勰的用意,而不宜把它們簡單地等同起來。否則,就容易在理解劉勰的思想觀點時出現偏差。例如,有人把《原道》之“原”與“本乎道”之“本”完全等同起來,而忽略了它與《宗經》之間的緊密聯系,沒有看出其事實上作為《宗經》鋪墊的作用,以致過分高抬了《原道》的地位,進而對所“原”究竟為何家之“道”產生種種疑竇,做出種種曲解,引發出種種論爭;又如,有人對《辨騷》之“辨”的作用忽略不計,只注意了“變乎騷”的“變”字,認為劉勰此篇只是為了研究文學的發展或新變而作,而完全無視文中大段辨析文字的存在,進而忽略了劉勰對《離騷》評價的分寸感,甚至把“博徒”與“四異”之類貶詞也強解作褒義,等等,都是由此引起的公案。對此筆者已有專文分別加以考辨[9-10],感興趣者可以參看。
五、余 論
四十多年前,徐復觀先生曾感嘆:“今日肯以獨立自主的精神,對一部書作深思熟玩,分析綜合的人太少了。大家只隨著風氣轉來轉去。百年來的風氣,封閉了理解《文心雕龍》之路。”[11]364至于多年來大陸學界的《文心雕龍》研究,則不僅僅是學術跟風問題,而是所受到的學術之外的干擾因素更多,導致了許多簡單問題的復雜化和復雜問題的簡單化,對“文之樞紐”的把握尤其如此。筆者以為,摒除各種干擾和先入之見,對《文心雕龍》原著“深思熟玩”,根據“實事”來“求是”,切實進入原書的語境,并盡可能抵達作者的心境,弄清其構思、寫作的思維脈絡,從而在實現“平等對話”的基礎上,正確揭示其本來意義,發現其當代價值,服務于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設,才是龍學研究的正途。這樣做,實在要比在原來習熟的道路上進行大量的重復勞動更有必要。
參考文獻:
[1] 牟世金.《文心雕龍》理論體系初探[G]//雕龍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2]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組.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305.
[3] 珊德拉.劉勰的“文之樞紐”[G]//戶田浩曉,著;曹順慶,主編.文心同雕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47.
[4]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4.
[5]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 徐復觀.文之樞紐——《文心雕龍》淺論之六[G]//中國文學論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7] 祖保泉.文之樞紐臆說[G]//文心雕龍學刊第一輯.濟南:齊魯書社,1983:175.
[8] 劉勰.文心雕龍[M].戚良德,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9.
[9] 魏伯河.走出“自然之道”的誤區——《文心雕龍·原道》讀札[G]//中國文論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10] 魏然.讀《文心雕龍·辨騷》[J].棗莊師專學報,1984(1):72-79.
[11] 徐復觀.能否解開《文心雕龍》的死結?[G]//中國文學論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