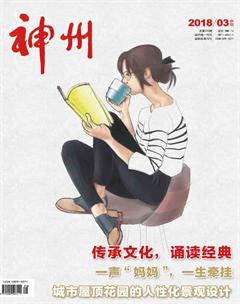從作品《出走》看蒙古族舞蹈的風(fēng)格傳承
李明
摘要:蒙古族傳統(tǒng)舞蹈產(chǎn)生于民間,屬于草原文化影響下的傳統(tǒng)舞蹈藝術(shù),是民族舞蹈中別具特色的一朵奇葩。它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特征別具特色、匠心獨(dú)具,蒙古族民族民間舞蹈歷史悠久,藝術(shù)特點(diǎn)鮮明,挺拔豪邁的舞姿,輕捷灑脫的步伐以及風(fēng)韻獨(dú)具的“肩部動作”是其表演手段和核心藝術(shù)。在飛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中蒙古族舞蹈的發(fā)展和傳承體現(xiàn)在其能夠在原汁原味的表演基礎(chǔ)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大膽創(chuàng)新,從而得到新的升華與發(fā)展,與當(dāng)下時(shí)代進(jìn)步緊密結(jié)合,一代代的傳承下去源遠(yuǎn)流長。
關(guān)鍵詞:蒙古族舞蹈;《出走》;風(fēng)格傳承
一、作品《出走》的劇目分析
蒙古族雙人舞《出走》這部優(yōu)秀的作品,是這部作品的編導(dǎo)萬瑪尖措根據(jù)家鄉(xiāng)父輩外出闖蕩的經(jīng)歷以及多年漂泊、遠(yuǎn)離家鄉(xiāng)的思鄉(xiāng)之情為靈感而創(chuàng)作,情緒自此而醞釀發(fā)酵,兄弟二人即將離開這片給予他們生命和愛撫的大草原,外出打拼,離別的鄉(xiāng)愁縈繞在兩兄弟心頭,一個(gè)和面對家鄉(xiāng)跪倒在地滿目愁思一個(gè)背對家鄉(xiāng)拼命克制思鄉(xiāng)的憂傷,但為了男兒志在四方的理想,這種內(nèi)心矛盾的糾葛,在欲走欲留、欲去欲還之間,以情緒帶動拉扯對抗產(chǎn)生的各種動力引發(fā)了一系列連貫的雙人舞動作。編導(dǎo)巧妙的利用這種內(nèi)心矛盾并在矛盾的激化中,通過舞臺對角線反復(fù)將兄弟倆這種欲走還留:弟弟一次次的回頭,哥哥一次次的阻攔下的離鄉(xiāng)的不舍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終于二人在《天堂》綿長惆悵的音樂中陷入了對故鄉(xiāng)親人、草原的無限回憶中,使觀者不經(jīng)為之潸然淚下,思鄉(xiāng)的哀愁灌滿全場,兄弟兩個(gè)出走草原異常艱難,男兒的剛強(qiáng)和柔情都集中體現(xiàn)在編導(dǎo)動作編排中突出的“跪”,整個(gè)作品中每一次的“跪”都是一次感情的遞進(jìn)和迸發(fā)。編導(dǎo)大量利用現(xiàn)代元素來把控蒙古族舞蹈動作,將兩者自然的融合,利用現(xiàn)代舞的呼吸和頓挫,使動作流暢自然,同時(shí)也加強(qiáng)了蒙古族舞蹈特有的韻味,例如:蒙古族民間舞蹈步伐上的“趟”、“拖”的特點(diǎn)巧妙的滲透在作品中,表達(dá)兄弟二人不愿離開故土的沉重的腳步,可謂之非常貼切、入木三分。
《出走》是一部極為特殊而且又具有典型意義的劇目,它體現(xiàn)了舞蹈家對新民間舞蹈的認(rèn)識和探索,體現(xiàn)了對蒙古族舞蹈如何緊跟時(shí)代,用傳統(tǒng)素材來使蒙古族民間舞蹈既有濃郁的民族味道,保留民間舞蹈的精髓,又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代感,使其能夠更好的傳承下去。《出走》這一大膽嘗試可以說是成功的,是蒙古族民間舞蹈的傳承所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二、蒙古族舞蹈風(fēng)格的傳承
蒙古族民族民間舞蹈以其悠久歷史,鮮明的草原文化藝術(shù)特點(diǎn),挺拔豪邁的舞姿,輕捷灑脫的步伐以及風(fēng)韻獨(dú)具的“肩部組合”相輔相成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表演手段和核心藝術(shù)。
(一)蒙古舞動律特征的傳承
任何一個(gè)民族的舞蹈之所以能成為一個(gè)單獨(dú)成立的個(gè)體,其首要的基本就是它獨(dú)具特色的動律。蒙古族舞蹈的動律是蒙族民間舞蹈的精髓,在作品《出走》中編導(dǎo)的運(yùn)用使其更具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如:1、繞圓動律:蒙古族人民似乎對圓有著天生的偏愛,在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到處都滲透著圓形、圓線、圓韻的各種元素,這些都是繞圓動律的來源。舞蹈《出走》的高潮部分,倆兄弟在面對離別家鄉(xiāng)的不舍而又必須外出拼搏的矛盾沖突下的拉扯中,運(yùn)用了很多揉臂的元素和雙人舞的配合繞圓就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2、擰轉(zhuǎn)動律:蒙古族人身形健碩、體格高大、性格開朗豁達(dá),生活在廣袤大草原上的他們,生活節(jié)奏緩慢,自由而扭動的動律正是上述特征的凝聚,《出走》雖然是柔和了現(xiàn)代舞的元素卻也無可掩蓋蒙古舞的以“攆”和“擰”的挺拔身形體態(tài)緩緩而動,占滿空間,顯得是那樣端莊而凝重。3、橫、擺、扭動律:“橫”始終在橫線的左右方向上;“擺”是指雙手在橫線上左右、上下擺動;“下扭”指腰隨雙手的擺動而左、右擺動,我們稱之為“橫、擺、扭動律”,蒙古舞蹈中的“揉臂”和“拖步”協(xié)調(diào)運(yùn)動則可充分展現(xiàn)出這種鮮明的動律特征,舞蹈《出走》中也運(yùn)用甚多,是蒙古族舞蹈中一種形神兼?zhèn)洹側(cè)岵?jì)的獨(dú)特動律。
(二)蒙古舞表演風(fēng)格的傳承
蒙古族的舞蹈表演風(fēng)格遵從著這樣一種歷史的脈絡(luò)變革發(fā)展著,從原始的繞樹而舞、踏足跺舞、拍手而舞的舞風(fēng)舞韻到源于宗教流傳極廣雄厚凝重的“查瑪舞”“安代舞”,再發(fā)展為匠心獨(dú)具、風(fēng)采卓著的狩獵性舞蹈,再到本文中由萬馬尖措老師所編創(chuàng)的優(yōu)秀的現(xiàn)代蒙族作品《出走》,最后到現(xiàn)如今由眾多優(yōu)秀的舞蹈家、編導(dǎo)家編創(chuàng)出得無數(shù)風(fēng)格各異、異彩紛呈的舞蹈舞劇作品,這無疑都是一種對其表演風(fēng)格的傳承和詮釋。數(shù)千年來它的表演風(fēng)格和形式不斷變化發(fā)展和完善,符合各個(gè)階層審美情趣代表了先進(jìn)文化方向的優(yōu)秀作品層出不窮、百花齊放,但無論如何變化都深深的打上了蒙古族舞蹈文化自身特色的烙印無法改變。在本文所淺析的作品《出走》中雖然充滿了大量的現(xiàn)代元素,但是其核心內(nèi)涵和表演風(fēng)格卻處處不體現(xiàn)著一種來自血脈的傳承一種歷史的繼承,作品《出走》在現(xiàn)代視角下以傳統(tǒng)的蒙古族表演風(fēng)格為基礎(chǔ)巧妙的運(yùn)用現(xiàn)代舞的元素來表現(xiàn)可謂大膽創(chuàng)新,匠心獨(dú)具。
(三)蒙古族舞蹈風(fēng)格傳承的意義
蒙古族傳統(tǒng)民間舞蹈具有悠久的歷史,是歷經(jīng)千百年來的國粹,我們應(yīng)該對其進(jìn)行舞蹈文化的創(chuàng)新傳承,創(chuàng)造新的被大眾所接受,賦予舞蹈文化和知識的再生產(chǎn)性,通過再創(chuàng)造,實(shí)現(xiàn)舞蹈文化的創(chuàng)新生產(chǎn),而不是簡單重復(fù)生產(chǎn)。蒙古族民間舞蹈藝術(shù)是我國特有的草原文化藝術(shù),弘揚(yáng)民族文化,如何對其進(jìn)行保護(hù)和發(fā)展,使其傳承下去是我們的責(zé)任。
本文從《出走》這樣一個(gè)優(yōu)秀的蒙舞作品中來看蒙古族舞蹈的風(fēng)格傳承與文化內(nèi)涵,無異于管中窺豹。《出走》這樣一個(g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蒙族相結(jié)合的優(yōu)秀作品既是一種中西合璧的歷史必然,同時(shí)也是文化融合的未來潮流趨勢,我們要想更好的發(fā)揚(yáng)和傳承草原文化和蒙古族舞蹈的精髓,就必然需要更多類似好的作品,這就要我們在把握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和優(yōu)秀草原文化的基礎(chǔ)中一開頭包容的思想結(jié)合現(xiàn)實(shí)生活,堅(jiān)持先進(jìn)文化方向,創(chuàng)作出更多、更優(yōu)秀、更具代表性的舞蹈作品,才能為蒙古族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添磚加瓦,再鑄輝煌。
參考文獻(xiàn):
[1]衛(wèi)平.新世紀(jì)蒙古族舞蹈發(fā)展略述[J].內(nèi)蒙古藝術(shù),2002(1):51-52.
[2]高向英.對蒙古族舞蹈發(fā)展的幾點(diǎn)思考[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漢文版),2005,26(2):92-95.
[3]陳二勇.基于蒙古族舞蹈獨(dú)特的個(gè)性特征分析[J].戲劇之家,2014(16):160-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