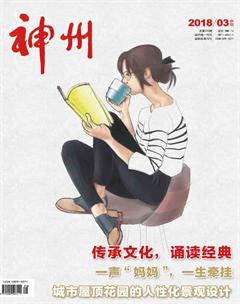張愛玲與蕭紅的語言風格比較研究
劉暮雪
摘要:張愛玲和蕭紅是中國文壇上閃耀的兩位女性作家,二者筆下描述了不少鮮活而動人的人物形象,尤以女性形象突出。本文從模仿方向、描寫手法、修辭方式三個層面對二者的語言風格進行比較研究,探求二者作品差異。
關鍵詞:張愛玲;蕭紅;語言風格
一、引言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民國中末期,文壇大盛。才子才女層出不窮,其中不乏有著文筆相近者,而蕭紅與張愛玲便是兩朵同樣憂郁動人,卻散發出不同芬芳的奇花。1942年蕭紅逝去,1942年張愛玲初入文壇。巧合的時間節點,相似的人生經歷,相同的細膩情思,卻并未使她們的風格一脈相承地貼近。雖同樣關注的是人生本質的深刻,同樣是在社會與家族環境下的身不由己,但字里行間都透露出兩人極大的不同。文字乃文章之細胞,而文風便構成了差異。所以本文將試圖從語言風格的角度一窺兩位才女作品之差異。
二、文獻綜述
作為民國文壇上兩位風格獨特備受矚目的女作家,不少學者早已對她們的作品和人生經歷作出了不少對比。
張蕾、馬樂(2017)從蕭紅詩化語言的運用,兒童化語言的運用,修辭方法的運用,自傳式語言的運用和地域化語言的運用五個方面對蕭紅的作品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他們指出蕭紅獨樹一幟的語言風格是通過其獨特的兒童敘事視角、女性意識、深刻的生命意識和地域文化意識而呈現的。
陳俐(2013)和覃治華(2008)通過分析都發現了蕭紅小說語言中“陌生化”的特點。他們認為因為蕭紅的作品中有大量超常規文體語言的使用,進而使她的文章產生了生疏感和新鮮感。比如陳俐提到在《呼蘭河傳》中“這榆樹在園子的西北角上,來了風這榆樹先嘯,來了雨,大榆樹就先冒煙了。” 這一句話中蕭紅并沒有按照人們尋常的思維順序進行論述,她將語序倒轉,將“風來了”“雨來了”這類話反過來說,便使尋常的,熟悉的事務自然的陌生化了。而覃治華也引用了《王阿嫂的死》中“山上黃了葉子的樹,在等候太陽。太陽出來了,又走進朝霞去。”這句話,闡釋了同樣的特點。由此可見,蕭紅語言陌生化的特點為她的文章營造了美感,也體現出了她作品中所具有的現代意識與一定的審美追求。
李琦(2012)從語言特點入手,分析了張愛玲小說之所以成功的三個語言特征:古典和現代元素的融合,新奇貼切的比喻和富含哲理性的語言,此外還分析了她獨特的語言藝術風格形成的原因:家庭的熏染,天賦的獨特性以及時代的影響,并通過這些分析得出了張愛玲的文章獨具特色且自有一定高度。
魏華(2012)從張愛玲語言藝術風格入手,提出了“張愛玲體”的概念。所謂的張愛玲體,劉川鄂認為其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性的主題將女人的命運加以“犯沖”的色彩和蒼涼的基調并以參差的結構和繁復的意象將其表現出來,而魏華將其總結為張愛玲將古典元素與現代元素相結合,以獨特的語言風格和流暢且靈動的筆觸描繪出的一種以蒼涼為底色的人性社會。她將人物放在日常生活中,看似脫離了過去社會和社會大環境,卻實則用她富有張力的語言生動的刻畫出了社會在潛移默化中為這些小人物決定的凄慘的命運,使他們或肢體殘缺,或精神破碎。比如《金鎖記》中描述的悲劇人物曹七巧,關于她的語言描寫呈現著一種凄涼的缺失,而關于她的外貌描寫則體現著一種美感。“七巧笑了一聲道:‘難不成我跟了個殘廢的人,就過上了殘廢的氣,沾都沾不得?她睜著眼直勾勾朝前望著,耳朵上的實心小墜子像兩只銅釘把她釘在門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標本,鮮艷而凄愴。”
韓雅(2015)從美術的角度,結合了沃爾夫林的藝術風格理論對蕭,張二人的文學作品進行了研究。她通過五對藝術風格學基本概念,將二人的作品進行了對比分析。尤其是在語言方面,她指出張愛玲的筆觸更加的細致,就像工筆畫,一絲一線都詳細的精心設計。而與之相對,蕭紅的描寫則更加寫意,仿佛是由色塊的疊加而形成,隨心所欲。例如《小城三月》中的人物翠姨,從頭至尾也沒有關于她的肖像描寫,只是通過描寫她的儀態,她的說話風格便勾畫出了一位雖面容如隔紗卻能讓人感到她沉靜穩重氣質的女子形象。而反觀張愛玲的作品,僅僅是關于眼睛的描繪便各有不同。比如《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眉心很寬,一雙嬌滴滴,滴滴嬌的清水眼。”而印度公主則有著“影沉沉的大眼睛”。一下便比對出了從外貌到性格中的差異,十分精巧。如此,二者區別,可見一斑。
王彥(2006)從心理學的角度結合了弗洛伊德所說的“替代性滿足”,解釋了蕭、張二人對對比強烈的色彩選擇源于二者相似的童年經歷和起伏命運。她們試圖通過作品中色彩的鋪染來為現實人生中的蒼白補色,以達到代替性的心理滿足。同時王彥還指出二者雖語言風格迥異,卻同樣選擇以色彩描繪來反應主題,并構建不同的色彩話語世界,某種程度上貼合了格式塔心理學派的“異質同構” 理論。
三、張愛玲與蕭紅的語言風格
(一)模仿方向:紅樓夢vs魯迅
創新是文學的生命,但是創新離不開傳統的滋養。文學的創新是基于對傳統文學語言的高度熟稔而做出的大膽嘗試和靈活應用。
張愛玲出生于沒落的官宦家庭,自幼便浸潤在古典文學的氛圍中,并深諳其道。她熱愛《紅樓夢》一書,文風也頗受其影響。如紅樓中對黛玉的描寫“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琉璃瓦》一文中,姚家大女兒的形象躍然紙上,“人像金瓶里的一朵梔子花。淡白的鵝蛋臉,雖然是單眼皮,而且眼泡微微有點腫,卻是碧清的一雙美目”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晚年的張愛玲還寫過《紅樓夢魘》一書。此書作為一部考據性著作,張愛玲不惜以十余年時光著成,可見其對紅樓夢的熟悉與癡迷。固然醉心于紅樓夢,但張愛玲的文字也并沒有一味仿古,受時代和家庭環境影響,她的作品中包含著許多現代的元素。例如《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王嬌蕊為了與情人佟振保在一起,毅然決然同丈夫離婚,便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果決性格特征的體現。
反觀蕭紅,結合《回憶魯迅先生》一文,魯迅先生帶領她進入文壇,她深受先生影響。而透過“魯迅的森然冷峻與蕭紅的細致入微”的區別,我們又不難看出他們所共有的一針見血,力透紙背的特點。這一特點鮮明地體現在了《生死場》一書中,麻木的農民、對死生的輪回掙扎,將當時中國人的劣根性直白地剖開在讀者的面前,與直面的中國人劣根性的魯迅先生極為相像。
(二)描寫手法:勾畫VS 潑灑
將張愛玲和蕭紅的作品放置一起時,我們不免會通過他們的文字觀感而產生一種整體的印象。
張像是個雕刻家,一刀一刀地雕琢著文字并勾勒出極其鮮明的人物。就如其文《色,戒》開頭對王佳芝的描寫,額、發腳、六角臉、淡妝、薄嘴唇、云鬢、后發、手臂,電藍水漬紋緞齊膝旗袍,半寸高的小圓角衣領、與耳環成套的領針,細節入微,精致萬分,就宛如一幅工筆畫,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蕭紅則更像個寫意的畫者,筆墨潑灑,用直白淺顯的描述并傳達最深切的情感,就如她在《呼蘭河傳》中描繪的“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她甚至都沒有描述花為何花,蟲是何蟲,但那些修飾事物本來面目的形容并不重要,她屬實已經將那寂寞與百無聊賴勾畫了出來,于情感上極為靈動。
(三)修辭方式:新奇vs平實
雖然描寫手法上,張愛玲是細致勾畫,蕭紅則是寫意潑灑,但有趣之處在于她們兩者若落在修辭的使用上卻又時反了過來。
張愛玲喜歡用新奇的比喻來刻畫出眼前事物的特征,即使本體和喻體毫無關聯,卻能很客觀的寫出“神”來,就似她在《天才夢》這篇作品的末尾,比喻一個天才橫空出現在世人面前時把華美的袍子和虱子放在了一起。其實便一語道破了她對人生的看法對生命的理解,即看似輝煌的人生,往往暗藏著最最悲涼的底色,也為她所有的作品定下了蒼涼的底色。
蕭紅的修辭則是平實的,最貼近現實刻畫的,卻體現了她對于生活最細致的觀察,最真實的感受。就像她在《火燒云》中提到的“這地方的火燒云變化極多,一會兒紅彤彤的,一會兒金燦燦的,一會兒半紫半黃,一會兒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黃,茄子紫,這些顏色天空都有,還有些說也說不出來、見也沒見過的顏色。蕭紅用最尋常的比喻形容了云的模樣,卻有著最生動的樣子。質樸的濃麗的色彩強烈的襯出了鄉村生活原始的美感,形成了蕭紅作品的底色,使她的作品迸發著無限的生機。
四、結語
時代的大書不停地在翻頁,春夏秋冬相無聲更迭,無數文人都如飛花,寥落成塵。我們無法阻止一個盛世文壇的隕落,物質化和享樂化在不斷侵蝕著我們的生活。但至少我們還可以追憶,透過那兩朵嬌艷的花朵所留下的余香,來一窺那所謂黃金的時代。
參考文獻:
[1]陳俐.陌生化——蕭紅小說語言的審美訴求[J].昭通學院學報,2013
[2]韓雅.論張愛玲與蕭紅的小說藝術風格差異[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
[3]李琦.論張愛玲小說的語言藝術[J].青年文學家,2012
[4]覃治華.淺談蕭紅小說的語言特征[J].呂梁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
[5]王彥.論蕭紅與張愛玲的色彩話語世界[J].滁州學院學報,2006
[6]魏華.張愛玲小說語言風格影響之評述[J].滁州學院學報,2012
[7]張蕾、馬樂.不一樣的蕭紅——蕭紅小說語言特色淺析[J].哲學文史研究,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