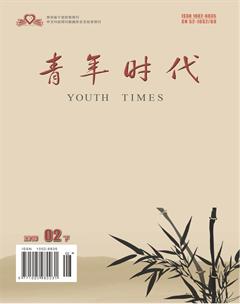淺析沈從文在《水星》雜志中的創作歷程
易倩
摘 要: 《水星》是一種純文學創作月刊,產生于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文壇,其在培育新進文人作家,鞭策文體試驗和藝術創新等方面的功用不容小覷。沈從文作為我國近現代著名的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其散文藝術創作中那顆憂國憂民的激越之心與穿破迷障如電的雙目;小說創作故事形態對生命的救贖以及詩體創作中對現實的憂患和嚴肅的思考均是沈從文的代言詞。它們共同構建“湘西世界”,一同探究現代性審美,這無疑是沈從文在《水星》文體試驗中極具經典化的貢獻。《水星》孕育了一批杰出的作家作品,沈從文與之協同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空間,在文學的星空中閃耀出光芒。
關鍵詞: 《水星》;沈從文創作;心路歷程;現代性
現如今,沈從文先生的創作已被廣為傳頌,乃至其筆下的“湘西世界”也被眾人推崇。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大師、文人乃至平凡人對沈從文先生的作品進行深入的研究,對其思想也逐漸深入理解。相比于其后期的創作,沈從文先生于《水星》雜志的創作好似“名作”被世人熟知。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嘗試簡要歸納沈從文在《水星》雜志中刊登的三類文體,分別以散文體《中國人的病》《湘行散記》、短篇小說體《知識》和詩歌體《北京》為例著重分析其不同文體作品中體現的不同思想;第二部分以第一部分為引,深入分析影響沈從文創作的多重因素即心路歷程,進而從某種程度上總結其創作與影響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第三部分試圖淺析沈從文的創作所帶給《水星》雜志以及后世的現代化影響,從中感受沈從文先生的一片赤誠之心和對民族前途的深層思考以及對人性的思索。
一、《水星》之作品解讀
(一)《中國人的病》、《湘行散記》——沈從文在《水星》刊物上發表的散文
在《水星》雜志中,沈從文的散文體集中體現在兩種類型,即哲理思辨類散文,如《中國人的病》與湘行散文,如《湘行散記》系列文章。
“‘獨立人格,‘自由思想,道家的清靜無為,墨家的勤勉風范,儒家的憂患意識,這一切都從沈從文的文字里汩汩而出。由此我看到的沈從文便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而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1]《中國人的病》的編選者劉紅慶如是說。《中國人的病》是沈從文在《水星》中發表的經典散文之一,雖然時間已去近70年,但文章中所呈現的社會現實與今天的社會現狀卻相差無幾,字里行間透露著極強的“現實主義”。愛國這一宏闊的社會主題,似難非難,似簡非簡。我不禁思考:中國人的病——病的根源在哪?一個國家,它的政治上必定不乏屹立不倒的普世官僚,卻極度缺乏具有強大魄力的政治家,學術上也少有對民族、國家無盡熱愛的學術哲學家。影響了中國幾千年腐朽的儒家文化正是其病根所在,他們麻木眾人的思想,阻礙社會的進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吃人”二字。如此糊涂,何來興國?近百年后重提中國人的病,現實告訴我們:這病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愈加嚴重,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憂慮。沈從文先生用憎惡的口吻,揭露、批判了虛偽、自私、腐敗的官僚資產階級與上流衣冠社會,直指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尖銳、透徹不讓魯迅!
再看《湘行散記》,“湘西情結”伴隨了沈從文先生的畢生,貫穿了他一生文學創作的總體進程,并滲透到他的各類文學文本之中,在散文文本中的體現尤為突出。沈從文以美學的方式理解湘西,與社會洽談,與世界和解。在《水星》雜志中刊登的《湘行散記》系列散文中,作者詩畫相融,描繪了一曲湘西田園牧歌。文章以議論的筆法袒露作者對其故鄉湘西美景的熱愛和對湘西人民寧靜生活的向往與憧憬,以樂觀積極的語調書寫著湘西底層人民的艱苦生活從而對“知識分子”進行尖銳的嘲諷,美文中夾雜著幽默與諷刺韻味。《湘行散記》以作者旅途的行程為整體線索,行文如青云,如流水,從容中浸透著作者豐富的個人情感和淡淡的內心憂慮。仔細揣摩,《湘行散記》不但是一系列美文,它亦是悲憫人生的生命哲學,在歌頌湘西原始文明所孕育的健康且充滿活力的生命同時,也融入了作家隱隱的傷痛與憂思。在浪漫的牧歌情懷里,彈奏著這并不和諧的沉痛的樂章,使散文在唯美之外還承載著些許沉重的歷史感與負重感。透過字里行間,我不僅看到了湘西優美的風土人情,還觸摸到了作者那顆赤誠的內心。在給人唯美的視覺盛宴的同時,亦給人以思想上的啟發,促使我們熱切關注沈從文先生構建的“湘西世界”,激發我們對寧靜生活的向往與憧憬以及對整個民族所承受的苦難歷程加以思索。
(二)《知識》——沈從文在《水星》刊物上發表的短篇小說
沈從文是現代文學史上氣派獨特的小說家,其短篇小說選用了以外聚焦敘事偏移的敘事聚焦模式,使之作品既呈現出明智、沉著的藝術效果,又避免了讀者在解讀作品時的主觀隨意性,這奠定了其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知識》是沈從文在《水星》中的短篇小說之一。這篇小說以那個動蕩的年代為時代背景,講述了一個在外求學有所成就后歸回家鄉,并希望在自己家鄉干出一番大業的哲學碩士,在回鄉離家不遠的路上目睹的一件影響他終身的事情。一青年男子在被毒蛇咬死后,他的家人面對這個事實所流露出的那份淡定與平靜,讓這位哲學碩士困惑不已,不解為何面對一條生命,他的家人竟如此淡漠。卻因那青年男子的父親、母親的一席話頓然醒悟“這才是自己要學的!”。正如那父親道:“世界上哪有不死的人,人死了,我坐下來哭,讓草在田里長嗎?死的就盡他死了,活著還是要好好的活,只要能夠活下去,這個人大約總會好好的活下去的。”恰如那母親說:“人死了,我就坐下來哭,對他有何好處,對我有何益處。”[2]這是一部發人深省的短篇小說,它延續了作家對生命尊嚴和人性尊嚴的反思,充分表達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對那所謂文明人對現實生活無知嘲諷,基本達到了沈從文對樸素、理智,冷靜的藝術效果的不懈追求。沈從文先生巧妙地將自己的思考從容不迫地滲透到人物場景中,從淳樸的氣息中散發出淡淡的憂郁,將一切憂思都消溶與淡泊之中。
(三)《北京》——沈從文在《水星》刊物上發表的詩作
沈從文在《水星》刊物里創作的這一時期正處于其詩風轉變時期。評論家韓侍桁曾在《一個空虛的作者——評論沈從文先生及其作品》一文中這樣評論沈從文先生的寫作傾向:“若順序的讀了這位作者前后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他的文字越來越輕飄,他的內容變得越來越空虛。”[3]這話雖含有貶義色彩,卻又隱約道出其風格的變化。
《北京》是沈從文這一時期表現對社會現實的憂慮和嚴峻思考的代表詩作之一。當時的國家時局動蕩,作者在詩中這樣描寫黃昏時分的古都北京:“天空中十萬個翅膀接天飛,/莊嚴的長征不問晴和雨。/每一個黑點皆應跌落到城外青霧微茫田野里去,/到黃昏又帶一片夕陽回。/(這烏鴉,宮廷柏樹是它們的家)/一列骯臟的駱駝負了煤球也負了憂愁,/含淚向長街盡處凝眸。/街頭巷口有十萬輛洋車,/十萬戶人口在圓輪轉動下生和死。”[4]《北京》一詩盡顯詩人亂世中的悲情與惆悵。通過“天空”“翅膀”“田野”“烏鴉”“柏樹”“駱駝”“長街”“洋車”“圓輪”等一系列意象巧妙地向讀者展現出那歷史的回眸瞬間,既象征著中國紛亂的世事和千萬苦難民眾所背負的傷痛,卻又無奈對這個千瘡百孔的祖國飽含深情。只有在夜里,我才敢低喊你的名字——北京!
二、沈從文創作之心路歷程
沈從文作為中國知名文學家,是中國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轉化的產物。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些許影響文學成長的內在要素仍然對沈從文先生的創作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有學者曾從鄉土、都市、出版、大學、女性、政治等多個方面探討了影響沈從文先生的創作因素。本文主要結合沈從文在《水星》刊物中發表的作品對其心路歷程作簡要概述,并分析總結其互動關系,為第三部分沈從文創作的現代審美學意義的論證做引論。
(一)鄉土之湘西情結
“湘西情結”堪稱貫穿了沈從文先生畢生創作的全部過程。我將其創作大抵劃分為三個時期。《水星》雜志主要涉及前兩個時期的作品:1924-1927是原生態的早期階段,在此期間,沈從文將湘西描述為“原型世界”;1928-1936為中期,這一時期正是《水星》問世時期。沈從文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原生態描述到以文化視角來審視社會乃至人生的過渡。沈從文按自己的生活閱歷與體驗以及對理想的追求,構建了一個“湘西世界”的假象,具有極高的文學審美及批判價值。這一創世性的轉變使得沈從文以一種藝術的方式理解和闡釋湘西,以自己獨特的見解創作了《湘行散記》系列散文發表在《水星》中。
(二)都市之多元化因素
沈從文先生自稱“鄉下人”,但其實他的大半生都在都市中度過,其文學活動亦多是圍繞都市而展開。若說湘西情結為沈從文先生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資源,那么多年的都市生活則給予沈從文先生的文學活動及其成長歷程以堅實的政治舞臺。北京與上海我謂之沈從文先生的“雙城”,它們共同影響了沈從文先生文學創作與心路歷程。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群體成員間的意識形態分歧逐漸公開化,因而在北京構建了一個多元的文化空間,這為沈從文先生的文學創作早期提供了難能可貴的發展空間。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在徐志摩、胡適的扶助下獲得了初步績效。20年代末,沈從文便追隨新文化中心難移的腳步轉陣上海,其創作受益于上海多元化的社會體制而飛速發展并趨于成熟。1933年重返北京,與“京派”結緣,從中吸取精神營養,盡情揮灑其文學創作的光輝。相繼在《水星》、《國聞周刊》等雜志期刊發表散文、小說、詩體創作,代表作如《北京》、《情緒的體操》等,由此達到了登高望遠的人生彼岸。
(三)政治之捍衛自由
沈從文先生一生都在呼喚一個明媚的新中國。沈從文先生一生坎坷,他一直在左翼和右翼兩大文學陣營的摩擦與抗衡中度過。究其原因,沈從文先生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個人與時代的關系都有著獨特的見解。他一生都在堅守文學獨立之原則,并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強調文學為社會作用的看法都是其坎坷心路歷程的見證。《水星》雜志創作時期,國家時局動蕩,沈從文個人生活發生各方面的改變加之其創作上意識的自我突破都為沈從文的文學活動打下基礎,不可磨滅。對中國五四時期以來的知識分子來講,孤獨和苦悶的情愫跬步不離地感化著它們。沈從文先生獨樹一幟,他一生的沉浮跌宕,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其孤獨情愫更加持久、深刻。《中國人的病》、《風雅與俗氣》等批判性散文均揭示了沈從文一生從孤立到絕望的心路歷程。
三、審美之現代化余響
有學者以為欲區分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其實不只是時間維度上的前后,現代文學更是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兩者在意識形態、審美韻味、語言工具等方向都有著明顯差異。于是,我將沈從文先生的創作放在現代文學發展蛻變的歷史進程中加以索求,從影響了現代文學發展的要素加以分析,進而闡釋沈從文先生文學創作的審美現代化影響之所在。
首先,沈從文先生所創造的鄉土散文對當今文學領域具有跨時代的借鑒意義,其地位不容小覷。其文學活動蘊含著一定的審美意識,不僅提高了作品自身潛在的價值,同時也引發人們的思考。讓讀者在走進當時真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同時,感受其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深沉思考,這便是沈從文先生一生的信仰——美與自由。正是基于沈從文先生對故鄉美景的熱愛和對寧靜生活的向往,才造就了其鄉土散文的藝術成就,隨之帶動了文學領域的整體進步。
其次,沈從文先生的小說創作深深根植于深厚的中國傳統敘事藝術的基礎,其敘事藝術吸收、借鑒、繼承并發揚了中國傳統敘事藝術中的有益成分,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和民族風格,為世界敘事藝術的殿堂新添了中國元素與色彩。沈從文先生結合新的時代背景和時代特點,創新中國傳統敘事藝術,鞭策了中國傳統敘事藝術的發展。
綜上所述,沈從文先生是我國第一個對現代文明進程進行深刻反思的文學家。他自覺地扮演著一名批判者、揭露者、和反思者的形象。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沈從文先生自成一家,他的創作給我們構建了一個充滿人情韻味的文學寰宇。他所構建的文學世界不僅僅意味著某種理想化的存在,它更是揭露現實丑惡的一面明鏡,是一種否定現代的無窮力量。沈從文先生的文學活動為后人反思和批判現實提供了引子,召喚著人們覺醒并不斷追求更加人性化的現代社會,這正是沈從文先生文學創作的現代審美品格之所在。
“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這是沈從文先生的一生寫照。
參考文獻:
[1]沈從文,劉紅慶.中國人的病[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47.
[2]沈從文.知識[J].水星,1935(1):3.
[3]韓侍桁.一個空虛的作者——評論沈從文先生及其作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69.
[4]沈從文.北京[J].水星,19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