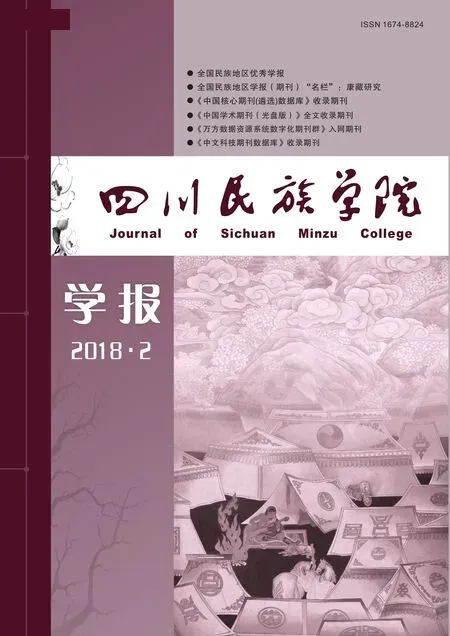行到高處:楊嘉銘教授的學術生涯及其《格薩(斯)爾》圖像研究的心路歷程
楊公衛 馬一鳴 曲 讓 楊桑杰
楊嘉銘教授,四川省康定市爐城鎮人。1964年高中畢業后參加工作,先后從事藏區建筑及康定師專創辦和教學工作,2000年調入西南民族大學,任西南民族大學博物館館長及民俗學碩士點領銜導師、二級教授。2012年退休至今,已過70高齡的楊嘉銘教授仍堅持從事藏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先生幾十年來堅持自學與田野調查相結合,在藏族地區積極開展調查研究。行跡遍布五省區藏區,學術成果頗有建樹。其中在藏族建筑、藏族教育、藏族歷史文化、格薩爾圖像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等方面屢有創新成果。先生在田野調查方面,堅持實地調研與深度訪談。對于當地文化現象,通過文獻閱讀與考古發現探索其文化價值。對于微小素材,亦記錄求證,上下求索,力求見微知著,一葉知秋。
2017年11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公布了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名單,全國獲批立項共311個項目,其中我校獲批7個項目,立項數創歷史新高,位列國家民委委屬高校第一,四川省內高校并列第一,與山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并列全國第十。在我校7個重大項目中,最吸引我們眼球的是楊嘉銘教授的“英雄史詩《格薩(斯)爾》圖像文化調查研究及數據庫建設”。楊嘉銘教授在退休后的古稀之際,項目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支持,這是對楊教授學術生涯四十多年來堅韌不拔地走自學成才之路,刻苦攀登學術高峰的精神,碩果累累的學術成就的最高肯定。行到高處,水到渠成。我們作為晚輩有感于此,認為先生幾十年堅持田野,堅持自信自強,獨立創新的學術經歷與田野調研的心得和格薩爾圖像文化的研究的寶貴經驗需要繼承發揚。我們帶著一份好奇之心,通過對楊嘉銘教學術生涯的了解學習,進行總結梳理,這給予我們后輩莫大的啟迪和教益。
訪談者:楊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近40年的時間,您對藏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和成果涉及了多個領域。您的行跡遍布康藏山川水系,成果廣博。您能否和我們談談您四十年的學術經歷?
楊教授:回首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我將其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即前十年的業余初學階段和之后三十年的步入專業學術道路的自學階段,直到現在我都始終堅持自學。前十年的學習階段可以說是十分艱苦的,也帶著幾分迷茫。高中畢業參加工作后不久,“文革”就開始了。十年“文革”之后,自己最寶貴的青春也一去不復返。為了追回已逝去的年華,決心在工作之余,快馬加鞭自奮蹄。為了讓自學的苦途能堅持下去,我在家里的墻壁上掛上“君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笨鳥先飛”、“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等警句,以鼓舞自己自強的意志。同時,堅持學習一些有關民族方面的知識,學習有關地方文化方面的知識。堅持筆耕不輟,以不斷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和寫作水平。老實說,從1977年至1985年的八年多時間里,自學倒是有了較大的起色,但究竟今后要干什么,卻是一片茫然。
值得慶幸的是,1985年7月,康定民族師范專科學校(今四川民族學院)籌建,我被調去參加籌備工作,一年之后便留校任教。這個機遇,成就了我以后民族學,藏學研究的方向,并且自學的信心和決心也就更加堅定了。
兩年之后(1987年),通過奮發努力,我慶幸趕上了全國首次職稱評定,獲得助理研究員職稱。同時也趕上了甘孜州人民政府委托學校承擔的《甘孜州民族志》[1]的編寫工作,并擔任這項編寫任務的主編,從而實現了人生職業道路上的一次轉身。
我的第二階段的自學是一個漫長的歷程。從我調到康定民族師專開始至今,大約30多個年頭。這段自學歷程不但漫長,而且難度比第一個階段艱難、復雜得多。首先,學習的專業理論不僅深度更深,同時也更廣泛,而且需要追趕學術前沿。其次是要有大量的學術成果問世,以體現出自身自學最為客觀、最具說服力的實證。在所出版和發表的成果中,還必須有代表公信力的相關獲獎成果,再有就是反映成果多少的數字累積量。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先后發表了以藏族歷史文化為主的研究文章120余篇,出版(含獨著、合著)專著20余部,總撰稿字數達400余萬字。曾參與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5項;國家民委社科基金研究項目1項;參與教育部世界銀行貸款研究項目1項,教育部重點招標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一項;以及中國文聯國家重點出版項目《中國唐卡藝術集成——德格八邦卷》[2]的編寫;主持過四川省社科基金研究項目2項及多項地廳級項目。成果先后獲得省部級一等獎2項,二等獎4項,三等獎5項等等。在1996—1997年度,我獲得由四川省總工會、四川省職工自學成才獎勵基金會頒發的“四川省職工自學成才一等獎”。1999年,先后被中華全國總工會、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勞動及社會保障部聯合授予“全國自學成才者”榮譽稱號及中華全國總工會授予的“全國自學成才十佳標兵”稱號。我自學成才的事跡一時成為佳話,并且被許多報紙雜志登載和宣傳。
這是我四十年來學術生涯的大概情況。回首幾十年,我一直堅持自學,從最初摸索的十年到走上學術之路的三十年里,始終保持初心,堅持嚴謹的態度,堅持刻苦鉆研的學風,為藏族歷史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家鄉社會經濟的發展,民族地區教育的提高,藏族文化的推廣,以及為社會服務中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學界同行的肯定,社會和國家的認可讓我在學術領域中實現了由自覺到自信的突破。對于藏族面具、藏傳繪畫、藏族石刻的研究,除了提升自己對藏族歷史文化研究水平,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外,客觀地講,也為后來自己開展《格薩(斯)爾》圖像的研究給予了學力上的巨大支持。
訪談者:楊教授,聽說在您的學術生涯中,您最重視田野調查,足跡遍布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藏族地區,許多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扎實的田野調查之上的。您能否和我們談談您田野調查的經歷和您獨特的心得?
楊教授:眾所周知,凡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需要學習和掌握田野調查的基本理論和知識,并以此作為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大凡成功的學者以及他們的傳世之作,大都與扎實的田野調查分不開的。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早年十分重視田野調查,他的名作《江村經濟》是他于1933年在他的家鄉江蘇省吳江縣廟港鄉開弦村的田野調查基礎上完成的博士論文。布·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該書“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著名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康藏研究先驅者任乃強先生,他在康區的田野考察是名聲在外。他最長的一次實地考察,時間長達一年余,先后走遍了大半個康區,連續撰寫了十一篇考察報告。他的大作《西康圖經》(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卷本),也是建立在田野考察基礎之上的。他們的田野調查之精神和扎實的功力一直都是我效法的榜樣和力量。
應當說,我在學術上的每一點進步,除了勤奮自學,便是踏實的田野調查了。多年來,我已經十分習慣作田野調查筆記,對于一些頗具代表性的田野調查,我都會寫成調查報告,其中《瀘定摩西石器聞見記》、《魚通公嘛經文目錄》、《明季麗江木氏土司統治勢力向藏區擴展始末及其納西族遺民蹤跡概述》、《白松鄉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狠抓雙語教學,力爭實現普初——康定縣塔公鄉牧區初等教育調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戲及寺廟神舞面具調查》、《貴州省德江縣儺堂戲及其面具文化調查報告》、《黔中安順地戲傳承與發展調查報告》等,反映出我田野調查的一個側面。另外,我的不少專著都是建立在田野調查之上的,例如《德格印經院》[3]、《中國唐卡藝術集成·德格八邦卷》、《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嶺國人物石刻譜系》[4]、《雪域驕子嶺·格薩爾王的故鄉》[5]、《傳承與發展——阿壩州嘉絨藏族織繡研究》、《千碉之國——丹巴》[6]等。
長期以來,我一直十分重視田野調查,強調“從田野中來,到田野中去”。如果要說比較規范的田野調查,也就是指之前有預案,調查比較深入,結束后有調查報告的田野調查。1987年冬,我們一行三人去瀘定嵐安做考察。當時所撰寫的調查報告《瀘定嵐安歷史文化考察瑣記》,至今仍記憶尤深。嚴格的說我的田野考察應是以此為始,至今田野調查的經歷長達三十余年。
在我開始進行田野考察時,我都會將書本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并不斷實踐摸索,在這里與大家分享幾點自己的方法和心得。由于我的研究重點基本都在藏族歷史文化方面,所以,五省五藏區便成為我常來常去進行田野調查的地方。尤其是在我的家鄉甘孜藏區。許多地方我都做過反復多次的調查。例如德格縣,我一共去過不下20次,其中光德格印經院,德格八邦寺我都分別做過5次以上的調查。丹巴是我長期考察的地方,也是我進行田野調查的地方,記得那時我剛剛參加工作,還是“文革”之前的1966年初。改革開放后,我在丹巴考察過那里的嘉絨藏族,羌族遺民,考察古碉的次數最多,大約也有20次之多。本世紀初的10余年間,我把研究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格薩爾圖像方面,所以去考察的地方大都在海拔3500米——4500米的半農半牧區和純牧區。例如去丹巴莫斯卡牧區考察格薩爾石刻,騎馬翻越海拔約5000米的金龍山,我連續去了兩次。去海拔4000米的石渠,兩次考察“巴格嘛呢墻”和“松格嘛呢城”。去海拔4000米的色達考察那里的格薩爾文化,達3次之多。在甘孜藏族自治州18個縣中,除了前面所列舉的縣份外,其余所有各縣都留下了我的考察足跡。說實話,我外出做田野的次數和時間要比別人多一些,吃的苦,受的累也比別人多。有的記者在其文章中,把我稱作“曠野教授”。家鄉的同行們管我叫“穿山甲”。一句話,我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吃過的苦的確不少,但是,我從中嘗到的甜頭和得到的滿足感也是成正比的。因為它和自學一道,共同成就了我這一生的事業。
若要我談談田野調查的心得,簡短的幾句話是很難說清楚的。首先,在進入研究生學習階段,社會學科大都要學習社會調查(包括田野調查)和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這是進行田野調查工作的基石。其二是在田野調查之前,應作好前期預案工作。預案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方面要通過網絡,或是在圖書館查閱相關的資料和曾經的一些研究成果,這方面的準備做的越充分,那對之后的田野考察和幫助就會更大。另一方面就是要做好調查提綱。調查提綱力求能夠細化一些,所涉及的范圍更寬泛一些。其三才是實地田野調查工作。田野調查方法在不同的教材中,不同的專業各有差異,但最基本的實地觀察法、深度訪談法、問卷調查法等都是必用的方法。無論哪種方法,都要在實際調查中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在調查中,眼勤、嘴勤、手勤、腿勤、腦勤。所謂眼勤,就是多看,多觀察;嘴勤就是多問,多啟發;手勤就是多記筆記;腿勤,就是多走動;腦勤,就是多去思考,多提問題。當天的事,當天必須了結。不留尾巴,并做好考察日志。
至于一些具體的個人的考察心得,主要有以下三個方法比較管用。第一是拉網法。簡而言之即為當你到達考察點后,在完成基本調查以后,把當地突出并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做一個收集,記錄在冊,把全部內容鋪開形成一張信息網,保存下來。可能在幾年后你會發現這些相關資料會對你的研究產生相當大的幫助。為什么呢?因為當我們在初學的時候,尤其是研究生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很容易遇到一個理論和實際結合不好的問題,由于我們的知識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沒有實際經驗,當地很多文化現象,在當時的情況下你可能認為跟你研究的問題不相干,所以經常會被忽略掉。但是恰恰這些內容就可能成為你的知識庫中的財富,使你今后受用一生。所以我們要將所有信息由點及線、由線及面,建構知識體系,并從中中找到你的突破點,建立自己的知識網絡,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搞研究不能僅靠到網上尋找資料,更應該到田野中去,視野要開闊,這個方法很管用。沒有田野,沒有一件件的實地調查的資料,是不可能呈現一個系統的成果。我們收集信息,先把精華提取出來做,不是精華的部分也不要把它當作糟粕,往往金子就是在這里面發現的。
第二是聯系法。所謂聯系法就是指當我們調查任何人,任何事物,任何物體時,絕對不能只局限在其自身上。我們應該將周圍的人,事物,物體統統加以觀照,與其周邊的文化環境,生態環境普遍聯系。我在丹巴縣調查梭坡古碉時,聽聞丹巴有格薩爾石刻的消息。最初我是抱有懷疑的態度的。我心中有幾點疑惑:首先書上從未有過記錄記載此處存在格薩爾石刻;其次從自然環境上來講,丹巴是農區,傳統意義上如果有石刻也應存在于游牧地區。當我調查時,發現原來此處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農區,而是高山牧場。當地老鄉的語言也并不是丹巴方言,而是安多方言。并且當地寺院是寧瑪派寺院,寧瑪派有格薩爾信仰。如此一來莫斯卡這里出現了格薩爾石刻就從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變成了意料之中且合情合理的事了。
第三是寫好田野調查報告。田野考察報告是田野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環,更是田野調查成果的集中體現。它以書面文字的形式,分別將田野調查的目的、方法、過程、主要收獲和結論集中展現出來。它既可以說就是一篇調查研究論文,也可以將其中許多收集到的材料,直接運用到論文和專著中去。調查報告撰寫的質量好壞往往影響到田野考察工作的成果。同時,調查報告寫多了,思維能力也就會隨之提高,寫作能力也就會不斷得到加強。我們學社會科學的同學,對于田野考察報告的撰寫一定要多煉多寫,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本功,千萬不能偷工減料。我自己在這方面,付出了許多,也嘗到了甜頭。
回首我的學術之路,無論在藏區建筑、藏傳繪畫、面具文化和格薩爾圖像文化的研究中,許多成果都是建立在田野調查之上。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與《格薩(斯)爾》圖像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后,在研究資料十分奇缺的情況下,田野調查成為了開展《格薩(斯)爾》圖像研究的重中之重,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我越來越感覺到,田野調查仿佛已經成為了《格薩(斯)爾》圖像研究的生命線,研究工作每進一步,都離不開田野調查的艱辛與積累。自1999年至今的近20年時間里,在《格薩(斯)爾》圖像文化的研究十分薄弱,資料十分奇缺的情況下,我先后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昌都市,青海省的玉樹州和黃南州、西寧市,甘肅省的甘南州、蘭州市,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壩州等藏區進行了較多次數和較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尤其是在四川甘孜州地區。本人后來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專著,都是在文獻資料奇缺的情況下,完全依靠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形成的。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感受社會,接觸社會,并得到了極為寶貴的收獲。我認為只有走向田野,進行田野調查,才能搜集到珍貴的、鮮活的第一手材料,得到新知識,填補空白領域,從而定論未定論的觀點。
訪談者:楊教授,您對格薩爾圖像文化頗有研究,并且是我國格薩爾圖像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您能否和我們談談您格薩爾圖像文化二十年求索的經歷?
楊教授:關于《格薩爾》圖像文化的研究,是我較長時期以來一直十分關注的藏族歷史文化研究內容之一,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二十年時間了,前十年中我與格薩爾圖像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并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礎,經過后十年的思索我們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團隊,這將對格薩爾圖像文化的理論化+數字化的新型圖像學研究發展模式產生較大的推動作用。
我年少時期就曾聽到過家鄉老人們講《格薩爾》的故事,對格薩爾王也有一些印象。但對《格薩(斯)爾》圖像文化的了解卻是1987年以后的事。1987年,我到四川甘孜德格縣印經院進行首次調查,在那里第一次看到藏于院內的兩幅格薩爾王木刻版畫,應當說,這是我的學術視域中所看到的第一幅《格薩爾》的圖像。
1999年,我去到德格阿須草原,參加了盛大的格薩爾王紀念館重建落成開光典禮。修葺一新的格薩爾王紀念館,給我最深刻、最難忘印象的是殿堂內雕塑的嶺·格薩爾王及其嶺國眾將領,以及妃子們共49尊姿態各異,栩栩如生的彩色泥塑像。開光結束后,我找到了格薩爾紀念館的倡建者巴伽活佛,請求是否可以讓我為格薩爾塑像拍照,活佛應允了。這是我正式地第一次面對面地觀看和拍攝格薩爾泥塑像并通過藝術視角方式的親身感受。
2001年夏,我第二次來到阿須草原,再次領略了紀念館中的格薩爾雕塑的藝術風采。在返回的路上,我還去了寧瑪派著名寺廟竹慶寺。在竹慶寺考察過程中,聽說該寺歷來有格薩爾藏戲演出傳統,于是頓生拍攝格薩爾藏戲面具的念頭。經過多方努力,終于將嶺·格薩爾王,嶺國三十員將領和八位女士,還有十三威爾瑪護法神共四十多具面具形象也收錄進了我的鏡頭。
在此之前,對于《格薩爾》圖像我沒有涉足過,看過的書也十分有限,自然對它的關照非常少,更談不上研究了。但經歷以上兩次考察以及我所得到的的收獲,加深了我對格薩爾的印象,特別是對其圖像藝術,找到了感覺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開始著手研究和學習相關的研究成果和一些理論書籍給自己充電。
2003年,我在丹巴莫斯卡發現的《格薩爾》嶺國人物石刻譜系的石刻,是格薩爾圖像中的一個全新的類型形式,拓展了格薩爾圖像文化的內涵和新領域,這對我的觸動,要比之前在德格阿須和竹慶的考察深得多。同時,也提升了我對格薩爾圖像的認識,給了我新的啟迪。我開始從理性的角度思考,格薩爾圖像究竟包括哪些類型?是否應當對格薩爾圖像文化做一個歸納,并由此產生“格薩爾圖像文化”的理念。5月,我們合著的《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薩爾王傳>嶺國人物石刻譜系》一書問世,得到了學術界高度評價。著名格薩爾研究專家降邊加措認為這項成果是“21世紀有關《格薩爾》的重大發現”,“是一項填補空白之作”。
不久后,我又得到一個新的信息,在色達縣色爾壩的雅格寺也發現了格薩爾石刻;我認為丹巴縣莫斯卡《格薩(斯)爾》嶺國人物石刻譜系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格薩爾文化流傳范圍極廣,可能其他地方還會存在類似的石刻,我個人認為其重點應在牧區。我先以四川甘孜藏區作為基點,來開展調查和研究。因為甘孜藏區是格薩爾文化的核心區之一,近年來,我所考察的格薩爾圖像之地,大都在這一區域內,有一定的基礎和積累;我本人又是這一地區的人,多數研究工作都是針對這一地區的,所以,除格薩爾文化之外,其他方面的文化研究工作做了不少,歷史情況、社會情況、地理情況、宗教情況都較熟悉,這些,都是可與格薩爾圖像融會貫通的。鑒于精力、人力、物力諸方面的不足,不可能一下子把圈子扯得太大。飯只能一口一口吃,任何事情都要由小及大,不可能一蹴而就。
從2004年到2008年的5年間,我利用其他研究項目的外出調查機會,先后去了甘孜藏區的石渠、甘孜、德格、理塘、道孚、爐霍、新龍、雅江、鄉城、稻城、丹巴、白玉、乃至青海的玉樹等藏區,均不同程度地收集到了一些有關格薩爾文化方面的資料,至于格薩爾圖像方面的收獲,則主要是在石渠和色達、德格等地獲得的。
2004年10月和2005年7月,在兩次石渠考察期間,我不僅在松格嘛呢城和巴格嘛呢墻發現了數量較多的格薩爾石刻,還看到了其他嘛呢墻中的格薩爾石刻。同時,在石渠和色達、甘孜都看到了至少可以證明是清代的格薩爾唐卡,還看到了極其珍貴的古壁畫。
我在石渠宜牛寺第五世活佛四郎仁欽那里看到一幅老的唐卡,這幅唐卡畫面長62厘米,寬48厘米,是一幅嶺·格薩爾王騎征圖,其特別之處在于唐卡中嶺·格薩爾王的面部造型與眾不同,其額上開有天眼。這是我多年來看到的唯一一幅開天眼的嶺·格薩爾王的唐卡。關于嶺·格薩爾王開天眼之說,在《格薩爾王傳——英雄降生》[7]中是有所描述的。
2006年,我從成都出發,直奔色達草原。經過10多天的考察受益匪淺。在我總結的格薩爾圖像藝術類型中,應當說大多都得到了充實。特別是雕塑、壁畫、石刻、唐卡4種類型的格薩爾圖像藝術,使我大開眼界。
就雕塑而言,我去了四處地方。在色達縣格薩爾文化博物館中看到了由色達縣文化館館長班瑪交先生設計塑制的一組4尊嶺·格薩爾泥塑像。塑像制作精美,形態各異,據說他是按照局·米旁大師“格薩爾大師金剛長壽祈請頌”中所寫的內容創作的。此外還設有一個格薩爾雕塑的專門展廳,廳中陳列嶺·格薩爾王、妃子珠牡、列窮和嶺國眾將領的木雕像。在格薩爾博物館和泥朵、色爾壩等地,都還有數量相當的格薩爾彩繪石刻。
在多年的研究中,我先后發表論文《松格嘛呢——格薩爾的寄魂城》《石渠格薩爾文化探索之旅》《格薩爾造型文化論綱》《格薩爾圖像藝術的新開拓》《格薩爾圖像的基本類型》《<格薩爾千幅唐卡>繪制紀實》《關于英雄史詩主人公嶺·格薩爾王是否有原型的討論》《一部展示偉大史詩<格薩爾>的精美畫卷——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唐卡述評》。出版的專著為《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薩爾>嶺國人物石刻譜系》《雪域驕子嶺·格薩(斯)爾的故鄉》《西藏格薩爾圖像藝術欣賞》(上、下)[8]。在我發表的格薩爾圖像研究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格薩爾造型文化論綱》,該文是作為參加在昆明召開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十六屆大會“格薩爾文化研究”專題而撰寫的,可以說也是本人十余年開展《格薩爾》圖像研究的一個學術基本總結。全文約3.5萬字,是此次大會中格薩爾文化專題中最長的一篇論文。文章總共分四個部分來展開研究:即一是格薩爾文化解析;二是格薩爾造型文化研究的基本基礎;三是格薩爾造型文化的新拓展;四是格薩爾文化解析和格薩爾造型文化類型系統架構的理論依據。其中基本類型傳統造型文化的基本特點兩部分是文章的重點,也是本人后來所形成的格薩爾圖像文化概念的重要內容。在格薩爾文化解析中,我認為格薩爾文化這個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眾多學者通過對《格薩爾王傳》(以下簡稱《格薩爾》)不斷發掘、收集、整理的基礎上,在《格薩爾》史詩地位被確立的前提條件下提出的。
按照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的基本定義,格薩爾文化應是這部史詩精神與物質兩個文化層面的總和,同時也是這兩個文化層面歷史與現實的全部。《格薩爾》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被世人公認的“世界上最長的并以活性態存在”的史詩,充分證明了《格薩爾》及其他的主要創作者、傳播者——說唱藝人在格薩爾文化體系中的主體地位。《格薩爾》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對其他文化的滲透,似乎也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所以,就具體文化事項而言,它不僅包括《格薩爾》及其說唱藝人、還包括與《格薩爾》相關的傳說故事、遺跡遺物,也包括與《格薩爾》相關的造型文化、民間民俗活動和宗教活動,包括近現代以來在國際國內興起的‘格學’研究等等。在上述文化事項中,《格薩爾》及其說唱藝人是格薩爾文化的主體,其他文化事項均是在這個主體文化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派生性文化。如果將這些派生性文化比成‘毛’,那么《格薩爾》及其說唱藝人則是‘皮’。在‘毛’與‘皮’之間,既存在著源與流的關系,同時又存在著相輔相成和交相輝映的關系。在《格薩爾》在眾多派生性文化中,格薩爾造型文化以它特有的藝術語言、視角特質為格薩爾文化增添了奪目的藝術光彩和無窮魅力。這個觀點在當時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同,并成為后來格薩爾圖像文化中“語圖關系”的核心觀點。
在與格薩爾文化結下的前十年情緣的過程中,我初步總結了格薩爾圖像文化的兩個重大內容:首先我們發現了過去從未見過的類型形式,加深了對格薩爾圖像文化的認識,豐富了格薩爾圖像文化的內涵,對格薩爾圖像文化的理解上升了一個高度。 其次我們通過扎實嚴謹的田野調查和搶救工作對格薩爾圖像類型形式做了概括和說明,延伸了格薩爾圖像文化的外延,即在數字時代通過現代化手段建立健全格薩爾圖像文化系統,并為后期“英雄史詩《格薩(斯)爾》圖像文化調查研究及數據庫建設”的申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此后的十年里,我時常陷入深深的思考。眾所周知,英雄史詩《格薩爾》在我國藏區產生已逾千年,它是當今世界卷帙最為浩大、最具生命力、至今依然活態生存于世的偉大史詩。國外學者,最早從公元18世紀80年代就開始接觸到并開始研究蒙文本的格薩爾史詩。隨著《格薩爾》在國內的不斷發展和國外的傳播,目前已然在國際上逐漸成為一種發展態勢,并形成格薩爾文化(或稱史詩傳統)的核心組成部分。綜合國內外關于《格薩爾》圖像研究的發展歷史及其研究內容而言,早期的研究成果是比較少的,一直都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格薩爾文化的主體,是其文本和說唱藝人,所以一直以來,學界都把研究的目標集中在這個主體之中,這是毫無疑慮的。二是就圖像本身而言(這里主要指藏族工巧明之中的傳統繪畫與雕塑),由于自藏族形成以來,宗教文化便成為藏族社會中的核心文化之一,所以藏傳繪畫與雕塑中所體現內容自然也就是大量的宗教藝術作品,并存在于廣袤的藏區土地上,需要我們既耐心又細心地去尋找和探尋。
在前十年里,對格薩爾圖像的探尋和研究都是自己一個人在探索著。在年過半百的時候發現了格薩爾圖像的新類型格薩爾石刻,填補了一項空白。隨著自己年紀的增長,以及格薩爾圖像文化的框架逐漸清晰,尤其在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格薩(斯)爾》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后。我深深地感到,繼續深入開展《格薩(斯)爾》圖像的調查研究,已經不再是個體的行為,而是一種義不容辭的歷史擔當。自2012年至2017年我本人所參與的有關格薩爾圖像研究方面的項目主要有以下兩項,一是于2012年參加了由中國文聯立項,中國文聯文學藝術基金資助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百科全書·史詩卷格薩(斯)爾、江格爾、瑪納斯》的編寫,《格薩(斯)爾》史詩的藝術部份由本人撰寫。二是于2015年底在學校民族研究院和科技處的關懷和支持下,申請了“我國藏區格薩爾圖像文化研究”項目,經評審獲批為西南民族大學2016年立項的中央高校基本業務經費專項資金項目國家重大項目孵化項目,本人為項目責任人。這個項目的立項為2017年我們成功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英雄史詩格薩(斯)爾圖像文化調查研究及數據庫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2008年后至今的十年期間,經過反復的學習和思索,結合本人的實際情況,結合學術研究領域的不斷創新,通過對學校批準的中央高校基本業務經費專項資金項目《我國藏區格薩爾圖向文化研究》的研究實踐,我對格薩爾圖像的研究開始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和轉變,也找到了突破口。我從過去的個人單打獨斗的研究行為轉變為組建一個高學歷、適齡、知識結構合理的團隊,組建了由民族學、民俗學、歷史學、藏學、計算機技術多學科人才組成的團隊;將以理論化與數字化相結合,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為目標,利用多學科方法交叉研究并建立格薩爾圖像學研究基本框架的方法;為今后《格薩爾》文化的其他研究提供范例,為數字時代格薩爾圖像文化的發展提供依據,在當代條件下為格薩爾圖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找到途徑。通過學校兩年來的項目孵化,我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立項批準,這一方面從客觀上證明了我20余年來對格薩爾圖像文化的執著追求所換來的一個新的擁有,另一方面又暗示著,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又一段艱辛的征程即將開始。
楊嘉銘教授幾十年如一日堅守信念,不忘初心。唯愿行到高處,楊嘉銘教授將自己個人置身事外,將社會、把國家利益放在最高處,這種嚴謹的學術態度和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我們為之動容,也極其值得我們后輩學者借鑒。
采訪結束,走出楊教授的家,已是萬家燈火。通過短短時間與楊教授的接觸,我們每個人都被教授巨大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楊教授對我們后輩學生和藹可親的態度,認真地傾聽和耐心地回答使我們對學術研究,田野調查及格薩(斯)爾圖像藝術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并使我們學到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在今后的學習生涯中增強了自信心。我們不禁開始思索,讀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曾經的我認為讀書是對自己學識和能力的提高,對親人培養的回饋。經過對楊教授的采訪后,我的想法發生了巨大的轉折。一個為理想和事業幾十年如一日的信念堅守、為挽救優秀民族文化的勇敢擔當、為立足于貢獻社會的博大胸襟的前輩,深深地感動了我們。我們讀書不應僅僅立足于個人的發展,而更應當向楊老學習。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孜孜不倦,提升自己的學識、品德,讓自己真正做到有能力為社會、國家和廣大人民做貢獻。并在這個過程中,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這份初心,我也會始終銘記并一直堅守。真正的學問是一條沒有地圖的旅程,需要我們去摸索探尋。老驥伏歷,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學生們祝愿楊老健康長壽,格薩爾圖像研究事業早成!
[1]楊嘉銘.甘孜藏族自治區民族志[M].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2]馮驥才.中國唐卡藝術集成——德格八邦卷[M].陽光出版社,2011年
[3]楊嘉銘.德格印經院[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4]羅布江村、趙心愚、楊嘉銘.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薩爾王傳》嶺國人物石刻譜系[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2004年獲四川省第十一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5]楊嘉銘、趙心愚.雪域驕子嶺·格薩(斯)爾的故鄉[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2004年獲第五屆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三等獎
[6]楊嘉銘, 楊藝. 千碉之國――丹巴[M].巴蜀書社, 2004年
[7]佚名.格薩爾王傳——英雄降生(藏文)[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
[8]楊嘉銘、楊環、楊藝.西藏格薩爾圖像藝術欣賞(上、下)[M].臺灣山月文化有限公司,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