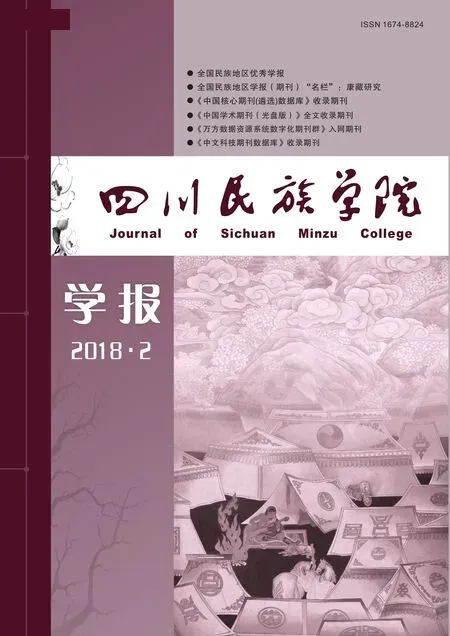淺析那彥成對青海藏區的治理
周先吉
那彥成(1764~1833),字韶九,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大學士阿桂之孫,號繹堂,晚號更生,謚文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進士,為官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三督陜甘,兩督直隸,一督兩廣,兩署巡撫,是清中期一位重臣和著名疆臣,在他受命出任西寧辦事大臣及陜甘總督期間,基于當時青海地區復雜的情勢,尤其在處理蒙藏民族問題方面,有效地實施了一些管理舉措,值得后人在相關問題上引起重視。
一
清朝是我國第二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封建政權。清王朝在建立初期非常重視包括甘寧青地區在內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一方面沿襲元、明兩代有效的治邊政策;一方面根據“因俗而治”和“分而治之”的基本方針,采取和制定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行政管理體制。尤其在清朝初期,調整其統治策略,在總結前朝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于藏區推行了有利于國家統一的民族宗教政策,對藏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以及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明末清初,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勢處于從政治多元走向地方統一的局面。是時,藏傳佛教格魯派興起并迅速發展,呈后來者居上之勢,這引起了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勢力的排斥和打擊,為此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權和教派之爭。明萬歷四十年(1612),藏巴汗統治了前藏絕大部分地區,成為當時西藏歷史上一個較大的地方政權。到17世紀30年代,藏巴汗政權與占據青海的喀爾喀蒙古卻圖汗以及康區白利土司三方因共同反對格魯派而結為聯盟,從東、北、西三面包圍格魯派,格魯派的形勢岌岌可危。此時,駐牧于天山南麓的蒙古碩特部汗王固始汗,受到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與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的援請,率兵進入青海、康區、西藏,最終消滅了卻圖汗、白利土司、藏巴汗的勢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格魯派在西藏社會中取得了絕對的優勢,并建立了“甘丹頗章”政權。至此,固始汗統一了西藏地區,將軍政大權掌控于自己麾下,為其后清朝管理當地提供了前提條件。
順治九年(1652),五世達賴喇嘛偕四世班禪抵達北京朝覲。翌年在返回西藏途中,清廷賜五世達賴喇嘛金冊金印,確認了他在蒙藏地區的宗教領袖地位。隨后,清朝派遣使臣前往西藏,對固始汗進行了冊封。事實上,清朝在冊封五世達賴喇嘛的同時冊封了固始汗,既支持五世達賴喇嘛在宗教領域弘傳佛法,又敕封固始汗“作朕屏輔”,間接對青海、西藏地區進行行政管理。清政府對達賴喇嘛、固始汗的敕封強化了對西藏治理。在其后過程中,清廷繼續推崇藏傳佛教、優禮格魯派高僧大德,以此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即“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1]不僅如此,清朝在中央設立了“專管外藩事務”的理藩院,在地方建立了治理西藏的機構和制度,首先是在蒙古汗王掌管的地方政權下,由第巴·桑吉嘉措管理地方政治事務;其后于康熙五十九年(1721)廢除汗王和第巴制度,同時決定設立由四位噶倫聯合掌政的噶廈政府,共同管理西藏事務。由此表明,清朝不再封授和碩特汗王,也不再承認和碩特蒙古對西藏的統治,轉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噶廈地方政府,這使得羅卜藏丹津重新統治西藏的幻想破滅。羅卜藏丹津是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之子,他一心冀希恢復祖先在西藏、青海等藏區的“霸業”,最終釀成兩年后(1723)在青海公開發動叛亂。這次叛亂歷時不足八月,很快就被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率兵戡定,但其影響極其深遠:“及雍正元年,王師平羅卜藏丹津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斯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門剌麻[喇嘛]旗各自為部,不得復為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西寧辦事大臣涖盟。自后青海始同內地,漸削弱矣。”[2]它直接導致了清政府治藏政策的變化,對青海藏區的治理也在此時出現了轉折。
17世紀40年代,蒙古和碩特部汗王曾于西藏、青海建立統治,是時,青海各藏族部落“惟知有蒙古,不知有廳衛營武官員”[3],大都納于和碩特蒙古的統治之下。鑒于蒙古族在青海的強大勢力,清初中央政府對當地蒙藏民族采取“抑蒙扶藏”的基本政策,以限制和打擊蒙古勢力。雍正二年(1724),羅卜藏丹津叛亂被平定,清廷當即實施善后措施,制定并頒行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條》 《禁約青海十二事》等。翌年(1725),又在西寧特設“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簡稱“青海辦事大臣”(后統稱為“西寧辦事大臣”),管理青海政治、軍事、各部會盟和茶馬互市等事務,成為清代主管青海蒙藏事務的最高軍政機構。從此,結束了蒙古汗王對青海的統治。
二
清政府為加強對青海的治理施行了一系列辦法和措施,加強了對蒙古諸部的管理,設立盟旗制度:“分其旗分,編為佐領。各管各屬,定有分界,”[4]每百戶設一佐領,并嚴格劃定各旗游牧邊界。此后,又設祭海會盟制度,規定各旗每年會盟一次,由西寧辦事大臣主持。緊接著將原歸蒙古汗王管轄的青海藏族部落收歸清廷直接管轄。第一任西寧辦事大臣達鼐在青海藏族地區清查戶口,設立千百戶制度,分別給各部落首領授以土千戶長、土百戶長等職,加強對青海藏族社會的管轄力度。不僅如此,清廷唯恐蒙藏雜處再生事端,明確規定了兩族游牧生活的地界,將藏族大部分限制在黃河以南區域,由千戶長統一管理;而將蒙古劃分到黃河以北以及環青海湖的地區游牧定居。后來由于河南藏族人眾地狹、河北牧場水草豐美,于是,河南諸多藏族部落迫于生計渡河畜牧,導致了本文將探討的那彥成處理藏族部落北渡黃河、駐牧河北事宜。此外,清廷通過羅卜藏丹津事件,充分認識到藏傳佛教的巨大影響,于是下令限制佛教上層政治和經濟勢力的發展,整頓和管理藏傳佛教寺院。為改變青海地區的行政建制,朝廷還將西寧衛改為西寧府,隸屬甘肅省,下設西寧、碾伯兩縣和大通衛。由此說明羅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朝將治藏目光轉移到青海地區,加強了對該地區蒙藏各部落及社會的掌控和管理。不僅如此,有鑒于青海藏族各部落“今日番中一族有千余戶,則其勢浸大,萬一有梟雄糾合數族,則萬眾之聚,實為地方隱憂。”[5]清朝規定將他們全部收歸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按照上述新近頒布的兩條法律條款的規定,清廷于各部落中確立了千百戶長負責制。為確保該制度的順利實施,那彥成再將其細化:“將舊設千百戶,餌以領易糧茶之利,而于所管番人立之限制,令千戶管三百戶,百戶管一百戶,什長管十戶,是千戶之族有三頭人,二千戶之族有七頭人,各領接管,上邀天朝茶糧互市之恩,其勢不肯相下,自必倍加恭順,為我藩籬。”[5]從嘉慶九年(1804)那彥成首次出任陜甘總督,三年后(1807)任西寧辦事大臣,十五年(1820)復任陜甘總督,到道光二年(1822)再以刑部尚書身份任陜甘總督三年有余,在任職期間他針對青海具體問題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一,請將隸屬蘭州府之循化廳改隸為西寧府,便于清廷進一步直接管理青海藏族部落。循化廳成立之初隸屬于蘭州府,由陜甘總督統轄。嘉慶十二年(1807),西寧辦事大臣那彥成會同寧夏將軍興公奎、陜甘總督長齡上奏朝廷,應不拘一格、不限民族成分重用人才:“循、貴兩廳同知,應請不拘[泥]旗、漢人員,以便易于得人也。查嘉慶八年(1803)貢楚克札布等《奏定章程》‘循、貴兩廳同知應用旗員’等語。特以旗員通曉清語,辦理蒙、番事件較為熟諳。第通省旗員無多,此內或人地不宜,或礙于處分,一時不能得人,每至出缺,深費周章。竊以文員辦理地方,但能實心任事,即可措置得宜。如從前貴德同知姜有望系屬漢員,查辦番案出力,曾經賞戴花翎,原不必定用旗員始能練達邊務。嗣后應請循、貴兩廳缺出,但擇人地兩宜之員酌量升調,不必專用旗員。庶易于為地擇人,不致為成例所拘矣!”[6]
此外,道光三年(1823)以前,循化廳和貴德廳分別隸屬于蘭州府與西寧府,管理黃河以南的蒙古族和藏族,自西寧辦事大臣設立之后均歸西寧辦事大臣管轄。凡遇到蒙藏民族事務問題,貴德廳同知就近轉與西寧辦事大臣衙門處理,便捷且迅速。而循化廳則不然,凡事需從蘭州府經轉,耗時耗力十分不便。那彥成再次出任陜甘總督后,為了便于監督、約束和處理蒙藏兩族事務,奏請將蘭州府之循化廳改隸西寧府:“竊查甘肅循化、貴德兩廳,均系理番同知,向歸青海大臣管轄。該兩同知分管黃河迤南番族,凡有蒙、番事件,貴德同知即由該管之西寧府就近核轉青海大臣衙門辦理,甚為便捷。惟循化同知遠隸蘭州府屬,青海大臣檄辦事件,須由蘭州府轉行。西寧距蘭州六百里,蘭州距循化又五百余里,文報往返,已屬需時。而蘭州府又不歸青海大臣統轄,遇事又多掣肘。現在河北番族,全數驅過河南,改設立千戶、百戶、百總,層層鉗制,則以后之稽查約束,更關緊要。該兩同知地界毗連,必須會同辦理,而分隸兩府,勢難期于畫[劃]一。應請將循化同知改隸西寧府屬,一切公事,均由該府就近移轉青海衙門辦理,以免歧異。該廳距西寧郡城僅止二百余里,文移往返,亦可無虞延緩,實于邊務番情,悉臻妥速。”[7]至此,嗣后循化廳一切公事均由西寧府就近移交西寧辦事大臣衙門辦理,循化廳始改隸西寧府,既提高了辦事效率,又為清廷管理循化廳所屬各藏族部落事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第二,清厘黃河以南藏族部落,編查戶口,重申千百戶制度,嚴格管束各藏族部落。以羅卜藏丹津事件為契機,由于青海蒙古族勢力的強大,清廷為了削弱其力量采取“分而治之”、“扶番抑蒙”政策,通過扶持藏族部落來鞏固清朝在該地的統治。根據藏族封建化進程的快慢,清廷將其分為“熟番”、“生番”和“野番”,設千百戶、總千戶進行管制,統統劃歸于清政府管轄。將蒙古分為二十九旗,劃定地界,規定不許私自擴大領地、越界游牧。以黃河為界,實行蒙藏分治,黃河以北及環湖地區為青海蒙古二十四旗的駐牧地,黃河以南除五旗蒙古外,為循化、貴德兩廳所屬藏族各部落的游牧地。如此導致后期青海蒙古族人口銳減,力量衰微。相反,青海藏族部落在脫離蒙古族統治后,經休養生息勢力逐漸發展,從蒙強藏弱變為藏強蒙弱。因初期劃分蒙藏地界的不合理性,藏族部落隨著人丁增長而缺少足夠的牧地,開始徙牧黃河以北地區,蒙藏間矛盾紛爭不斷。早在乾隆時期,河南蒙旗經常遭到循化、貴德兩廳以及果洛藏族部落的攻掠。嘉慶年間藏族部落仍頻頻渡河北移,大批蒙古牧民紛紛避入內地。此時,清廷改變最初的“扶番抑蒙”轉而采取“扶蒙抑番”政策,驅逐北遷的藏族部落,引起了青海蒙藏社會的動蕩不安。而這僅僅是河南藏族部落遷徙之始,其后大規模徙牧河北發生在道光年間。道光元年(1821),汪什代海等河南二十三族藏族部落全部北渡,于青海湖周圍駐牧。此前朝廷雖屢次派遣西寧辦事大臣查辦,但并無明顯成效。道光二年(1822),清廷再命治理民族問題頗富經驗的那彥成“查辦番案”。他決定“先治河南”,著手清查河南各部戶口,照內地保甲一律編查,加強千百戶制度。清查戶口結果為“貴德廳有生、熟、野番三種,熟番五十四族,向來種地納糧,均能謀食生番十九族,住居貴德之東南,畜牧為生,惟野番八族,戶口強盛,內有汪什代亥一族,近已全數移居河北,其余七族,現俱插帳河濱,遠難控制。循化廳有生、熟二種,熟番十八族,生番五十二族,大半皆有糧地。”[8]在此基礎上,那彥成稟旨進一步推行千百戶制度,“分其戶口,每三百戶設千戶長一人。千戶長之下設百戶長、百總、什總。凡百戶長一人每管百戶,三百戶歸一千戶長管理。百總一人每管五十戶,兩百總歸一百戶管理;什總一人每管十戶,五十戶歸一百總管理。”[5]將藏族各部落更進一步納入清廷的直接管轄下。
第三,規定藏族易買糧茶章程,整頓貿易。青海藏族部落本無類似章程,由此,那彥成首先規定藏族依照蒙古之例請票易買糧茶,由戶口多少分食,請票均由各族千戶長在循化、貴德兩廳代領后,才能購買糧茶,照票每年準買兩次。“若有不遵法度之人,即不準領票。至所必須之布、線 、靴帽、木碗之類,亦于票內注明,一同換買”[8],在事關牧民的糧茶貿易方面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其次,開設歇家,制定相關制度。歇家在民族貿易中既充當著商務代理人的角色,還為官府督收差稅。清中后期,歇家積弊日益增多,那彥成等不僅封禁各地私人歇家,還將西寧、大通、循化、貴德、丹噶爾等地的官方和私歇全部造具花名冊,由官經管,并且“另立循環印簿,每歇家兩本,將逐日來店住宿之蒙、番詢明何事進口,所來何貨,所換何物,詳細填注簿內,”[5]并規定每月呈報衙門。再次,規定固定貿易點與交易期。清代,商民前往青海蒙藏地區易買羊只貨品的稱“羊客”。為進一步規范羊客與蒙藏部落間的交易,那彥成等將貿易點定于“應請嗣后毋論何州、縣羊客與河北蒙古買羊易貨,止[只]準在于西寧縣屬日月山卡以內東科爾寺、丹噶爾及大通縣屬之烏什溝、察漢俄博等處,互相交易。其河南蒙古、番子羊只、貨物均在貴德廳屬之西河灘售賣,該羊客不許經赴蒙、番游牧處所牧買,致滋流弊”[5],并規定每年四至九月為交易期。
第四,規定玉樹藏族馬貢折銀請仍循舊例交納,取消主事、通丁征收貢馬銀。清朝建立之初,青海各藏族部落仍受蒙古族統治。長期以來,蒙古貴族對藏族部落收貢“并無定數,任其增減,索取無休,以至眾心不服”。[9]羅卜藏丹津事件被平定后,清廷冊封各千百戶,開始向玉樹各部落征收賦稅,實行貢馬銀制度。清廷規定,每百戶需要繳納馬1匹,每匹馬折征白銀8兩,不足百戶者,每戶征銀8分。原議該部落首領自赴西寧交納。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政府改派通丁每年到玉樹等地各藏族部落催收,或由當年會盟之主事征收。但“通丁出口往返數千里”,并“任意攜帶貨物并私帶買賣客商……計其往返之期,總在半年以外”。[5]主事者也同樣弊端種種,他們“私備布匹等物致送番族,名為土儀,因得受番族饋送,薄往厚來。是正供不過六百余兩,而蒙番所費,實十倍正供不止”。[5]道光二年(1822),那彥成三任陜甘總督之時,鑒于上述弊端上奏建議“所有此項貢馬折銀應請仍循舊例,責令該總管千、百戶等如數湊齊,于每歲九月間交該處貿易番目自赴西寧交納”。[5]從此,“其主事、通丁之例,永行停止”,切斷了通丁與主事盤剝黎民,從中牟利的敲詐欺壓行徑,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玉樹藏族部落及當地藏胞的經濟負擔。
三
清朝對青海藏區的管轄從最初的無暇顧及到雍正年平定叛亂為轉折,開始了大規模的整飭治理,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清中央政府憑倚著振興格魯教派的政策,與青海各部藩屬建立關系;為削弱和碩特勢力,長期采取了“扶番抑蒙”政策。其后又加大了對西部藏區的治理管控力度,于雍正三年(1725)設置西寧辦事大臣,專管青海蒙藏事務。為此,在藏族部落中分封千百戶等職,籠絡部落頭人,支持藏族部落的發展,千百戶制度的正式確立維系了清中央政府與藏族各部落間的關系。有清一代,對青海地區的藏族部落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法,根據部落情況相應地從行政、法律等方面對青海藏族部落進行管轄,整體來說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
那彥成曾經三任西寧辦事大臣及陜甘總督,他任職期間恪盡職守,在施政、經貿、人口管理等幾個方面制定和完善了章程,維護了清王朝在當地的實際統治。總體來說,那彥成管理青海藏族部落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也有弊。第一,在河南藏族部落徙牧北遷之時,通過統計人口并實行了千百戶制度,將青海藏族部落納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控之下。這一制度雖然取得了暫時的成效,在一段時間內鞏固了清朝對青海藏區乃至西北地區的統治,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黃河以南藏族部眾人多地小的問題,導致他們近一個世紀持續的北移活動,最終于咸豐年間形成了今天所謂的“環湖八族”。在這次徙牧河北的過程中,清廷與藏族部落可謂兩敗俱傷,朝廷多次委派大臣“查辦番案”,但均無成效,且勞師傷財,而北移的藏族也多次遭到清軍的武力鎮壓,損失慘重。不僅如此,徙牧河北也使蒙藏兩族間關系變得更緊張,甚至形成了長期對立狀態,不利于民族地區的團結和穩定。第二,加強千百戶制度,青海藏族部落脫離蒙古部族的統治由西寧辦事大臣管轄,一方面有利于清朝的治理,達到分而治之、平衡蒙藏力量,穩定了青海地方社會的目的;而另一方面,朝廷削弱和分化了當地藏族的力量,從而使千百戶們各自為政,彼此紛爭,對藏族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消極作用。第三,歇家的出現以及青海蒙藏貿易制度章程的制定和完善,不僅為藏族商人的貿易來往提供了便利,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藏族人民的權益,減輕了其經濟負擔,還使清廷對民族經濟貿易的管理加以強化。尤其通過那彥成的整頓吏治,使青海民族經濟貿易進入有清以來的繁榮時期。但因嚴格限制藏族牧區經商活動,章程規定僅可以在固定的地點和時間內互相以物易物的等等禁令,在一定程度內,妨礙了各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往來,阻礙了民族地區社會的發展。
那彥成是嘉道時期的一位重要的疆臣,他對青海地區的民族事務進行了深入且細致的調研,也進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管理,這在清代蒙藏史上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評價其青海施政舉措,需要我們客觀地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考量,作為清王朝顧命西北的一位封疆大臣,他的所作所為受階級利益和歷史環境所限。一方面,他實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民的負擔,客觀上促進了當時青海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是,其奉行的還有一些措施,是清王朝為鞏固封建統治而進行民族壓迫的表現形式,這些源于階級的本性和立場,對此本人不能茍同,應予以否定。
[1]清實錄·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轉引自北京雍和宮《御制喇嘛說碑文》
[2][清]魏源.圣武記.卷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p112
[3]清實錄·世宗實錄.卷二十[M].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p26-30
[4][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十八,武備志·青海[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p531
[5][清]那彥成.平番奏議.卷四.上絳堂尚書論番事書[Z].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p395、p395-396、p160、p45、p221、p173
[6][清]那彥成.那彥成青海奏議[Z].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p69
[7]鄧承偉等.西寧府續志.卷九.藝文志·陜甘總督那彥成請將理番同知改隸近番府屬疏[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410-411
[8][清]鄧承偉等.西寧府續志.卷九.藝文志·陜甘總督那彥成清厘河南番族編查戶口疏[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403、p406
[9]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十六.田賦志·塞外番貢[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p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