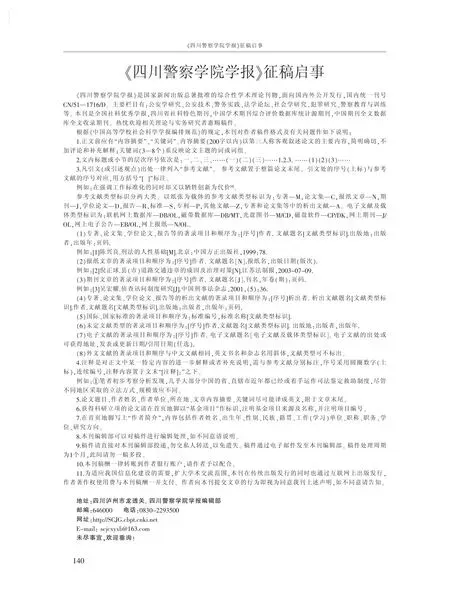社會心理學視域下的農村滅門慘案解析
——以婚姻家庭糾紛引發的滅門慘案為視角
馬李芬,呂 堯
(四川警察學院 四川瀘州 646000)
這些年來,關于滅門慘案,尤其是農村滅門慘案的信息頻頻出現在網絡或報端。滅門慘案雖然只是一個的個案,我們不能危言聳聽。但它卻折射出社會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同時,這些案件如果不能及時得到遏制,很可能發生蝴蝶效應。因此,對這類案件值得深入研究并有效防范。
一、農村滅門慘案的規律、特點梳理
(一)農村滅門慘案發案的地點與時間呈現一定的規律性
農村滅門慘案大多發生于經濟欠發達的我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如河南、安徽、寧夏、青海、云南等地經濟較落后的鄉村。發案的時間多在春節前后或春節期間。基于婚姻家庭糾紛引發的滅門慘案,發案時間大多在春節這段時間,有的甚至就發生在除夕。春節期間,城市單位放假,農村外出務工人員返鄉,走親訪友、喝酒賭博,經濟開銷陡增,往往成為矛盾的根源。滅門案的直接動機是仇恨,報仇泄恨,而仇恨的來源正是沖突和矛盾。犯罪嫌疑人選擇春節這樣特殊的時段,主要原因是為了達到最大的心理報復感——別人家過年,你們家得辦喪事。
(二)農村滅門慘案手段殘忍
在滅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幾乎沒有使用相對平緩的方式,作案的手段都極其殘忍。從作案的方式看,有的縱火,有的使用利斧、砍刀等冷兇器,有的甚至使用獵槍、半自動步槍。比如,2014年1月30日發生在云南省騰沖的慘案中,犯罪嫌疑人邵某用疑似半自動步槍接連打出了24發子彈,擊中9人,導致5人當場死亡,1人送往醫院途中死亡,另有3人受傷[1]。從造成的損害來看,現場血跡斑斑,受害者傷痕累累。從侵害的對象看,受害者有小到一兩歲的嬰幼兒,大到耋耄之年的老人,有的案件中,甚至孕婦也未能幸免于難。有的犯罪嫌疑人甚至對自己的至親都下手屠殺,手段殘忍、血腥,令人觸目驚心。
(三)犯罪嫌疑人多為性格較內向的中青年男性
青壯年時期,精力、體力較好,報復性較強。滅門案的犯罪嫌疑人給人的印象往往是很老實的人,性格內向溫和,平時言語不多,很少與他人發生爭吵。比如,2013年10月14日發生在寧夏固原的滅門案中,犯罪嫌疑人麻某在外人看來是“模范老公”,與妻子發生爭執,通常會讓步[2]。
(四)犯罪嫌疑人多與被害家庭存在家屬或者親戚關系
在農村因婚姻家庭糾紛引發的滅門慘案中,犯罪嫌疑人與受害人要么是親戚關系,要么是親屬關系。如,2013年2月23日發生在江蘇連云港東海慘案中,犯罪嫌疑人楊某殺害的就是其妻子、岳父母及妻姐[3];前述云南騰沖案中,犯罪嫌疑人邵某用疑似半自動步槍擊中9人,導致5人當場死亡,1人送往醫院途中死亡,另有3人受傷(殺害的是妻子的同宗兄弟)[4];2013年3月12日發生在安徽省鳳臺縣滅門慘案中,51歲的父親(朱敬四)殺害的是小兒子一家……[5]。
二、農村滅門慘案頻發的背景及成因探討
蘭州大學副教授申端鋒認為,當前的中國農村社會正在經歷一種新的轉型之痛,即價值觀轉型之痛[6]。價值觀逐漸偏離原來的軌道,誠信、友善的價值標準逐漸被物質利益至上、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替代,加之亞文化所帶來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攀比之風盛行,這些消極的價值觀在信息時代被飛速傳播。
(一)心理障礙或精神問題
在自由競爭的市經濟體制下,原本血氣方剛的中青年農民,卻因一缺文化,二少技術,三沒人脈而變成了弱勢群體,面對巨大的貧富懸殊、經濟的拮據,難免失衡,變得浮躁,滋生暴戾心理,出現心理障礙或精神問題,他們在言行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失調性,情緒情感管理也易失控。正如,2009年11月16日發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烏蒙鄉烏蒙村殺死父母、伯父母、奶奶和堂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陳文法曾被醫院確診有精神分裂,被害妄想嚴重[7]。2009年12月發生在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高明鄉陰山排村的使用獵槍等兇器造成13人死亡1人重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劉愛兵就有精神病史[8]。
(二)因高彩禮引發的矛盾
農村訂婚、結婚成本較高,特別是家庭較困難的農民,因訂婚、結婚而債臺高筑。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在締結婚姻時,男方向女方贈送聘金、聘禮的習俗,這種聘金、聘禮俗稱“彩禮”。按照習俗,男方家向女方家送彩禮的多少,要由女方家的要求和男方家的經濟狀況而定。在價值觀轉型之痛背景下,“天價彩禮”又出現在媒體的新聞報道中,記者通過對東北、東南、華中地區的農村進行了調查,彩禮不到30年翻了幾百倍,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在調查中,記者發現,經濟越差的地方,彩禮要價越高,如在江西鄱陽縣,每個鄉鎮情況雖然有所不同,但彩禮普遍都在10-15萬元,有的地方彩禮甚至可以達到20-30萬元[9]。這對一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 6207元的農業縣來講,無異于天價[10]。由于“彩禮”嚴重超出村民所能承受的能力,不少農民因彩禮返貧。
另外,婚事排場攀比之氣也非常嚴重。有的地方不但聘金相對較高,還對請來喝喜酒的客人發放紅包,最多的每人發4千多元。這些巨大的結婚開銷為婚姻家庭矛盾埋下了伏筆。
有的婚后矛盾加劇,到了離婚的地步。男方結婚時費盡周折籌夠了彩禮,離婚卻面臨“人財兩空”、巨額債務的現狀,往往容易引發報復女方家的惡性案件。有的甚至在結婚當晚就發生慘案。比如,2017年1月11日發生在河南湯陰縣付道鎮東師莊村,正值洞房花燭夜,新郎竟然殺死了自己的新婚妻子,究其原因,就是因女方索要的彩禮錢高[11]。
(三)家庭關系不協調
農村訂婚、結婚年齡早,年青人自己都不盡成熟,對于家庭,更是缺乏責任感。在承擔家庭責任的能力方面,有的連自己生活都舉步維艱,更談不上贍養老人、撫養子女。這些都為婚姻家庭矛盾的產生埋下了伏筆。婚姻家庭矛盾的增多,他們心中的怨氣、怒火猶如不定時炸彈,一旦碰到導火索則會隨即爆發,釀造一樁又一樁的滅門慘案則成了他們發泄積憤的最佳途徑。
1.父母與子女間、兄弟姊妹間產生矛盾。農村一般多子女,子女長大結婚后,都涉及家庭財產的分配,在分配這個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些矛盾。農村的醫保還不盡完善,社會養老保障機制還未完全建立,加之價值觀因素、經濟條件等的影響,可能導致子女與父母產生矛盾,或者出現子女嫌棄老人的現象。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稱,他近年來在安徽、河南、江蘇等省的十幾個村莊調研發現,子女不孝現象很常見,很多老年人生活狀況較差[6]。父母與子女有了矛盾,如果不能及時有效的加以解決,很可能釀成慘案。上述安徽省鳳臺縣朱敬四(父)殺害小兒子一家,其原因就是因家中房產分配中,小兒子夫妻倆認為父親“偏心”,砸了父母全部家當,并將其趕出家門。當朱敬四因親戚去世幾次返鄉時,又屢遭小兒子當眾惡毒辱罵、持刀威脅,他在憤懣和絕望中生出了“了斷”的想法[5]。
兄弟姊妹間為了財產利益或贍養父母的問題,也可能發生矛盾,進而產生滅門慘案。如2016年6月22日晚23時20分,遼寧省鞍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鋼都”發布案件最新信息稱,目前,海城市東四鎮惡性案件已發現6名被害人尸體,均系犯罪嫌疑人王海軍的媳弟家人 (從事養殖業)。據當前掌握情況,初步認定系家庭利益糾紛引發案件[12]。
2.夫妻間發生矛盾。基于婚姻家庭矛盾引發的滅門案中,受害的女方往往是性格較強悍的人。而發案前的犯罪嫌疑人則性格較溫和,善于忍讓,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而對外的忍讓又常常被家人,尤其是妻子奚落、甚至被辱罵成廢物、懦弱、沒本事。這種奚落、辱罵對于學歷不高、文化水平偏低、處于社會底層、在外面本就飽受歧視、自卑敏感的犯罪嫌疑人而言,無疑是火上澆油,壓抑了的憤怒猶如可怕的情緒火山會不顧一切地尋找突破口,到那時,哪怕是一點瑣事就可能會引發慘案。
有的案件中,誘發犯罪嫌疑人實施極端行為的矛盾甚至出現了多重性,既有與自己父母的矛盾,又有與妻子的矛盾(這種矛盾的存在必然導致與岳父母、妻舅等產生矛盾),矛盾一旦爆發,便可能會出現滅絕人性的慘案。如2009年11月發生在北京大興的滅門慘案,犯罪嫌疑人李磊交代說,從小父母就對他管教非常嚴厲,而對他的妹妹十分偏袒,這使他心生積怨。他結婚后,娶的妻子又過于爭強好勝,而他自己性格內向,致使家庭積怨尤如一座火山。案發前的幾個月,李家拿到了600萬元人民幣的拆遷補償費,在這筆巨款的使用上又出現了分歧,直接導致了李磊弒父殺母砍妻捅妹滅子的瘋狂行為[13]。
(四)婚姻關系破裂
犯罪嫌疑人外出務工,妻子留守在家中,有的禁不住誘惑,有的耐不住寂寞,找了替補,因此有了背叛丈夫的行為。出軌行為被丈夫發現后導致婚姻關系破裂,引發滅門慘案。有的農村婦女外出務工,見識多了、能自立了,開始嫌棄自己的老公,怪老公沒本事。有的外出務工的女性為了能立住腳或找個省力掙錢的好差使而傍了有決策權的男性,由此引發夫妻婚姻破裂。被戴了綠帽子的男性,容易采用極端的方式解決問題。
有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并沒有出軌,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自卑、敏感多疑,懷疑妻子對自己不忠。比如,前述云南省騰沖一案中,犯罪嫌疑人邵某懷疑妻子和別人有染,經過外人調解,曾與“情敵們”立下字據,要求進行精神上和名譽上的賠償,然而心中仍懷有恨意,最終向妻子的同宗痛下殺手[4]。
有的案件中,由于夫妻間因性格不和、生計問題而產生矛盾導致婚姻關系破裂,有的因婆媳矛盾引發夫妻鬧離婚,有的女方產生攀比心理,感覺生活乏味,有的看不慣丈夫的抽煙、酗酒、賭博等陋習而提出離婚,當男方極力挽救卻達不到效果時,則可能產生砸花瓶(我得不到的,別人也休想得到)行為。
(五)大眾傳媒帶來的消極影響
電視、電影、網絡等大眾傳媒傳播的嚴重暴力情節及報道的現實生活中暴力犯罪對公眾起到了消極的影響。消極、有害的信息容易引起免疫能力差的人的犯罪欲望,現代網絡信息高速公路又為這些信息的傳播插上了騰飛的翅膀,不僅為犯罪創造了動機,還提供了平臺。無論是機場爆炸案,還是校園兇案,模仿效應無時不在。同樣,在一起滅門案發生后,通常也有多起案件隨后發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將這種現象稱為 “社會暗示”。她說:“一種信息發出后,會有兩種以上不同的接收方式,正常人是知道信息、了解信息,而犯罪人群就會從中去發現、研究作案方式和作案手段。對于犯罪人群而言,接收信息就是‘方法的告訴’和‘犯罪方式的啟迪’”[14]。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也認為,就一般意義而言,犯罪具有傳染性,如同疾病的傳染一樣,一種犯罪發生后,這種犯罪有可能被仿效而形成復制效應。這就像“爛蘋果定律”,先是一個蘋果發生腐爛,如果這個蘋果不被清除,那么整個一筐蘋果都會爛掉[4]。
三、農村滅門慘案防控對策思考
(一)注重心理疏導,對心理障礙者及時治療
1.積極開展心理健康宣傳教育活動。縣、鄉鎮政府職能部門要充分利用宣傳單、海報、廣播等形式,積極組織各類型的心理健康宣傳教育活動,改變村民對心理問題的誤解,提高其對心理健康的關注程度,提高人群精神健康水平,讓他們樹立起自立、自信的健康品格,將由心理異常導致的社會問題降至最低。
2.廣泛開展心理咨詢與心理危機干預服務。借助醫院、精神衛生機構豐富的心理健康咨詢及治療資源,采用傳統模式和新媒體模式,提供面談、電話熱線、微信、微博等手機網絡服務平臺等多種服務渠道,對村民宣傳精神疾病知識,開展心理治療,糾正或改善其個性缺陷,提供有效的壓力緩解、情緒管理等心理自我調適方法,提高心理應變能力,有效減少農村由于重大突發性心理危機而產生的惡性事件。
3.定期開展心理健康普查工作,構建農村心理健康檔案。借助人口普查的經驗,定期聘請心理學專家對全體村民進行心理健康普查,構建農村人口心理檔案,及時掌握村民的心理健康狀況,動態的監測村民心理變化情況,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構建人格障礙、精神疾病等高危人群的預警機制,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干預,提升對因嚴重心理障礙引發的傷害事件的應對能力。村民還可以隨時查看自己的心理健康檔案,促進其自我心理調適。
對心理障礙嚴重者除了采用心理治療外,還應當運用生物醫學治療的方法。縣或鄉鎮的監測評估中心在監測中發現心理問題嚴重的群體,應當及時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動員患者及家屬到正規醫院接受治療。
(二)轉變價值觀、崇尚新風尚
在傳統鄉村倫理體系中,子女不孝順會受到家族、村中權威長者的批評,會遭到左鄰右舍及其他村民的譴責。而當今,這種傳統制約已近乎解體,社會輿論也失去了力量。年輕人更看重現實利益,價值觀中似乎“沒錢”比“不孝”更丟臉。要轉變這些價值觀,就要充分發揮農村黨組織、村委會、村婦代會等基層組織及農民工用工單位的作用,利用社會輿論的力量,掀起尊老、愛老的潮流,讓晚輩尊重、愛戴長輩,評選、宣傳孝子(媳)、孝女(婿),政府給予物質獎勵,多角度、全方位扶持孝子(媳)、孝女(婿)發家致富。農村政府應當發揮對倫理失范行為的糾正作用。
轉變農村不良社會風氣,恢復樸實、友善、和睦的鄉風。大力倡導“人人生而平等”,鼓勵家庭成員間互相尊重,讓每個村民都能夠活得“精神上有尊嚴”。在婚姻的締結環節,農村基層組織要宣傳新的婚姻習俗,要鼓勵村中年長的、具有威望的人帶頭摒棄舊的婚姻習俗,不收彩禮,不講排場。政府還可以組織村民舉行集體婚禮,簡化程序,節約開支,積極引導、鼓勵支持有開明社會風氣的先進年輕人士,率先破“天價彩禮”習氣,使婚姻程序朝健康向上的新軌道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方向發展。
針對賭博違法犯罪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特點,特別是農村地區賭博問題仍比較嚴重的現象。公安部2018年1月29日在京召開視頻會議,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進一步深化打擊整治賭博違法犯罪活動,重拳打擊賭博違法犯罪活動。
(三)防微杜漸,多途徑及時解決婚姻家庭矛盾
在青海省大通縣滅門案(2014年2月9日,青海省大通縣蔡某因家庭矛盾殺妻子砍死7歲兒子、8歲女兒后自殺。)發生后,大通縣派出所所長稱,目前在農村以婚姻家庭矛盾引發的治安甚至刑事案件約占派出所接警案件數的80%[4]。
農村基層組織要利用一切條件與機會 (如節假日外出務工的人員回家時)宣傳婚姻法、刑法、繼承法等法律、法規,教育村民珍愛自己的婚姻家庭,鼓勵子女、夫妻間多聯絡,增進感情,做到互敬互愛,保證每位家庭成員精神上有尊嚴,宣傳酗酒、賭博的危害,對于愛酗酒、賭博的人員予以規勸,通過多種途徑避免婚姻家庭矛盾的產生。對于村民的婚姻家庭矛盾,農村基層組織要早發現,早介入,早調解,防止矛盾擴大化或加劇。在農村特有的人文環境和宗族勢力、地方家族勢力等綜合原因所導致婚姻矛盾疏導途徑單一的背景下,農村基層組織要充分調動各方面的力量來解決好婚姻家庭矛盾:第一,動員矛盾雙方都敬重、信任的宗族、家族、鄰里長者來勸解、協調;第二,鄉村干部依法、公正地調處矛盾糾紛;第三,通過村婦代會等組織協調;第四,向矛盾雙方提供法律途徑。比如,告知村民可到公安派出所、到法院尋求解決。有了這么多的合法途徑來解決婚姻家庭矛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暴力事件的發生。
(四)規范大眾傳媒,發揮積極作用
大眾傳媒的行業自律是其謀求自身發展空間、爭取社會廣泛認同的必要措施。大眾傳媒需要從職業標準出發約束自己的行為,傳播信息時,不應該僅僅考慮自身商業利益和效率,而應當從對公眾負責、對社會負責的角度出發,要運用強大的信息傳播功能宣傳法律知識,提高公眾的守法、維護法律尊嚴的意識,宣傳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弘揚社會主義的責任感、使命感、道德感。最重要的是,大眾傳媒要對現實典型案例進行客觀、全面、鮮活地報道,邀請相關專家做節目,剖析犯罪的原因,提出預防的對策。大眾傳媒進行報道時,要善始善終,要追蹤報道對犯罪人的處罰,以起到警示作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遏制農村滅門慘案的發生,還需要一方面發展農村經濟,另一方面解決農民進城就業問題。發展農村經濟,加大農村地區扶貧力度,扶持優勢產業,改善農民生存環境,讓每個村民都能夠活得“物質上有保證”,減少因經濟原因而導致的婚姻家庭矛盾。對進城務工的農民進行文化和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社會競爭能力。同時政府部門要逐步發展和培育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消除就業歧視,打破區域藩籬、行業禁錮和單位壁壘,對農民工敞開就業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