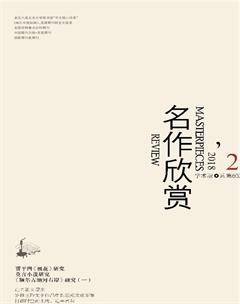老子學說對死亡的超越
摘 要:老子直面死亡,從死亡的事實出發,提出“出生入死”(《老子》五十章);進而又從價值維度對死亡進行超越,提出“死而不亡”(《老子》三十三章)。老子的“出生入死”解構了生命之永恒崇拜,老子的“死而不亡”從價值維度超越了生命的有限性。
關鍵詞:老子 死亡超越 死而不亡
老子直面死亡,從死亡的事實出發提出“出生入死”(《老子》五十章);進而又從價值維度對死亡進行超越,提出“死而不亡”(《老子》三十三章)。
一、出生入死:老子對彼岸世界的解構
一般認為老子談論死亡的內容是稀少的,其實不然。在通行本《老子》一書中,直接提到“死”的原文竟然達到了十八處,因而死亡問題是老子學說的一個重要內容。老子討論死亡問題,是對人的生死二重性同時考察的。在老子思想中,對反思維,也就是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確實是存在的,“反者,道之動”(《老子》四十章)里的“反”就是對反。老子還明確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老子》四十二章)的對反命題,認為陰陽是共生的。這種相反相成的思維,在“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二章)這一段里有集中的表述,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后都是對立統一的。對于人來說,最根本性的對反是生與死的對立統一。老子在表述對反思維“反者,道之動”(《老子》四十章)之后,接著就言說了有和無的對反,“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無”(《郭店老子甲本》)。在“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這一組對反性表述中,“有無相生”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而有和無,便是生與死,是存與亡(存在與消亡),《郭店老子甲本》中的無原文正好是亡(通行本《老子》是“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認為無的地位高于、先于有的地位,即有無不是并列的位置,這與“有無相生”的思想相互矛盾,應取《郭店老子甲本》)。“有無相生”,通俗地說就是生死相依、存亡統一,有生就有死,有存就有亡。因而人包含生和死兩個維度,回避死亡的生,是不完整的,老子的生死學說是以直面死亡這一事實為基礎的,“出生入死”(《老子》五十章)是一種事實描述,言說人的生是奔向死去的,人是從生到死這一個過程,死亡是最終的結局,而不是日常語言中的“出生入死”,不是意指不怕死的冒險精神。老子的“出生入死”和海德格爾的“向死存在”(向死而生)頗為類似。老子從死亡事實出發,來考量生之有限,從而構建意義世界,這與孔子有本質的差異——孔子則是直面生而回避了死,“未知生,焉知死”。
二、死而不亡:老子對死亡事實的超拔
“出生入死”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這也決定了生命的有限性,而試圖用一種無限來超越有限。當然,老子也給出這樣一個通道,那就是生命必然消亡,但價值可以永恒,這就是在“出生入死”的基礎上提出了“死而不亡”(《老子》三十三章)。“死而不亡”,死的是生命,不亡的是價值。老子談論的不亡,絕不是靈魂不亡,在原文中沒有靈魂的論述,帛書本《老子》是“死而不忘”也驗證了這一點——“死而不忘”是價值永恒,價值融入歷史文化里。所以老子特意還提到,有道之人死后對子孫后代的影響,同時融入家族史里,子孫后代“不忘”而進行祭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老子》五十四章)。“出生入死”指向事實存在,“死而不亡”指向價值存在。價值之所以可以永恒,是因為價值是符合道的,而道是永恒的,“長生久視之道”(《老子》五十九章)、“道乃久”(《老子》十六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老子》二十一章)、“獨立而不改”(《老子》二十五章)、“谷神不死”(《老子》六章)、“天長地久”(《老子》七章)。如果人符合道,不失道,則價值可以長久,“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老子》三十三章)。“不失其所者久”,就是不失其道者久。老子本人也一樣,生理的老子死了,但價值老子(文化老子)沒有亡,我們至今還在談論老子,老子是“缺席的存在者”。生命消亡,但價值長久,老子還稱其為“沒身不殆”(《老子》十六章、五十二章)。王弼把“死而不亡”注為“身沒而道猶存”,這也就是老子的“沒身不殆”。“‘死而不亡乃喻指‘身沒而道猶存(王弼注);像歷史上許多大思想家一樣,身軀雖然死滅了,但他們的思想和精神卻永續長存,這就可以說是‘壽了。”道是恒久的,人法道則人“沒身不殆”,這在老子原文中也是明確論述的,“道乃久,沒身不殆”(《老子》十六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老子》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這里的母是道,因為道是始。“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復守的是道,守道則“沒身不殆”,也就是守道則“死而不亡”。在老子學說里,生和死(存在與消亡)是對立統一的,“有無相生”;而生命之死與價值不亡(有限和無限)也是對立統一的,“逝曰遠”(《老子》二十五章)。逝是有限的生命維度,而遠(恒久)是無限的價值維度。老子學說里有明確的無限觀念的表述,“復歸于無極”(《老子》二十八章)。孔孟也一樣是用價值超越死亡的,比如孔子的“殺身以成仁”,孟子的“舍生而取義”。但不同的是孔孟的死亡觀具有悲劇精神(悲壯感),而老子的死亡觀是自然平和的。孔子為了價值可以輕死,老子則是貴生的,在順生死中成全價值,“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老子》七十三章)。因而老子是明確重死而反對輕死的,“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老子》八十章),“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老子》七十五章)。莊子則是用樂觀精神面對死亡的,妻死擊盆而歌,認為死亡是完整生命所不可或缺的,死亡意味著擁抱天道自然,“息我以死”。
三、復歸于樸:老子對價值永恒的確立
什么樣的價值是“死而不亡”而具有無限性呢?老子認為是素樸,所以老子在“復歸于無極”這一章,同時提到了“復歸于樸”(《老子》二十八章)。老子主要用“久”來形容價值永恒,在通行本《老子》中,出現“久”的原文達到了十一次,出現的頻率是比較高的。首先道是久的,“長生久視之道”(《老子》五十九章)、“道乃久”(《老子》十六章),人法道而行,則人“可以長久”(《老子》四十四章)。老子從反面確認了不可恒久的要素是剛強,不可剛強是行道的主旨,“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老子》四十二章)。剛強是違背道的,“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也就是說堅強屬于死亡一類,不可持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老子》七十六章)。類似的論述還有很多,“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老子》九章),“自矜者不長”(《老子》二十四章)。在治國層面,老子反對威權治國,對執政者提出了警告,認為威權不可恒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老子同時從正面論述了恒久的要素是柔弱,柔弱是道的運用方式,“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因而,柔弱是恒久的,“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老子具體又從三個方面論述柔弱與恒久的關系,一是先人后己而恒久,“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舍后且先,死矣!”(《老子》六十七章)二是知足知止,在身與名利之間保持一個平衡而恒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四十四章);“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老子》二章);“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二十二章)。三是在治國方面,廉政、簡政之無為之治可以恒久,“治人事天莫若嗇……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老子》五十九章),“少則得,多則惑”(《老子》二十二章)。老子在治國維度反對剛強主張柔弱,實際是反對威權而主張民主,威權政治是剛性的,而民主政治是柔性的。詹姆斯則把哲學家的氣質分為“柔和的、剛毅的”兩種,認為柔和氣質的人屬于理性主義者,而剛毅氣質的人屬于經驗主義者。有的學者認為老子主陰(柔),而孔子主陽(剛),“剛毅木訥近仁”,也有一些道理(遺失的《齊論語》,在海昏侯墓中得以出土,《齊論語·智道篇》首句便是“孔子智道之 也”,而 同陽)。
參考文獻:
[1] 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2] 陳鼓應注譯.老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詹姆士.實用主義[M].李步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注:本文入選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死亡哲學分組會議
作 者:李健,暨南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編 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