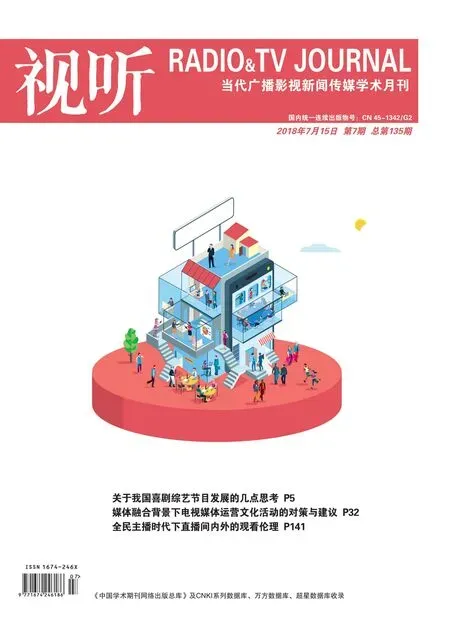當代中國電視紀實作品的聲音審美探析
□李江
電視紀實作品是聲音語言和畫面語言相結合的產物,在此所談及的聲音語言“并非是以口相傳的‘語言’,而是限于藝術領域的獨特的語言形式”①。相較于畫面而言,電視紀實作品的聲音語言更具可塑性,在增強作品的真實性、豐富作品的敘事手段、表現作品的內在情緒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修飾下的真實美——真實性
電視紀實作品講究真實并不意味著對藝術創作手法的缺失,作為“一種對現實進行審美觀照的藝術形式”②,聲音語言越有層次感、立體感、運動感,在藝術層面上也就越生動、越形象、越鮮明。電視紀實作品中的音響效果只有比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聽覺更敏銳、更清晰,甚至超越現實,才能讓受眾產生身臨其境般的審美體驗。
(一)現場同期聲是作品真實性的有效體現
人物同期聲增強了電視紀實作品的現實主義色彩,拉近了受眾與電視紀實作品之間的距離,極大地體現了電視紀實作品真實性這一審美特性。講述藏族人民與牦牛之間相互依存的電視紀錄片《牦牛》大量使用人物同期聲,不會說普通話的藏民操著一口濃厚的藏族方言,時不時地冒出“扎西德勒”,哼著《青藏高原》,傳遞出西藏獨特的地域魅力和區域文化。紀錄片《昆曲六百年》通過演員排練、演出、視聽資料等人物同期聲,使得細膩柔軟的昆曲旋律貫穿作品始終,從聽覺上深化了昆曲大美至美、獨具一格的藝術魅力,為作品增添了一抹濃重的神采。《指尖上的中國——鳳棲梧桐》大量使用了古琴獨奏、古琴教學、古琴調試等現場同期聲,天籟般的音質傳播著古琴安靜細膩、虛靜高雅的獨特韻味,體現出斫琴者、古琴、演奏者三者人琴合一的藝術境界。
(二)音響效果呈現出多層次的真實美
2012年,杜比實驗室推出了杜比全景聲,帶領受眾進入到令人震撼的聽覺空間,實現了聲音語言的多維度展示。杜比全景聲的推出,強調了音響效果在影視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推進了電視紀實作品在聲音語言層面的突破與創新。
電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翻開了中國電視紀實作品在音響效果制作上的新篇章。整部作品的音響效果除了現場拾音之外,還大膽地使用擬音、混音等電影聲音制作技術,在音效的制作方面可謂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為了突出獲取食材的艱辛、展示美食的質感,片中關于采摘、鑿冰、魚躍、振翅、酥脆、粘稠、吞咽、吸吮等眾多音效均經過專業的擬音,最終混縮而成。為了展現街頭大排檔的喧囂,《舌尖上的中國》在前期拾取環境聲的基礎上還混入了收銀抽屜的開合聲、鍋碗瓢盆的碰撞聲、沸沸揚揚的人群聲等眾多細節音效,在氛圍的渲染上做到了極致。
在充分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模擬、混縮出來的音效,體現出電視紀實作品“逼真性與假定性的有機統一”③,這種音響效果的處理方式非但不會削弱電視紀實作品真實性這一本質特征,反而豐富了作品的聲音層次,打破了受眾在“審美經驗中的定向期待視野”④,極大地拓展了電視紀實作品的藝術魅力。
(三)數字化技術處理加強了畫面的運動感與透視感
奔馳的駿馬、呼嘯而過的火車等運動主體勢必會產生距離、方位上的變化,而距離、方位上的變化必將引起運動聲音上的變化。當運動主體離我們越近,運動所產生的聲音就越大、音調就越高;反之,當主體離我們遠去,聲音就逐漸變小、音調逐漸變低,直至消失。《玄奘之路》對鳥鳴、馬嘶,《極致玩家》對奔馳的火車等聲音語言的處理伴隨著畫面運動主體的縱深運動而作出相應的變化,根據多普勒效應制造出遠近、高低等運動的距離感,使整個聲畫系統立體起來,使受眾切實感受到物體的運動軌跡。《舌尖上的中國》關于養蜂人采蜜的場景描述中,伴隨著養蜂人接近蜂巢,蜜蜂振翅的聲音也在發生著變化,從一兩只微弱的振翅聲慢慢增加至一群蜜蜂蜂擁而至的嗡嗡聲,從聽覺上形象地體現了人物由遠及近、蜜蜂由少到多的變化。
二、聽覺上的二度創作——敘事性
畫面具有局限性,限制了影像,僅僅依靠畫面語言是無法完成作品的敘事的,相較而言,聲音卻比較自由,不受畫面的束縛,因此在敘事上也更為靈活多變。
(一)用旋律傾訴
在電視紀實作品中,音樂從聽覺層面參與敘事、輔助敘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完善了作品的敘事能力。在大型紀錄片《我愛你,中國》中,每集的片頭均采用播放器播放音樂的形式來交代背景。《東方紅》等膾炙人口的革命歌曲突出了50-70年代濃厚的時代感;流行歌曲《跟著感覺走》等彰顯出改革開放為人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我和你》等歌曲訴說著北京奧運會等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歌唱祖國》則將中國人對祖國的敬愛、對夢想的展望表現得淋漓盡致。除此之外,為了突出此部作品的主題性和統一性,徐鯉選擇歌曲《我愛你中國》為主題音樂,并采用單主題貫穿式,抒發了對祖國的濃濃愛意。為了展現不同的情緒和情感,徐鯉還將《我愛你中國》進行了大膽的編曲,抒情的鋼琴版、悠揚的弦樂版、活潑的管樂版等多種改編版本、變奏版本醞釀著不同的情緒,抒發著不同的情感,同時也避免了同一旋律反復出現所造成的重復感。
(二)對時空的延展
電視紀實作品的聲音語言可以擴展時空,解說詞、旁白等人聲語言,動作音效、環境音效等音響效果都為時空的擴展提供了無限可能。畫外音提醒著受眾畫外時空的存在,從聽覺上填充了視覺上的缺憾,彌補了畫面語言敘事的局限性,帶給受眾額外的信息接收方式。比如《世界遺產在中國》關于泰山與信仰的敘述中,和著木魚、引磬的敲擊聲,引出經文的唱誦,將作品敘事的范圍由巍峨的泰山擴展至神圣的宗教儀式,彰顯出這座大山所蘊含的民間精神信仰。
(三)張弛有度的聲音剪輯
由于較強的真實性,電視紀實作品的敘事風格較為深沉,冗長的紀實性敘事手法容易使受眾產生審美疲勞。而聲音語言的巧妙運用則可以打破原有的敘事方法,將音樂、音效穿插在解說詞的敘述當中,從而像標點符號一樣造成適當的停頓,營造張弛有度的觀賞節奏。《世界遺產在中國》對云岡石窟的敘述處理較為巧妙,通過大量渲染氛圍的音樂以及鼓聲、誦經等音響效果的穿插剪輯,使佛教在北魏由盛到衰到滅頂再到重振的整個過程處理得猶如波瀾起伏的大海,加強了畫面的生動性,為受眾帶來了極大的聽覺快感。
三、情感的渲染與升華——抒情性
情感的生成與釋放在藝術作品中占據重要地位。盡管電視紀實作品講究真實美,要求最大程度還原現實,但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仍然無法脫離創作者的主觀情感。如果作品盲目追求紀實,沒有情感的流露,只能成為對現實生活的機械復制,無法完全表達靈魂深處的情感積淀。聲音語言作為一種語言元素存在于電視紀實作品中,是作品情感釋放的重要紐帶。
(一)寄情感于音符之中
在電視紀實作品中,音樂能夠展現隱藏在畫面背后的喜怒哀樂,極大地釋放受眾的情感與情緒,延續受眾在視覺層面的審美體驗,賦予受眾更多的遐想空間。音樂加強了電視紀實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或震撼,或唯美,是渲染情感、烘托氛圍的有效手段,從而帶領受眾進行更深層次的審美感悟。
在眾多電視紀實作品當中,大型史詩紀錄片《大明宮》可謂是寄情感于音樂語言的典范。《大明宮》的音樂創作延伸了作品關于歷史的講述、人物的刻畫、情感的表達等諸多方面:清脆嘹亮的笛聲伴隨著女聲輕吟的《往事隨風》在緩慢悠揚的合奏中娓娓敘述大明王朝的歷史背景;集大氣、震撼、委婉、深沉為一體的女聲哼鳴旋律《如夢》幽幽地傾訴著武媚娘的傳奇一生;柔和優美、婉轉流暢的二胡獨奏《蓮花的呼喚》醞釀著唐玄宗李世民因愛情而丟失江山的復雜情緒。在《大明宮》中,有恢宏壯觀的建筑描述也有慷慨悲憤的情緒釋放,有對開元盛世的贊美也有對王朝衰退的惋惜,流暢的音樂線條打破了受眾的審美心理定式,完整呈現了大明王朝歷史變遷的整個過程。
(二)后期技術處理的藝術化表現
聲畫之間、聲聲之間不同的處理方式,可以突破受眾對作品在感性層面的認識,豐富停留在受眾腦海中的具象畫面,從而使受眾領悟作品蘊藏的內在情感。音量的動態處理可以實現情緒的渲染、情感的迸發。在《新絲綢之路》中,伴隨著解說“唐代長安城正顯出它巨大的身影,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座城市呢”,畫面逐漸淡出,渾厚的背景音樂卻愈加具有爆發力,音量逐漸提升,延時效果器產生的余音延伸至下一個場景,直至遠景俯拍長安城的畫面淡入,音樂完全結束。在整個過程中,音樂、畫面呈交融狀,短短的幾十秒時間凝聚了懸念的設置、情感的鋪墊,為展現長安城的宏偉壯觀作下鋪墊,給人以震撼之感。
四、獨特的熒屏體裁——文學性
畫面加解說是電視紀實作品的主要敘事手法,也是解說詞異于其它文學創作的根本所在。在電視紀實作品中,解說詞不管是從創作方面還是受眾的接收方面,均不可以脫離畫面而單獨存在。在電視紀實作品中,解說詞以直觀準確的方式對畫面內的信息進行清晰的說明,對畫面外的信息進行權威的補充,避免受眾因個體差異對作品的理解產生歧義。
在電視系列紀錄片《生命》中,李易以他閱盡滄桑、沉穩渾厚的嗓音與大自然物種頑強的生命力形成了高度的統一,全面詮釋了生命的含義,以通俗易懂的解說詞化解了受眾與自然學科之間的障礙,帶領受眾在自然界體驗了一場非同尋常之旅。《生命》充分體現了解說詞在電視紀實作品中的韻味,是作品審美層面上的高度升華。
五、尾聲
不同的聲音語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錄音師對聲音的錄制、剪輯師對聲音的剪輯、混音師對聲音的混縮等都是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藝術創造的過程,也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謂之永恒的交響詩。對隸屬于視聽藝術范疇的電視紀實作品而言,畫面語言與聲音語言要呈緊密融合之勢而不可相互干擾。聲音語言要輔助畫面語言進行敘述,酣暢淋漓的聽覺盛宴固然重要,卻不可喧賓奪主,往往聽覺上的適當留白反而會引發受眾更廣泛的思考,只有完美的視聽結合才能傳遞出電視紀實作品真正的精髓所在。
受巴贊紀實美學的影響,中國電視紀實作品由于盲目追求紀實而導致審美層面的缺失,忽視了聲音語言的藝術魅力。優秀的電視紀實作品應該在創作之初就將聲音語言納入考慮的范疇,進行人聲的定位、音樂的構想、音效的設計。聲音的先行有助于作品在后期剪輯過程中對敘事、節奏、情感等進行全方位、綜合性的把握,也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聲畫合一這一渾然天成的藝術形式。
就目前來看,中國電視紀實作品不管是在聲音處理的技術上還是聲音創作的意識上,尚且處于邊緣化的生存窘境,僅有少部分作品的聲音處理能與電影作品相提并論,大部分的電視紀實作品仍然囿于傳統的模式和原則,缺少專業的紀實作品錄音師和聲音創作團隊,這些在本質上是對電視紀實作品紀實意識的模糊。對于當下中國電視紀實作品的創作者們來說,必須加強對聲音語言的重視,學會用聲音思考、用聲音架構,利用先進的聲音制作技術進行大膽的摸索和突破,從而縮短與國際一流聲音制作水平之間的距離,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
注釋:
①施玲.影視配音藝術 [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3.
②蔡尚偉.影視傳播與大眾文化[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148.
③彭吉象.藝術學概論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360.
④彭吉象.藝術學概論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