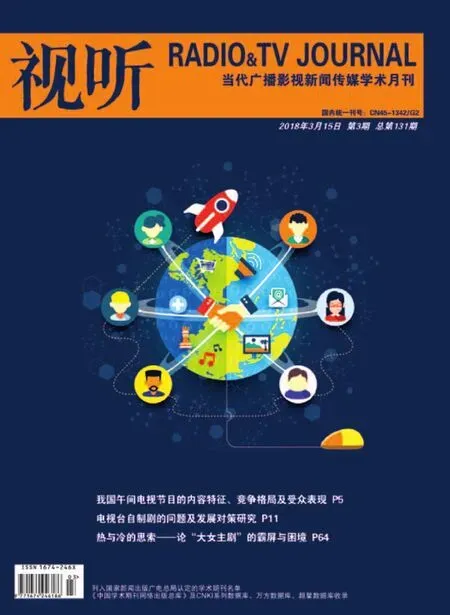傳播學視域下的網絡謠言治理探究
□嚴彪
一、網絡謠言的鮮明特性
一是生產成本低。網絡謠言的信源呈現匿名性特征,造成生產成本極低,傳播主體幾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即可將謠言散播出去。因網絡自身屬性,網絡謠言的傳播和接收往往同步進行,且接收者形成二次傳播,網絡謠言呈放射式傳播路徑,不斷擴大傳播范圍。二是社會危害大。在現實環境下,由于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約,人們本身的話語空間不足,加之獵奇心理,不自覺地成為謠言散播的工具。在網絡環境下,擺脫現實環境的束縛,加上網絡技術的支持,加速了網絡謠言的傳播速度和范圍,造成的社會影響力也特別巨大。三是核心意涵變異。網絡謠言多無事實根據,我國學者李若建提出,“謠言往往是在把真實成分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出現了位置錯配。”換言之,網絡謠言是各種信息碎片的重新排列組合,符合一定的思維邏輯,客觀上有一定的真實成分存在,會引起部分人的認同和共鳴。網絡謠言在傳播過程中會人為地進行二次加工,在傳播鏈條上的各環節夸大公眾感興趣的信息,同時弱化存在感不強的信息,造成信息本源異變。
二、網絡謠言滋生蔓延的原因
(一)傳播者的自身利益驅使
傳播者在網絡平臺上傳播謠言,多半將自己標榜成揭露事實真相的衛道士,利用我國轉型期的種種社會矛盾,迎合部分民眾的心理,依附貧富差距、福利待遇、民主程度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議題,造謠生事,妖言惑眾,并發動網絡水軍,人為制造網絡主流民意,形成所謂“擬態環境下的虛擬民意”。這并不是現實環境下民意的客觀再現,反而往往是背道而馳,這些議題不斷去挑動網民的敏感神經。他們游走在法律紅線的邊緣,還贏得相當一部分無法辨別是非的網民的支持。他們利用自己所謂的網絡人氣轉化經濟利益,或炒作捧殺,或惡意重傷誹謗、排擠異己,逐漸形成龐大的利益產業鏈。
(二)受眾角度的多元因素
首先是外部環境造成的群體意識作祟。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認為,作為群體中的個體具有“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情感因暗示和相互傳染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的特征。當網絡謠言甚囂塵上,在社交平臺已然演化為集體意識,個體的非理性從眾心理開始發酵,在強烈的群體意識氛圍下,個體的獨立甄別能力開始失效。外部環境對個體的影響客觀上縱容了網絡謠言的傳播。
其次是個體的自身因素。由于客觀環境制約,個體在現實環境下話語空間不足,網絡平臺的匿名性給予個體足夠大的話語空間,這種自由表達的語境氛圍讓個體無意識中放松自我約束,對網絡謠言缺乏“個體把關”。網絡謠言客觀上是一種輿論傳播方式,起到了道德評價的作用,個體錯誤地選擇這一輿論方式來發泄自己對現實環境的不滿,成為個體泄憤的私器。
最后,個體受反向思維定勢的“刻板印象”制約。比如有些網絡謠言最后被證實為真實信息,缺乏對網絡辟謠的信任,形成反向思維定勢的“刻板印象”,這種“定型化效應”影響了個體的理性思考判斷。
(三)網絡社交平臺的“把關人”角色失位
網絡社交平臺對網絡謠言缺乏監管,有監管難度大等客觀原因,某種程度上也有社交平臺縱容的成分。如果網絡社交平臺加大監管力度,會授人以柄,被網民扣上“干涉言論自由”的帽子,對自身平臺的發展不利;其次是某些網絡謠言的巨大影響力會吸引網民關注,增加了網絡平臺的影響力和活躍度。
(四)官方公信力下降,傳統管控思維失靈
網絡信息碎片化和多元化客觀上造成官方部門執法難度大,但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于主觀原因,官方辟謠缺乏可信度,沒有事實依據支撐,往往采取“官本位”的行政命令式辟謠,不僅無法起到辟謠的作用,還引起民眾反感,造成輿論反彈。官方公信力下降造成網絡謠言四起也是不爭的事實。對于網絡謠言,官方還把傳統管控思維從線下延伸到線上,缺乏應變和革新。傳統管控手段以行政思維式的“堵”和強權思維式“引”為主,在面對網絡時代時,這些均已失靈。官方只是一味地查封、屏蔽網絡謠言,只會更加刺激民眾的好奇心理,讓網絡謠言在傳播過程中多次加工,越發偏離事實真相。再者,“堵”思維在網絡的科技性面前捉襟見肘,網絡時代的信息渠道“變幻莫測”,人為的“堵”只能鞭長莫及。強權思維式的“引”和科學性的宏觀調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這種引導是強加在民意上的,并不能讓民眾信服。
三、網絡謠言的應對之策
(一)傳播主體要克己守法,守住道德底線
傳播主體透過網絡平臺獲取經濟利益無可厚非,但必須是在合法范圍內,傳播信息要三思而行,對自己發布的信息要仔細甄別,檢驗是否客觀真實。不斷加強自我學習,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不能因為要“吸眼球”“博出位”而毫無顧忌地在網絡平臺大放厥詞。同時,加強法律教育,明確法律規范,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違規違法,以免最后追悔莫及。
(二)受眾要明辨是非,正確行使言論自由
互聯網時代,網民獲取信息更加便捷,信息的碎片化和“井噴式”生產確實讓民眾應接不暇,信息的傳收同步化、快餐式閱讀讓受眾無暇思考,那種現實環境下的獨立思考能力慢慢喪失,受眾沒有精力對諸多的信息進行一一甄別,但這不能成為受眾縱容網絡謠言肆意散布的借口,更不能不明就里地成為網絡謠言擴散的工具。
首先要做到“不信謠”,現在的網絡謠言越來越難以分辨,普通民眾的知識水平不足以分辨信息的真假。這一方面需要知識水平高的民眾對民眾加以科普,同時,普通民眾要加強自我學習,要有“質疑精神”,不能“拿來主義”,人云亦云。
其次要做到“不傳謠”,對尚未被證實的信息不要隨意傳播,正確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凈化自己的話語空間。同時要行使公民的輿論監督權利,對網絡謠言要及時舉報,將網絡謠言扼殺在萌芽狀態中。
最后要做到“不制謠”。網民要加強自律,合理表達自己觀點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各抒己見,博采眾長,匯聚民智,才能推動社會發展,但是民眾不能因為一己私念,為了發泄私憤,惡意編造網絡謠言。
(三)網絡社交平臺要有職業道德,加強行業自律
網絡社交平臺既然能給大眾的擬態話語空間提供越來越先進完善的技術支持,必然在信息把關方面不存在技術障礙。這些網絡行業的從業者不能一味追求經濟利益而喪失了自己的職業道德,對網絡謠言的縱容勢必會造成行業的惡性競爭,都采取此等低級手段,玷污了網絡信息環境。所以,網絡行業從業者要明確自身的“把關人”角色,對網絡謠言要加強監管,在信源處扼住網絡謠言的咽喉,能有效控制網絡謠言的傳播。
(四)官方部門要轉換管控思維,靈活科學行使官方職能
官方的公信力日益下降,讓辟謠舉步維艱,這就需要政府要以更加公開透明的姿態應對網絡謠言,對網上傳聞要積極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用事實戳破網絡謠言,對查處屬實的網絡傳聞,不護短、不遮羞,依法懲處,修復官方形象,提升自身公信力。
其次,要轉換傳統的管控思維,與民眾真誠對話,給“輿論場”和“民意場”建立溝通渠道,不能再以“官本位”和“集權思想”讓民眾感受到不平等的對話姿態,在平等交流的狀態下,任何網絡謠言都會不攻自破。
最后,靈活科學行使官方職能,建立應對網絡謠言的應急預案,各部門分工明確,協同合作,這就需要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國外在應對這一問題時都有一套標準作業模式,信息核實部門和信息發布部門各司其職,前者積極核實信息的真實性,然后交由信息發布部門向社會傳達核實結果,極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我國網絡行業發展速度極快,網絡立法滯后也在所難免,這就需要相關部門要完善網絡立法,規范民眾的網絡行為,打擊網絡謠言,凈化網絡環境。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3.李若建.虛實之間:20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謠言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4.[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 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