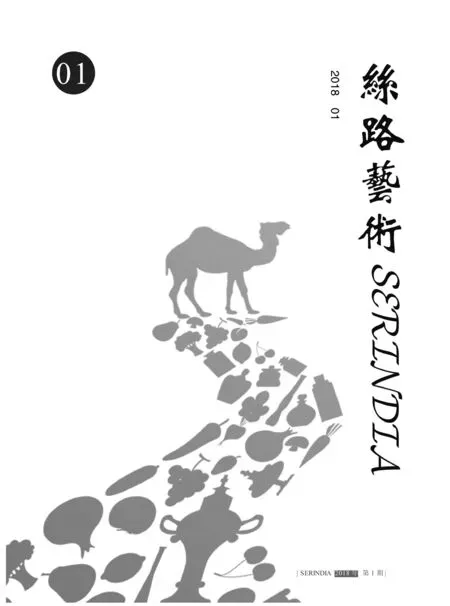淺議犯罪構成理論與三段論的推理方法
洪一良
(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一、三段論的推理方法的概念和作用
三段論的推理方法,又稱為演繹推理,是從一個共同概念聯系著的兩個性質的判斷(大前提、小前提)出發,推論出另一個性質的判斷(結論),即由一般性的前提推導出特殊性結論的推理,是法律推理的一種類型。因此,三段論的推理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大前提,這是概括了若干同類個別事物中的普遍性特征判斷的命題;二是小前提,這是說明個別事物屬于大前提主詞外延的,是我們所需認識對象的比較特殊的命題;三是結論,表明該個別事物也具有大前提中普遍性特征所揭示的屬性,是由兩個前提的聯結所推導出的命題。
刑事司法中定罪過程中,三段論推理方法的作用突出體現。首先,要求司法人員有足夠的實踐經驗來為推理的進行提供鋪墊。沒有相關的實踐經驗,沒有獲得感知的、需待認識的事物情況,沒有運用演繹推理的“預定目的”,也就沒有運用演繹推理的基礎。
刑事司法人員將通過審理所發現的具體犯罪事實導入刑事法律的某一方面的一般性規定中,從而得出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結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有司法機關正確地運用三段論的推理方法,認真地查明案件的重要事實,準確地找到與案件事實相對應的刑事法律規范,才能得出符合法的正義要求的判斷。這也是司法人員經過長期的法律知識學習和辦案經驗積累所形成的邏輯思維的體現,如果司法人員沒有接受足夠的邏輯思維訓練,就容易在頭腦中出現“想當然”的思維誤區,憑“想當然”辦案,就可能出現冤、假、錯案,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二、我國犯罪構成理論與德日犯罪構成理論的比較
犯罪構成由刑事實體法規定的、決定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并為成立該種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主客觀要件的總和。我國傳統犯罪構成理論包括: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和犯罪主觀方面四個要件。不難看出,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是將小前提(案件事實)拆分成若干個部分,再判斷能否將其一一對應在大前提(刑法規范)之內的一種方法。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能夠解決司法實踐中發生的大部分問題,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卻存在難以解釋的地方。
例如15周歲的甲和17周歲的乙共同盜竊,由甲實施盜竊行為,乙在外面望風。按照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甲由于不滿足盜竊罪規定的16周歲刑事責任年齡,因此不構成犯罪,但是乙能否構成犯罪就難以認定,因為乙的望風行為并不是刑法規定的盜竊行為,小前提和大前提難以做到一一對應,但顯然乙是應當構成犯罪的。
此外,我國犯罪構成理論在未遂犯的認定中存在主觀臆斷危險。在犯罪構成四要件體系中,四個要件是不分先后順序,可任意置換,這往往就使得司法人員在犯罪未遂的案件判斷中先確定了結論,然后直接在小前提中認定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如果司法人員認為行為人具有主觀罪過,那么行為人的客觀行為就是危害行為;反之如果司法人員否定行為人具有主觀罪過,那么就認定行為人無罪。這樣的推理方法在邏輯上就存在問題,因為決定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的是其所實施的客觀行為,而不是主觀思想,否則就連沒有侵犯法益的思想犯也可以認定為犯罪。
德日刑法的犯罪構成理論十分復雜,也存在爭議,但通常認為階層式的犯罪構成理論具有更強的合理性。階層式的犯罪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先從形式上判斷行為是否刑法規定一致,如果符合就對行為進行實質考察,評價行為是否客觀上侵犯了法益,存在侵犯法益的行為就對行為人進行最后的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判斷。
階層式犯罪構成理論相比我國傳統犯罪構成理論有以下優勢:
(1)合理地解決共同犯罪的問題。上述案例用階層式犯罪構成理論就很容易解答,15周歲的甲和17周歲的乙是共同犯罪,因此兩人在構成要件符合性和違法性兩個層次上是一個整體,即確定兩人在實質上都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但是由于15周歲的甲不滿足刑事責任年齡,因此在有責性上將甲排除成立犯罪的可能,而17周歲的乙自然是成立犯罪的。
(2)更好地避免了司法人員的主觀臆斷。階層式的犯罪構成是一種層層遞進、抽絲剝繭地認定犯罪的過程,而不是像傳統犯罪構成那樣拼圖式地將各個要件進行對應。在前兩個階層的判斷中,都是對行為人進行客觀上的判斷,只有客觀上符合刑法規定的實質要件,才認定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換言之,司法人員要認定行為人成立犯罪,就必須先認定行為在客觀上侵犯了法益,或者對法益造成了實質的威脅,從而排除將思想犯認定為犯罪的可能。
(3)更符合從無罪到有罪的認定過程。階層式的犯罪構成理論,先推定行為人無罪,再將行為人的一系列主客觀要件從先客觀后主觀的順序進行逐層判斷,如果在其中一層阻卻,則徹底宣告其無罪,只有真正確定了行為具有客觀違法性和行為人具有非難可能性,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而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則要求司法人員直接尋找行為人可能成立犯罪的要件(證據),當所有要件找齊后就可以認定犯罪的成立,從邏輯上看這是一種有罪推定的過程,不符合我國刑事司法中無罪推定的原則。
三、階層式犯罪構成在三段論推理中的運用
由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司法人員必須先考慮刑法的規定,即先有大前提,然后才能在具體案件中判斷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這樣才能限制司法權力。
具言之,司法機關是被動地認定犯罪,只有出現了符合刑法規定的客觀行為,才能適用刑法;如果先確定行為的性質,再尋找具體的刑法規范,這就將大前提和小前提倒置,使案件事實成為大前提,刑法規范成為小前提,就可能造成司法權力的濫用。我國傳統犯罪構成理論就存在這種先通過行為人的主觀確定案件性質,再尋找對應的刑法規范,使得司法人員有“想入罪就入罪,想出罪就出罪”的可能性,這是不可取的。例如,當司法人員認為行為人主觀上有盜竊的故意,客觀上乘坐了公共汽車,因此乘坐公共汽車的行為是盜竊罪的預備行為,因為刑法規定了盜竊罪,所以行為人構成盜竊罪。再如,如果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絆人的故意,客觀上導致他人重傷的結果,但是刑法沒有規定絆人罪,所以行為人不構成犯罪。
因此,筆者提倡階層式犯罪構成的推理方式,一切的前提都是先確定行為是否形式上符合構成要件。此外,階層式犯罪構成從實質上確定刑法規范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在第二階層違法性中,因為違法的本質是行為侵犯法益,所以有且只有侵犯法益的行為才能構成犯罪。故意傷害罪保護的法益是人的身體健康,行為人的絆人行為危害了被害人的身體健康,因此結論是行為人構成故意傷害罪。正是有了前兩個層次的對客觀行為的認定,第三個層次有責性只需要判斷根據刑法規定,是否有人應當對此危害行為承擔責任的問題。例如,有單位通過破壞水表電表,達到少交水費電費的目的,數額巨大,有人認為,刑法沒有規定單位盜竊罪,單位不能作為盜竊罪的犯罪主體,因此這種行為不能構成犯罪。
筆者認為,應當先確定盜竊罪的構成要件,然后再判斷案件事實是否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從而得出是否構成盜竊罪的結論。顯然,這種單位盜竊的事實完全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因此對單位內的自然人應當按照盜竊罪論處,由于刑法不處罰單位盜竊,所以單位通過有責性進行排除。
定罪是一個三段論的推理過程,犯罪構成在這個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筆者認為,法官在設立大前提時,應當將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法定刑升格條件、犯罪主體的身份規定等一系列規范納入其中,然后從小前提案件事實到規范,再從規范到案件事實,對二者進行分析、比較和利益衡量。小前提案件事實離不開可能適用的大前提刑法規范的約束和指示,刑法規范也必需通過具體的案件事實進行解釋。案件事實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應當通過刑法規范設立的目的即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進行評判。司法人員只有掌握犯罪構成的相關理論和三段論的推理方法,才能對案件性質作出準確判斷,結論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和刑法保護法益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