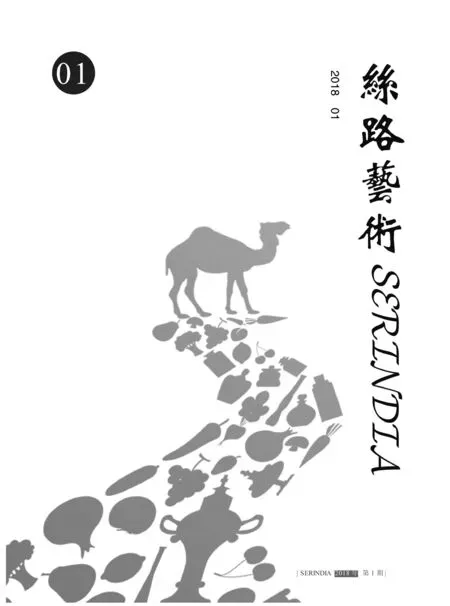看方聞《〈溪岸圖〉與山水畫史》
羅小雪
(山西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0)
一、研究方法
早在方聞之前就已經有用形式風格學來研究中國山水畫的學者高居翰,在《溪岸圖》的爭辯中,方聞以《〈溪岸圖〉與山水畫史》反駁高居翰對于山水畫形式筆法的一些錯誤認識,形式風格學是沃爾夫林用以分析西方古典主義與巴洛克藝術之間區別的作品,方聞創造性地將其用于中國畫的斷代。盡管《心印》的全名是《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但在研究過程中并不能完全像沃爾夫林一般完全摒棄圖像外的因素,在在中國傳統的藝術創作中,除去藝術家的個人意志外,影響藝術創作的因素還有很多,且中國常有“復古”這一傳統,各時代的畫家在相同的內容題材的影響下進行藝術創作,其中的差別往往很難辨別。
在《〈溪岸圖〉與山水畫史》中沿用了《心印》相似的研究方法,方聞以重建早期山水畫史及董源畫風格式在后繼畫家、收藏家的筆下的流傳狀況,與其說文章在鑒定《溪岸圖》真偽,不如說方聞試圖重構《溪岸圖》的創作成因,收藏狀況,和從師法董源的畫家們的畫中重建《溪岸圖》的流傳史,將《溪岸圖》置于五代宋初時代背景中了解時代背景,觀時人思想審美風尚,對了解當時繪畫面貌有幫助。這篇文章相對于《心印》的形式風格學,在內容的論證上更接近圖像學的研究方法。
沃爾夫林在研究西方古典主義與巴洛克藝術之間區別,提出了時代精神,民族特性和個人意志,在研究中國山水畫時民族特性是一致的,因此重點在時代精神和畫家的個人意志,在《〈溪岸圖〉與山水畫史》中的二、三、四五章節以整個時代背景為鏈接串起了董源的風格在畫史上的流傳,這一方面更接近形式風格學,因此從總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溪岸圖〉與山水畫史》是以形式風格為框架,部分加以圖像學的釋讀。
二、研究思路
文章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相互聯系互為論證,其中第一章節將《溪岸圖》的現存狀況,文章的整體思路是在以判斷《溪岸圖》真偽為目的,以串聯《溪岸圖》后的流傳史為線索,從傳世文獻(畫史、畫論)的記載、題材(流行與否與時代相聯系)、筆墨、皴法、題署、同時代的畫的類比。
從文章的一開始對鑒定《溪岸圖》的真偽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述,并對現階段認為是董源真跡的董其昌的題跋為證。從第一章節開始對《溪岸圖》的畫面內容進行描述①,并對前人的辯偽成果進行詳述。在第二章節中結合早于《溪岸圖》的山水畫的樣式、形式和題材和社會背景,對《溪岸圖》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境界的呈現有了合理的解釋,在這一章節中,方聞對比了同一時期山水畫的構成方式,認為《溪岸圖》的畫面構成符合10世紀的畫壇面貌。到第三章節具體到《溪岸圖》自身的繪畫風格和技法上分析從題署的真實性和書法的風格上符合這一時代的書法特性,在這一章節否定了高居翰所認為的筆法上的“含混不清”,在四章和五章對董源畫的主題和畫風畫法在元、明兩個時代被繼承和發展,并對各個畫家的生平和作品的風貌進行詳細描述。在最后一個章節對《溪岸圖》在近代的流傳進行了描述,并否定了當時國際上認為《溪岸圖》系張大千的偽作。將張大千的畫風進行描述,并將一張現代為王蒙的《青卞隱居圖》與《溪岸圖》對比進而得出結論。文章的結構條理清晰,盡管在辨別真偽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在一篇文章中講清楚傳承辯偽始末已經很難的了,且文章將涉及董源傳派的山水畫史進行了梳理,繪畫風格和藝術環境息息相關,重建了作品的歷史并論述了《溪岸圖》對后世的影響,對于辯偽而言不失為一個好的角度,好的方法。
三、小結
《〈溪岸圖〉與山水畫史》創作于二十世紀末的大都會博物館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會議期間,這場會議不僅對于《溪岸圖》的真假進行辯論,同時也對中國畫的的鑒定有了新的反思,傳統的中國畫鑒定一般依靠感覺和經驗,高科技的手段面對作偽高手的作品有時也無從下手,在現階段通過將風格形式的整理對中國畫斷代提供一些證據,無疑是更好的辦法。山水畫的“復古”傳統往往使得對山水畫的斷代變得困難,但是每個時代所蘊含的的時代精神仍會突破“復古”的局限,天才的藝術家們會在在臨摹與仿古中找到創新的養分,在自己的畫作中注入時代的精神。
隨著西方方法論與中國美術史學逐漸融合,各種方法論用于研究中國美術,有適合的也有不適合,方聞在這篇文章涉及多種研究方法,面對中國畫的鑒定,方法論的交叉使用已經是當前史論面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取各家之長說清楚一個問題是相當有必要的。
近年來隨著各大高校對西方方法論的教學普及,年輕的學者們對于用西方方法論研究中國繪畫已經逐步的有了新得,但是在早期為后人研究鋪下基石的學者們值得我們尊重和學習。
【參考文獻】
[1]薛永年.美國研究中國畫史方法述略[J].文藝研究,1989,(3)
[2]沃爾夫林.美術史的基本概念[M].潘耀昌,譯.2007年7月第一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3]方聞.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M].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