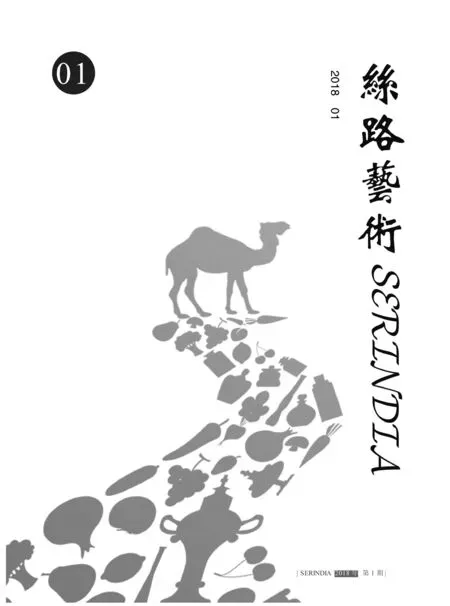航空承運人拒載乘客的法律責任
——以乘客身體狀況不適為視角
沈 然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200063)
一、實務案例
航空承運人因乘客身體狀況不適飛行而勸告乘客離機的情況一般以乘客已登機為前提,在機務人員主動發現或被動告知乘客存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通過請示機長并斟酌后,做出讓乘客離機的決定。這類案例在實務中并不少見,這會在乘客與航空公司之間引發爭議。
舉一真實案例,徐某參加旅游公司的出境旅游活動,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登上阿聯酋航空公司的某次航班,準備前往境外旅游地點,在等待起飛期間,徐某告知身邊同伴其腹部存在不適,其同伴便詢問乘務員有無藥物,機務人員得知后立即詢問徐某情況,后請示機長,最后做出讓徐某離機的決定。徐某當場表示不愿意離機,與機務人員發生爭執,僵持大約半小時后,徐某在機務人員的帶領下離開飛機,并辦理注銷手續,此事件導致飛機起飛時間的延誤。事后,徐某起訴航空公司要求獲得賠償,此事件也引發新聞輿論的關注。[1]
二、乘客與航空公司的主要爭議點
(一)乘客的民事權利
在航空公司因乘客身體不適勸告乘客離機時,乘客一般不會主動離機,最終通常呈現出乘客被迫離機的情況,就此引發乘客的民事權利受到航空公司侵害的爭議點。
實踐中,乘客主張受到侵害的民事權利包括名譽權和人格尊嚴等,相對應的,乘客在訴諸爭端解決時,會產生物質和非物質兩方面的訴求。非物質訴求即乘客要求航空公司進行公開或非公開的賠禮道歉,而物質訴求表現為乘客要求航空公司進行經濟性賠償,一般包括行程改變或終止產生的經濟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或賠償金和爭端解決的費用等。
(二)航空公司拒載根據
航空公司作為承運人單方面要求乘客離機一般是出于飛行安全等因素的考慮,通過犧牲少數乘客的個人利益保障飛機整體飛行的穩定安全。實踐中,一旦因承運人的拒載而產生爭議,通常會著重探討航空公司拒載的原因和根據,這是進一步判斷航空公司是否存在侵權行為或違約行為的重要依據。
(三)違約與侵權的抉擇
從侵害的權利角度分析違約與侵權的區別可以發現,違約行為侵害的是一種合同相對權,而侵權行為侵害的是一種絕對權,[2]雖然從表象上看,違約和侵權都侵犯一種權利,違反一種義務,但兩者實則屬于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適用不同的法律規范,因此,在將爭議訴諸爭端解決時,提交爭議方需慎重考慮選擇何種事由。
就航空公司勸告乘客離機而言,由于航空公司與乘客之間事先訂立載客合同(實踐中乘客出具航空公司出售的機票,即說明兩者之間具有合同關系),乘客可以憑機票提出違約之訴。另外,若乘客被迫離機后,認為自身的名譽權或人格尊嚴等民事權利受到侵害,也可以相應提出侵權之訴。
由此可見,違約與侵權之間并無定論,需要當事人根據自身情況做出選擇。
三、爭議點的法律分析
(一)航空公司拒載的違約性
乘客與航空公司的“約”通過機票表現出來,機票信息包括出發地、到達地、起飛時間和乘客的基本信息等,除此之外,還會明確指引航空公司的運輸條款,這一點常被乘客忽視。不同的航空公司會結合自身承運情況制定不同的運輸條款,乘客可以通過便捷途徑查詢到航空公司運輸條款的具體內容。
一般運輸條款基本都會涉及乘客身體狀況不適的處理,就前述阿聯酋航空的案例而言,該航空公司在運輸條款中明確規定,若因乘客身體原因導致承運人對其是否適合飛行產生疑問的,乘客應當提供健康報告等相關證明文件,并可由承運人決定其是否繼續飛行。該案中徐某并未提供證明自身健康適于飛行的文件,只模糊表示腹部不適且不能解釋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機務人員做出拒載行為是符合運輸條款規定的。
考慮到飛機航行的高度安全性,以及乘客在飛行中的身體健康和突發狀況下醫療救助的問題,不管是法律規定還是實務操作,航空公司在拒載的問題上保留較大主動權。很多航空公司在制定運輸條件時都采取了與該案中阿聯酋航空公司相同的做法,其實我國也有具體的規章規定,中國民用航空局于1997年修訂的《中國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國際運輸規則》中對此情況做了細致的規定,第五章“乘機”中的第29條詳細列舉了承運人拒絕運輸旅客及行李的情形,其第(二)項規定“旅客的行為、年齡、精神或者健康狀況不適合旅行,或者可能給其他旅客造成不舒適,或者可能對旅客本人或者其他人員的生命或者財產造成危險或者危害”。我國有關航空承運的相關規則基本上借鑒了國際慣例和條約的做法,因此,航空公司因乘客身體健康原因拒載的做法是符合國內外通行做法的。
實踐中,還可能產生運輸條款本身格式條款性質的質疑,進而引發航空公司免責的合理性問題。我國《合同法》第39條明確規定格式條款具有重復使用性、預先擬定性和非協商性,所以航空公司的運輸條款符合格式條款的特征。《合同法》第40條同時規定若格式條款具有法定情形或在免責的同時加重、排除對方權利情形的,格式條款無效。從該案航空公司有關乘客身體不適拒載的運輸條款規定看,其雖然免除或限制承運人拒載的法律責任,但實質是符合國內通行的航空運輸載客規定的,不具有違法事由,另外,該條款制定的初衷在于保護飛行安全和乘客身體健康,不存在《合同法》規定的加重乘客責任、排除乘客主要權利的情形,因此很難斷定航空公司格式條款的法律瑕疵。
(二)航空公司拒載的侵權性
侵權行為侵害的是一方享有的法定權利而非約定權利,航空公司與乘客之間是以機票為基礎的運輸合同關系,乘客登機到達目的地不被拒載的權利由合同約定,并非法定固有,因此若乘客基于侵權主張航空公司進行賠償是缺乏法律邏輯性的,這類案件一般應立足于違約而非侵權。
關于航空公司拒載行為是否構成侵害乘客名譽權和人格尊嚴的問題,需綜合考慮航空公司行為的合理性和乘客自身情況,根據我國法律規定,應當從受害人受損害的事實、加害行為、行為與結果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行為的主觀過錯四個方面來認定侵權,因此實踐中認定侵權的難度往往高于違約認定。
實踐中,航空公司一般不會毫無根據拒載乘客,會嚴格遵守航空運輸法律和條例規定以其自身運輸條款規定,難以認定其存在加害行為,另外,鑒于航空運輸的特殊性,要保證飛行安全和多數乘客利益,可能會犧牲或限制少數乘客權利,除非航空承運人故意拒載,否則很難認定承運人具有主觀拒載過錯,即使乘客被拒載后的確存在名譽或人格尊嚴受損的事實,也很難認定航空公司承擔侵權責任。
(三)拒載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情形,需要特定的人格權利遭受侵害。從上文分析可知,航空公司因乘客身體不適拒載的行為不能認定為侵權,也很難認定侵害乘客名譽權或人格尊嚴需要的構成要件,因此,乘客依據此法提出精神損害賠償仍缺乏事實和法律根據。
在航空運輸的賠償問題上,《華沙公約》、《蒙特利爾公約》和《海牙議定書》和國內的航空運輸規則都確立了直接和物質賠償的基本準則,并無賠禮道歉或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需強調的是,國際慣例一般限制航空承運人的責任,反對懲罰性賠償,由此可見,在該類案例中很難支持乘客精神損害賠償的訴求。
四、總結和建議
我國有關航班拒載的法律規定并不完善,《民用航空法》等并沒有具體的規定,實務中只能參照民用航空局的部門規章和《合同法》的規定,增加了法院判定的難度,未來仍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鑒于航空運輸的高度危險性,為確保飛行和乘客的安全,需要賦予承運人一定的主動權,并限制其責任,從本文分析可見,目前應支持承運人在特定情形下的拒載權,但也應進行相應約束,須審查拒載的正當理由,防止承運人濫用拒載權。[3]
參考文獻:
[1]孫黎.航空旅客運輸中承運人拒載的權利[J].人民司法,2009(1):67-68.]
[2]馬進.侵權行為與違約行為的比較研究[J].經營管理者,2009(9):31-33.]
[3]劉海安.航空承運人濫用拒載權的法律規制[J].法律科學,2015(7):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