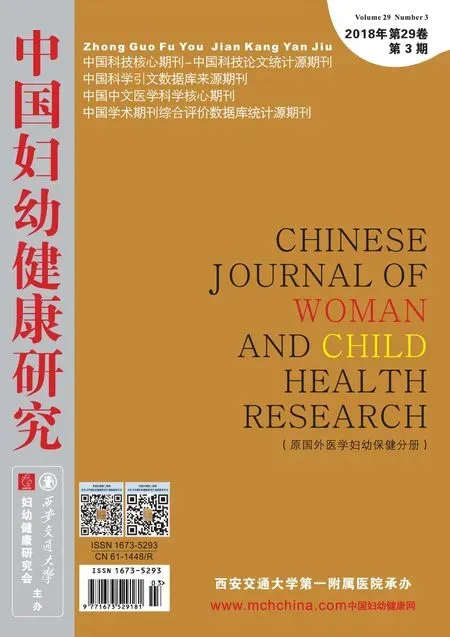父母產后抑郁與嬰兒氣質的相關性研究
,,,, ,
(1.安徽省馬鞍山市婦幼保健院,安徽 馬鞍山 243011;2.安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2)
產后抑郁是指產褥期發生的抑郁,其臨床表現情緒持續性低落、悲傷、易激惹,甚至是自殺等。因為與一般抑郁(抑郁、悲傷、沮喪、哭泣、易激惹、煩躁、甚至自殺等一系列癥狀為特征的心理障礙)調查的時間及工具不同,產后抑郁的發生率也存在較大差異。國外的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發現,母親產后抑郁的發生率高達35%[1]。此外,分娩作為一種重大生活應激事件,也可導致父親出現包括抑郁在內的情緒問題。目前,國內對父親產后抑郁的研究較少,國外也是在近年來開始關注父親的產后抑郁問題。日本的一項隨訪研究發現,父親在孩子出生后的前3個月抑郁情緒發生率高達17%[2]。產后抑郁的發生不僅影響著父母自身的健康,而且對子代體格、智力、行為等發育有著重要的影響[3]。本研究以氣質作為兒童早期行為發育的重要指標,探討父母發生產后抑郁對嬰兒氣質類型及相關維度的影響。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于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在馬鞍山市婦幼保健院婦女保健門診收集產婦建立產后抑郁隨訪隊列,對象主要來自為產后42天體檢且計劃隨后在本院兒童保健門診給兒童體檢的母親及其配偶。本次共有1 095對父母在產后42天體檢時完成產后抑郁篩查,根據知情同意且自愿加入原則,共有1 007名嬰兒的家長在嬰兒6~9月齡間完成氣質類型測試,隨訪率為92.0%。
1.2方法
父母產后抑郁、嬰兒一般人口統計學及嬰兒出生時情況等基本信息主要在產后42天體檢時由體檢醫生收集。①產后抑郁:運用《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EPDS),由父母于產后42天體檢時填寫,以進行產后抑郁篩查,將評分≥10分定義為存在抑郁情緒,根據篩查結果分為“父母均有抑郁”“僅母親抑郁”“僅父親抑郁”及“父母均無抑郁”4組,其中父母均抑郁52例,僅母親抑郁205例,僅父親抑郁54例,父母均無抑郁696例;②氣質測試:運用國內標化的《Carey嬰兒氣質問卷》對嬰兒進行氣質測定,于其6~9月齡間由主要撫養人填寫完成,共分為9個氣質維度,即活動度、節律性、趨避性、適應性、反應強度、心境、持久性、注意分散度及反應閾。根據各維度得分,將氣質分為4個類型:易養型、撫育困難型、發動緩慢型及中間型。
1.3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 Data 3.0建立數據庫,SPSS 13.0進行統計學分析,對計量資料進行t檢驗,對計數資料進行χ2檢驗。方差分析比較父母抑郁組間氣質維度均數分布情況;以氣質類型為因變量,父母抑郁及其他人口學特征為自變量,運用多項式Logistic回歸分析,計算OR值。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嬰兒氣質類型分布
本研究中各氣質類型以中間型較為多見,占41.8%(421/ 1 007);其次為易養型,占38.2%(385/ 1 007),撫育困難型占14.4%(145/1 007),發動緩慢型占5.6%(56/1 007)。比較氣質類型分布的人口統計學特征,父母文化程度、分娩方式不同嬰兒的氣質類型分布差異均存在統計學意義(均P<0.05),其中母親和父親文化程度較高,易養型氣質構成比越高,撫育困難型氣質構成越低,見表1。

表1 不同人口統計學特征變量嬰兒氣質類型分布比較結果[n(%)]Table 1 Comparison of distribution of infant temperament type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n(%)]

變量例數(n)易養型中間型撫育困難型發動緩慢型χ2P分娩方式?9.970.019 順產384159(41.4)145(37.8)65(46.9)15(3.9) 剖宮產及其他617224(36.3)273(44.2)79(12.8)41(6.6)是否早產4.580.205 是3516(45.7)9(25.7)8(22.9)2(5.7) 否972369(38.0)412(42.4)137(14.1)54(5.6)出生體重1.820.935 正常870334(38.4)361(41.5)124(14.3)51(5.9) 低出生體重218(38.1)8(38.1)4(19.0)1(4.8) 巨大兒11643(37.1)52(44.8)17(14.7)4(3.4)
注:*問卷填寫時漏填,變量有缺失值。
2.2父母產后抑郁與嬰兒氣質分布
本研究中母親產后抑郁發生率為25.5%(257/1 007),父親產后抑郁發生率為10.5%(106/ 1 007),分析嬰兒氣質類型在父母產后抑郁特征組間分布時發現,父母均抑郁組在撫育困難型和中間型的氣質類型發生率高于僅母親/父親抑郁及父母均無抑郁組,發生率分別為23.1%(12/52)和50.0%(26/52);僅母親產后抑郁組在發動緩慢型的發生率最高,為12.2%(25/205);父母均無抑郁組在易養型氣質的發生率為44.4%(309/696),顯著高于父母均抑郁或單一抑郁組。
比較不同父母抑郁發生組間嬰兒氣質類型分布發現,父母均抑郁、僅母親抑郁、僅父親抑郁及父母均無抑郁組間嬰兒4種氣質類型發生率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3.68,P<0.001);其中,父母均無抑郁組易養型氣質的發生率高于其他組,為44.4%(309/696),撫育困難型的發生率低于其他組為11.4%(79/696),父母均抑郁組撫育困難型的氣質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組,為23.1%(12/52),見表2。
比較不同父母抑郁發生組間嬰兒氣質維度分值時發現,趨避性、適應性、心境、持久性和反應閾5種維度均值在父母抑郁發生組間分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其中,父母均抑郁組嬰兒趨避性和反應閾均值高于其他抑郁組,僅母親抑郁組持久性、心境及適應性均值高于其他組,上述差異分布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2 父母產后抑郁組間嬰兒氣質類型分布[n(%)]Table 2 Distribution of infant temperament types among parent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n(%)]

表3 父母產后抑郁組間氣質維度分布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erament dimension average scores in groups
2.3父母產后抑郁與嬰兒氣質類型多因素分析
以嬰兒氣質類型為因變量,父母產后抑郁為自變量,單因素分析差異有顯著性的變量為協變量,進行多項式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父母產后抑郁是影響嬰兒氣質類型的重要危險因素。以父母均無抑郁組為對照,父母均有抑郁和僅母親有抑郁均是嬰兒撫育困難型氣質的危險因素,OR值分別是3.92和3.99,均P<0.05;此外,與父母均無抑郁組比較,僅母親抑郁與嬰兒發動緩慢型氣質顯著正相關,OR值為7.94,P<0.05。見表4。

表4 父母產后抑郁與嬰兒氣質類型的多項式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4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temperament in parents
注:以易養型為參照;*自變量對照組。
3討論
3.1父母產后抑郁情緒對嬰兒氣質發育的協同作用
既往研究廣泛地討論了產后抑郁對兒童心理行為發育的影響,但關注點多為母親產后抑郁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僅母親產后抑郁與嬰兒中間型和撫育困難型氣質正相關,與既往研究結論較為一致。紀艷麗等[4]研究發現母親產后抑郁的發生其子代在3歲時撫育困難型氣質的檢出率更高,并且趨避性、適應性、反應強度、情緒本質、注意分散度等維度評分明顯低于無抑郁組。本研究同時關注了產婦配偶在分娩后的情緒狀態,探討了父母產后抑郁的發生對嬰兒氣質的影響。通過分析發現,僅父親產后抑郁不是撫育困難型或發動緩慢型氣質的危險因素,而父母均為抑郁和僅母親抑郁組的子代氣質類型更可能是撫育困難型。
本研究發現產后父親抑郁的發生率為10.5%。王婷婷等[5]采用Meta分析方法評價了我國產婦配偶產后抑郁發生狀況時發現,產婦配偶產后抑郁障礙(PDD)發生率為13.6%(95%CI:8.7~21.3),與本研究的結果較為接近。父母產后抑郁對兒童的影響是深遠的,包括體格發育、智能發育、社交情感及個性形成等。氣質是兒童早期重要的發育行為指標之一。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發現,僅父親抑郁并未與嬰兒的氣質類型密切相關,但父母均抑郁可增加嬰兒撫育困難型氣質的發生風險。在分析氣質9個維度的均值時發現,父母均有抑郁組嬰兒在趨避性和反應閾2個維度上均值較高,外部行為可能表現的更敏感和認生。Ramchandani等[6]研究發現,父親產后抑郁與嬰兒氣質類型并無顯著相關,但父親抑郁組報告嬰兒哭鬧的情況更為常見,這與本研究的結果較為接近。
3.2產后父母不良情緒對兒童早期心理行為發育影響的內在機制
環境因素常被視為影響兒童早期心理行為發育的重要因素,母親不良情緒被視為是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之一。國內的諸多研究對母親產后抑郁影響兒童智能、情緒及行為發育取得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即認為其是兒童心理行為發育的重要危險因素。然而國內對男性配偶產后抑郁的認識不足,目前也僅僅是流行現狀研究,其對兒童身心發育的影響尚未得到重視。父母產后抑郁對兒童早期氣質及其行為表現影響的內在機制可能如下:①低落的情緒影響撫育質量下降,減少了與兒童的互動或對兒童的需求回應不及時甚至是忽視,同時對兒童懲罰性行為較多而鼓勵性行為較少,與兒童較難形成安全型的依戀關系[7];②處于抑郁狀態的父母,其自身調控情緒的能力變差,如長期存在這種狀態,對兒童的性格和行為發揮錯誤的“示范作用”;③父親抑郁影響家庭功能,尤其是配偶間的親密關系,可進一步導致母親產后抑郁癥狀的加重,形成疊加效應影響兒童心理行為發育。
目前,國內婦幼保健機構已逐步開展母親產后抑郁的篩查工作,但男性配偶產后的不良情緒狀態并未受到重視。為了進一步減少產后抑郁對兒童身心發育的影響,在此呼吁已開展孕產期心理保健的機構能同時關注男性配偶的情緒狀態,重視產后保健隨訪中產后抑郁的早期評估,以便于及時診治及干預[8]。
[1]Kirkan T S, Aydin N, Yazici E,etal.The depression in women in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period:a follow-up study[J].Int J Soc Psychiatry,2015,61(4):343-349.
[2]Suto M, Isogai E, Mizutani F,etal.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fathers: a reg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in Japan[J].Res Nurs Health,2016,39(4):253-262.
[3]Cents R A, Diamantopoulou S, Hudziak J J,etal.Trajectories of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predict child problem behaviour:the Generation R study[J].Psychol Med,2013,43(1):13-25.
[4]紀艷麗,康春梅.產后抑郁情緒與學齡前兒童情緒關系的相關性研究[J].護理研究,2017,31(20):2524-2526.
[5]王婷婷,徐陽,李戰戰,等.中國產婦配偶產后抑郁的發生率及其與產婦產后抑郁關系的Meta分析[J].中南大學學報(醫學版),2016,41(10):1082-1089.
[6]Ramchandani P G, Psychogiou L,Vlachos H,etal.Paternal depression: an examination of its links with father, child and family functioning in the postnatal period[J].Depress Anxiety,2011,28(6):471-477.
[7]Smith-Nielsen J, Tharner A, Steele H,etal.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security at one year:the impact of co-morbid maternal personality disorders[J].Infant Behav Dev, 2016,44:148-158.
[8]石英,趙銀珠,游川.保健隨訪對降低產后抑郁癥發生率的影響[J].中國婦幼健康研究,2011,22(2):153-155.
[專業責任編輯: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