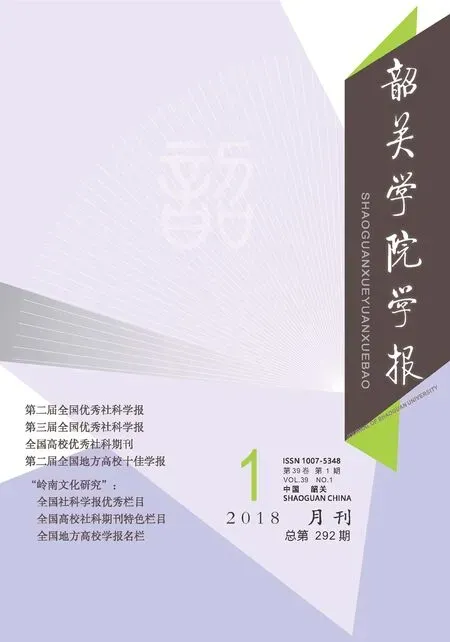論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知識產權地方立法保護
——以韶關市為切入點
宋貽珍
(韶關學院 法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是世界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及其相關的實物和場所。“非遺”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從2005年國務院第一次提出要進行非遺保護至今的12年里,我國已建立起縣級、市級、省級、國家級的四級非遺保護名錄,尤其是2011年6月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使我國非遺保護上了一個新臺階。目前審批通過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已經達到了1 372項。對非遺的保護,應該傳承與發展相結合。本文以韶關市為切入點,論述非遺創意項目不僅需要國家法律與政策的保護,更需要地方知識產權立法和政策的支持。
一、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必要性
具有二千多年歷史的韶關市,文化底蘊悠長而豐富,既有馬壩人遺址及石峽遺址為代表的古文明文化,也有以南華寺為代表的佛教禪宗文化;既有以珠璣巷、圍屋、瑤寨為代表的民族民俗文化,也有以張九齡、余靖為代表的名人文化;更有以丹霞山、南嶺國家森林公園、廣東大峽谷等為代表的山水文化等。這些文化中,既有祖先留下的物質文化遺產,更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的文化層次分明而各具特色,有待進一步挖掘與承傳。地處粵北山區的韶關,歷來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全市轄有一個自治縣(乳源瑤族自治縣),一個民族鄉(始興縣深渡水瑤族鄉)。全市現有少數民族43個,人口約5.5萬人。眾多的少數民族長期生活在這里,形成了豐富多彩、異彩紛呈的民俗文化和獨具特色的民族舞蹈、音樂、戲劇和傳統技藝。
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類型多樣,數量豐富。目前韶關市級以上非遺名錄已有60項,其中省級17項,龍舞(香火龍)、粵北采茶戲、瑤族盤龍節、瑤族刺繡、瑤族民歌等國家級5項。擬申請和正在申請的至少還有50多項。這些項目幾乎涉及非遺項目所有的種類。二是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分布相對集中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韶關地區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乳源瑤族自治縣、始興縣、南雄市、曲江區、翁源縣、仁化縣、樂昌市、武江區等8個縣(市、區)。已受保護的非遺項目基本來自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例如,乳源瑤族自治縣擁有10項非遺,韶關地區5項國家級非遺中,乳源縣就占了3項(《瑤族盤王節》、《瑤族刺繡》、《瑤族民歌》)。三是反映地區的歷史文化,有較高藝術文化價值。例如,粵北采茶戲是廣東粵北地區的小戲劇種,淵源可溯至唐宋,盛行于明代嘉靖年間,它是在民間燈彩歌舞的基礎上吸收贛南和湖南益州民間藝術精華創造而成的地方民間主要戲曲。瑤族刺繡是過山瑤在漫長的社會發展中積累形成的傳統技藝,反映了瑤族的歷史、家庭、宗教和生活等方面,是過山瑤“五彩文化”的縮影。南華誕廟會又稱六祖誕廟會,自唐代以來,已有1 300多年的歷史,成為中國佛教南禪宗的重要節日。四是面臨消亡和失傳。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承傳性、口頭性和可塑性特征[1],更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社會經濟發展快,人口流動十分頻繁,韶關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斷,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斷消亡,更多瀕臨失傳而亟需保護。例如,瑤族刺繡、仁化土法造紙技藝等,都是純手工制作,十分精美,但費時耗力卻沒有對等的經濟價值,如不加以保護就面臨被淘汰的命運;而許多靠口頭和行為傳承的風俗和禮儀、傳統音樂、戲劇曲藝、舞蹈等,如鬧春牛、扛阿公、石塘月姐歌、翁源煙花戲,等等。隨著現代化進程,也被年輕人視為落后老土而拋棄,或者不愿接手繼承而面臨失傳。
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我們民族千百年來生活和歷史發展的印記,每一項都生動描繪著我們從古到今的生活細節,同時也閃爍著民族智慧。沒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族,是缺少文化根基的,是淺薄的,也是沒有民族驕傲的。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挖掘和保護必須全方位得到重視。
二、韶關市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現狀
韶關市“非遺”十分豐富多彩,對“非遺”的挖掘、保護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機關及其政策,對挖掘出來的非遺項目,包括已經獲得各級名錄保護的項目,主要是進行靜態非生產性的保護,未能很好的進行產業化利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論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國務院、文化部、工信部、財政部制定了《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這些文件都強調對傳統文化必須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注重實踐與養成、需求與供給、形式與內容相結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產生活各方面。文化部有針對性地實施了一些研培計劃以及振興傳統工藝計劃,這些實踐證明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確是行之有效的非遺保護措施。
開發非遺的創意項目,建立起“文化+貿易”、“文化+創意”、“文化+科技”等融合發展新業態,正是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具體化,應該大力提倡并從政策、經濟、法律各方面加以支持,其中地方立法的支持尤為重要。但是從韶關市目前狀況看,在開發和保護非遺的創意項目方面,尚存在諸多問題。
(一)非遺文化創意意識淡薄,未能充分調動社會積極性與創造性
《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責任。因此,應該堅持全黨動手、全社會參與,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各項任務落實到農村、企業、社區、機關、學校等城鄉基層。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也應該積極參與文化資源的開發、保護與利用,生產豐富多樣、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質文化產品,擴大中高端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但目前,不少人的思維方式仍然停留在文化是事業,應該“以文養文”這個慣性思維中,管理模式不能與時俱進,對非遺的宣傳和利用大多局限于展覽和公益性演出,未能在韶關地區興起構建非遺創意項目的熱潮,沒有將非遺創意項目作為朝陽產業加以培育發展,導致非遺創意項目不多。
(二)非遺的傳承與發展面臨著挑戰
有些屬于我國的非遺項目被某些西方國家搶先進行了生產性開發、產業化利用,使我國非遺的傳承與發展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例如,2005年,韓國搶注“端午”為世界文化遺產;2006年,日本公司搶注我國古典四大名著游戲商標;2005年,韓劇《大長今》里反復強調“針灸”首先產生于韓國;2008年,美國夢工廠把中國的“功夫”和“熊貓”合成動畫電影《功夫熊貓》。這些原本屬于中國非遺性質的元素和文化,遭到肆意剽竊和盜用,還有一些中國非遺項目被國外申請了商標、專利保護,而反過來限制了我國的正當使用。種種現象表明,我國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開發與保護任重道遠。
(三)非遺文化創意機制不健全
雖然按國家有關規定,對非遺保護也應該做到“五納入”,然而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五納入”是指要將非遺保護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財政預算,納入體制改革,納入各級領導責任制。只有做到有機構、有人員、有經費、有制度、有措施,非遺保護工作才能有序開展,非遺文化事業才能快速發展。但是從目前來看,存在資金投入不足、人手不夠、制度不健全,缺乏激發非遺文化創意的有力措施。整個韶關文化產業尚無合理的投融資政策支撐,短期行為較為普遍,與外地重復的項目或粗制濫造的項目比較多[2]。
(四)對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開發嚴重不足,尚未形成非遺文化創意產業的平臺
由于上述原因,導致韶關地區非遺文化創意項目開發嚴重不足。目前,除了配合旅游業的丹霞文化、佛教禪宗文化和古人類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以外,多數富有韶關特色的非遺項目資源仍處于閑置狀態。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創意人可劃分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兩大類。營利性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創意人是指依法成立的以營利為目的的自負盈虧、自主決策的企業、公司、機構、個人等;非營利性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創意人是指那些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旨在完成文化藝術事業或使命的組織,如博物館、圖書館、文藝團體或傳承人等,也包括政府機構在內。韶關現有的一些非遺創意項目往往由政府部門主導和主辦,企業、社會團體作為創意人比較少。另外,具有創新性的人才十分稀缺,這也成為非遺文化創意項目開發的阻礙。韶關地區尚未形成非遺文化創意產業的平臺。
三、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知識產權地方立法保護的邏輯自洽
非遺文化創意項目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部分,是指以創新為前提,以非遺文化為內容,以科技為手段,形成對非遺項目的開發和運用的知識密集型、智慧主導型經濟項目[3]。當今,文化創意產業越來越占據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地位,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產業部門。國家大力鼓勵和提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非遺文化創意項目不僅是保護、傳承、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手段,而且還是增加當地經濟收入,提高當地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
因此,非遺創意項目地方知識產權立法保護必須注意以下幾個邏輯自洽問題。
(一)把握好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創新”尺度
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絕大部分,如獨具特色的民俗和禮儀文化、口口相傳的民族舞蹈、音樂、戲曲等都可以與著作權法規定的“民間文學藝術”相對應,本身就受著作權的保護。而“傳統技藝”部分,可以適用《商標法》或《專利法》加以保護。但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意項目與一般文化創意項目相比,有其不同之處。對非遺項目的創新,必須在全面把握非遺項目的完整性基礎上,在不改變該非遺的基本或實質性特點的前提下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創新,使該非遺項目既能保持原汁原味,又有時代的新意。例如,對乳源瑤族服飾的創新,必須先把握乳源瑤族刺繡的特點、染印特點、服裝花色裝飾特點等三方面,凡對任何一個特點進行了實質性改變,就不是乳源瑤族服飾了。試想,把瑤族刺繡改為蘇繡,把瑤族服飾上的花色放在漢服上,還能稱為瑤族服飾嗎?又如“石塘月姐歌”是韶關市仁化縣石塘村女性群體中一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民歌。歌詞用石塘獨有的方言演唱,具有濃厚的唐朝宮廷的唐韻。假若創新,變成男子用普通話演唱,甚至完全去掉了唐韻的特色,那么還能說是“石塘月姐歌”嗎?因此,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必須把握好尺度,創新要有原則和底線。
(二)界定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權利主體
借鑒2014年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的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屬于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中的成員基于傳承目的以傳統或者習慣方法使用本民族、族群或者社群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無需征求許可和支付費用。對成員的創新性使用是否應該征得許可并未作規定。但一般認為成員的創新就是該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的創新,因為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作為一個群體,其對非遺文化的承傳創新活動都是經由具體的成員在長期的生活中習慣行使完成的。由此,可以推定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創意人并非都是非遺創意項目的權利人。如果是具有著作權的特定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中的內部成員開發出以“非遺文化作品”進行創新或改編為主要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則創意人不對創新或改編后的非遺文化作品享有著作權,該著作權仍屬于原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如果是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之外的人要開發以“非遺文化作品”進行創新或改編為主要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則必須先征求該特定民族、族群或者社群的同意并支付許可使用費,但創意人在得到許可后可享有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著作權。
這個界定標準卻不適用于以對傳統技藝的改進為核心所完成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也不適用于以非遺產品商業營銷創意為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如對隆盛醬油釀造技藝、南雄釀豆腐制作技藝、苦爽酒釀造技藝進行改進,在技術方面有重大突破,使傳統產品味道更好,無論創意人是否是該特定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中的內部成員,皆可就改進的技術申請專利保護從而成為專利權人。這是因為,對傳統技藝的非遺保護,僅限于著作權方式,也就是說,傳統技藝的非遺權利人,得到的權利僅僅是一種著作權法規定的權利,而非專利法或商標法保護的權利,所以非遺中的傳統技藝,并不受專利法保護。自然,任何人都可以對這種傳統技藝進行創新并對創新后的技藝申請專利并獲得專利權。同理,以非遺產品商業營銷創意為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創意人,則可以通過注冊商品商標或服務商標的方式,成為商標專用權人,獲得商標法保護。
(三)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知識產權地方立法應遵循的原則
針對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知識產權地方立法,首先,在現有的《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的基礎上,制定適合韶關地區的地方法規。其次,在傳承和發展韶關非遺文化的前提下,制定促進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法律法規。最后,地方知識產權立法應該注意與其他立法及政策的協調,真正起到充分調動廣大群眾對非遺文化進行創新的社會積極性。
四、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知識產權地方立法的具體對策
(一)設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審查程序,規定非遺文化創意項目中的“創新性”標準
一方面,對是否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設立明確的審查標準。我國對非遺的保護不以得到立項核準為前提,沒有立項核準的非遺仍然是受《著作權法》自動保護的,但如果這些沒有立項核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發生糾紛,起訴到法院,就有個認定問題。而我國對非遺的認定沒有明確規定,地方立法可以參照國家和國際公約對非遺的定義,規定一個具體的認定標準。另一方面,對是否符合“非遺文化創意項目”設立審查標準。為了保持非遺文化的原貌和完整性,非遺文化創意項目中的“創新性”以及對“創新性”的限制,都應該有明確的標準,即對非遺項目的創新,必須在全面把握非遺項目的完整性基礎上,在不改變該非遺的基本或實質性特點的前提下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創新,使該非遺項目既能保持原汁原味,又有時代的新意。
(二)立法須清晰地界定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權利主體
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包括三種:一是以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為內容的創意項目;二是以傳統技藝為內容的創意項目;三是以對非遺文化進行商業營銷為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不同的類型,知識產權權利主體不同,其權利歸屬也有所不同。
首先,由于民間文學藝術著作權屬于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以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為內容的創意項目,分為兩種情況:第一,如果是具有著作權的特定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中的內部成員開發出以“非遺文化作品”進行創新或改編為主要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則創意人不對創新或改編后的非遺文化作品享有著作權,該著作權仍屬于原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開發出創意項目的成員因此可以獲得獎勵。類似于著作權屬于單位的“職務作品”。第二,如果是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之外的人,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進行創新或改編,開發出以其為主要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則必須先征求該特定民族、族群或者社群的同意并支付許可使用費,但創意人在得到許可后可享有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著作權。
其次,由于我國對非遺文化的保護目前僅限于著作權法保護方式,以對傳統技藝的改進為核心所完成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創意人,以及以非遺產品商業營銷創意為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創意人,無論是否是該特定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中的內部成員,皆可成為權利人。即創意人可就改進的技術申請專利保護從而成為專利權人,獲得專利法保護;或者可以通過注冊商品商標或服務商標的方式,成為商標專用權人,獲得商標法保護。但是,傳統技藝屬于商業秘密,創意人在對傳統技藝進行改進之前,應該征得原非遺文化權利人的許可,簽訂保密協議并支付使用費。以非遺產品商業營銷創意為內容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創意人,也應該征得該非遺文化權利人的許可并簽訂許可協議。
總之,應該以知識產權地方立法方式,將創意人及其權利歸屬一一分別明確規定,以避免糾紛。
(三)制定地方知識產權促進法
在該法中,對包括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在內的專利商標申請費用給予資助,對企業的包括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在內的知識產權管理進行培訓,完善非遺文化創意項目在內的知識產權估值,引導銀行與投資機構開展投貸聯動,積極探索專利許可收益權質押融資等新模式,積極協助符合條件的創新創業者辦理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改善因為資金的匱乏而導致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缺乏產業化平臺形成的局面。
(四)建立區域立法協作模式
設立地方立法協作機構,一方面審查立法機構立法人員的資格,另一方面協調各地區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更好的保證地區間立法一致的特性。避免地方知識產權立法與地方非遺、經濟、旅游各方面政策制度產生矛盾的現象[4]。開展立法與非遺文化相關知識的多樣化宣傳普及、培訓等,把提高群眾的非遺文化意識和創新意識作為常態的法制工作,以逐步改變對非遺文化及其創意項目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普遍薄弱的現狀,打造良好的非遺文化保護環境。
總之,對非遺文化的保護以及對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保護,不能一味尋求政府政策保護的方式,而應該把重心逐步放在法律保護上來。只有形成嚴密的系統化的法律保護網,才能真正使瀕臨絕境的非遺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生機。對非遺文化創意項目的知識產權地方立法,就是將項目的傳承保護與創新相結合,促使人們積極轉變思維,解放思想,提高對非遺文化創造性保護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知識產權地方立法,突出資源優勢,打破資金瓶頸,發展非遺文化創意產業,使非遺文化不僅得到承傳發展,而且為地方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喬曉光,蘇歡.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傳承——基于非遺社會實踐與現象的觀察思考[J].文化遺產,2017(1):4-10.
[2]陶宇華.加快發展文化產業——以廣東韶關為例[J].現代商業,2009(29):53,52.
[3]周怡,馬永雙.杭州文化創意產業知識產權保護地方立法研究[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3(13):60-62.
[4]衛學之.地方立法起草主體的實踐反思與規制路徑[J].河北法學,2017(8):18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