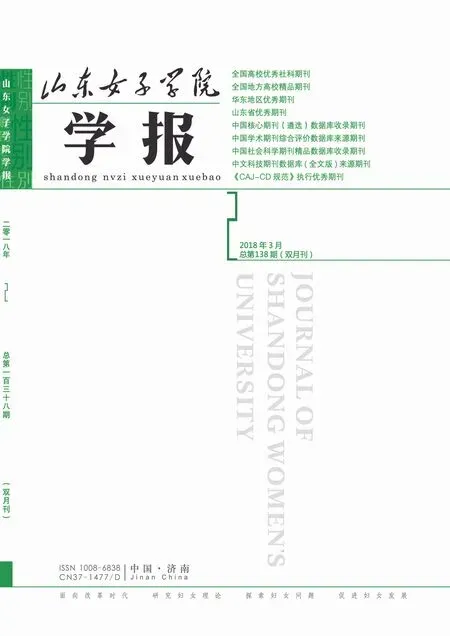新社會風險下的中國婦女福利:挑戰與應對
黃桂霞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婦女研究所, 北京 100730)
性別角色與家庭機構和功能的轉變,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使得新世紀的中國家庭尤其是女性面臨新的風險,其發展面臨更大的挑戰:一方面,人口老齡化、育兒精細化需要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家庭照顧,而勞動力市場、職業發展需要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多的時間投入,工作-家庭沖突問題更加凸顯,使得兼顧家庭的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相對弱勢;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深化以及中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家庭模式的改變,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原有的單位/工作保障減少,使得在勞動力市場處于相對弱勢的女性獲取保障的能力更差,不利于她們分享社會發展成果。這就需要我們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國家、社會、家庭密切合作,共謀男女平等、社會發展大計。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新社會風險是指1970年代以來,主要工業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由于社會結構變遷而出現新的社會需要,它包括勞動力市場變化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子女撫養和老人護理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帶來的風險,因超出福利國家風險范圍而進行福利改革政策所引起的新的社會風險。朱利亞諾·博諾里(Giuliano Bonoli)將“新社會風險”分為三類:不斷增加的工作量與傳統的家庭責任之間矛盾的激化;勞動力市場帶來的結構性失業,使得知識型社會中低技能工人隨時可能遭遇到失業和貧窮陷阱;職業生涯中斷的弱勢群體社會保障的不足[1]。
傳統的福利保障的是和市場經濟運行相關的風險,比如養老、工傷等,目的是促進社會再生產,勞資雙方都能從社會保障中獲益,核心群體是有穩定就業和連續就業的工人,其實是以男性為主的,所以,面臨新社會風險的主要群體是女性,尤其是有家庭照顧負擔無法平衡工作-家庭矛盾沖突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對她們的挑戰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新型勞動力市場需要終身學習,個人發展與職業發展都需要在勞動力市場投入更多,但同時家庭育兒精細化、人口老齡化又加重了家庭照顧負擔等,使得工作-家庭的沖突越來越激化;二是性別平等使得女性對職業發展帶來的社會地位與自我認同的追求越來越高,男女平等不斷推進,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加主動,更注重自我發展,與傳統性別角色定位的矛盾深化;三是女性因家庭照顧責任而中斷職業導致的社會保障不足。
經濟全球化、勞動力市場化以及福利國家的改革使得新社會風險的責任越來越分散到個體家庭及女性個人。作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照顧責任的增加以及保姆市場求大于供的困境,都使其需要在照料孩子與贍養老人方面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尤其是養育3歲以下嬰幼兒的職業女性,從子女照顧和發展的角度出發,一部分女性選擇暫時中斷職業,專職撫養嬰幼兒,甚至退出勞動力市場,加入到失業大軍行列,這使其不僅當期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還直接影響了其以后的職業發展和對社會保障的享受;還有一部分女性為了協調家庭責任和工作之間的關系,選擇了不利于職業發展的兼職工作或者靈活辦公的低職、低薪工作,但大部分兼職工作收入較低、保障較差,就低工作也使得女性的社會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另外,女性社會地位和人力資本的提高使其在勞動力市場占有一定的優勢,婦女對家庭的依賴性降低,離婚率和單親母親數量增加,而單親母親進入勞動力市場又遭遇很多傳統的障礙,面臨新的風險。應對以上挑戰的核心是化解工作-生活沖突,解決途徑就是平衡工作-家庭之間的矛盾,其實,工作-生活平衡主要是在這兩個領域內時間的分配以及在兩個領域作為勞動者和照顧者責任承擔的平衡,這也是婦女福利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新社會風險下中國婦女福利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勞動市場變化增大女性就業和職業發展風險
就業是女性獲得社會保障的重要基礎。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就業采取國家統分統招的形式,不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而且有各種制度保障同工同酬(當時,工資基本就是全部收入),國家還為雙職工家庭提供了方便易得的家庭可支付甚至免費的公共托幼服務以及職工食堂等,解除了婦女就業的后顧之憂。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政府和單位提供的托幼公共服務不進而退,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無形之中加重了目前中青年職工的老年人照料負擔,在家庭照料負擔和勞動力市場需要之間,婦女的就業矛盾更加凸顯。
市場經濟的深化給女性就業帶來的挑戰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就業權問題。職業要求提高,但家庭照顧服務支持不足,女性就業困難增加。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效率優先的勞動力市場,需要高人力資本的勞動者,且需要勞動者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但女性因家庭照顧分散大量精力,因生育造成人力資本貶值,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相對弱勢地位[2]。性別不平等和性別歧視在就業市場的加劇使得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境遇下降,再加上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比較中立,使得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回歸家庭不僅是家庭經濟的選擇,也是部分女性抵御風險和解決性別身份認同危機的出路[3]。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本身就失去了福利的主要來源,而且市場勞動收入越來越高,不參與勞動市場的女性與參與者相比失去的更多。
另一個是收入的性別差距。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女性收入僅為男性的62%,2017年中國在經濟和教育方面的性別平等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職業技術工人”與“高等教育入學率”兩個指標上已經實現了完全的性別平等。中國女性的每天工作時長為男性的1.09倍,且花在照顧家庭等無報酬工作上的時間占總勞動時間的44.6%,而男性的這一比例僅為18.9%。在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漸提高,甚至高等教育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專業技術人員女性比例也略高于男性的當前,女性為了平衡家庭-工作沖突,而更多地選擇了靈活、勞動強度較小但收入也相應較低的職業。
收入存在性別差距的另一個表現是績效工資的差異。在2017年的一項涉及13個省市2萬多職工的調查中,男女職工認為同工同酬的比例均超過80%,管理者中同工同酬的比例達到91%。國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機關事業單位同工同酬的比例在90%左右。“同工同酬”的比例之高與收入的性別差異之大形成鮮明的對比。透過現象看本質,事實上,同工同酬,同的是基本工資,而目前收入的內容更加豐富,比如績效工資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更高,也恰恰是與勞動力市場密切相關的這一部分工資存在明顯的性別差距。當收入不再僅僅是基本工資,而越來越多的與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相關聯時,以基本工資為標準的同工同酬可能就不再是個問題,或者這個問題變得不再明顯,因為它已被不平等的績效工資淹沒了,但收入的性別差距依然存在。所以,女性的就低就業、兼職與彈性就業、無酬家務勞動尤其是家庭照顧責任,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處于相對劣勢、收入較低的主要原因。
(二) 育兒精細化、人口老齡化增加家庭照顧需求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職工福利有相當大部分是針對婦女的高就業而無力承擔家庭照顧責任而提供的,單位保障的體制可以為女性勞動者提供家庭照顧,減輕她們的家庭照顧負擔,比如為職工生活提供便捷、減輕家務勞動的集體宿舍、公共食堂、托兒所等集體福利設施。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重點轉向經濟發展,為減輕財政負擔,弱化了公共福利的提供,甚至從很多公共服務中退出,為在職女性提供的平衡工作-家庭的福利措施也一并取消,家庭照顧責任重新轉移到家庭中的女性身上。城鎮保障以就業為導向的社會保險為主,婦女工作-家庭平衡面臨雙重壓力,市場經濟甚至驅逐了部分女性勞動力。農村的社會保障在一段時間內僅有較低水平的救助性的社會福利,而且至今依然不夠完善,只有基本的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生育相關的保障和育兒相關的保障政策近乎空白,農村婦女面臨更重的家庭照顧和養育負擔。
獨生子女政策下的中青年女性,上有老下有小,照料負擔越來越重。一方面兒童照料需求猛增。不僅是日常照料的精細化要求提高,養育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養育專業化要求越來越高,全職工作的女性想成為一個合格的媽媽非常困難,從早教到各種興趣班、學習班,家長需要全程陪同。另一方面預期壽命的提高與健康壽命的不同步,導致老年失能人口增多、失能時期延長,家庭照料負擔增加。自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趨勢掉轉,減少了345萬,而60歲以上老年人增加了891萬,2014年,又增加了594萬。這其中有三成甚至更多需要長期照護的失能老者,照料需要激增。2015年我國80歲及以上人口大約2300萬人,2035年將超過5000萬,2055年將超過1億人[4]。
育兒精細化以及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加重了家庭照護負擔,制約了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投資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擠出”了用于學習和教育的精力、時間和金錢,也加大了經濟活動人口的壓力。這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家庭成員外出勞動提高家庭經濟收入;另一方面又需要勞動者增加勞動力市場的投入,增加工作時間,以彌補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帶來的供給缺口,同時加大勞動強度、提高人力資本要求,以應對不斷升級的勞動力市場需求,這在現代服務業、知識生產領域等技術含量較高的企業更常見。這些都加重了工作-家庭沖突。
(三)福利供給模式變化凸顯工作-家庭矛盾沖突
工作-家庭沖突是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原因。當經濟壓力較大或者社會高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時,家庭往往會成為被忽視或放棄的一方,當家庭照顧需要較多、經濟壓力較小、個人職業發展期望較低時,工作、職業發展容易被忽視,但當家庭照顧需要較多、個人職業發展期望又高時,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會凸顯。
人口老齡化需要維持高就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進入市場,少子化、低出生率,更迫切需要成熟的婦女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深化,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工作的靈活性和可變通性卻越來越差,單位可以提供的時間和經濟保障越來越少,女性需要用勞動力市場的經濟收入來換取家庭照顧的時間,否則就會被勞動力市場淘汰。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伴隨的是婚姻越來越不穩定、不安全,家庭的照顧、福利功能日漸衰弱,女性的家務勞動尤其是照顧勞動得不到補償甚至不被承認。勞動力市場變遷和家庭穩定性下降,使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增加,她們亟需在社會上求得自身的發展、獲取一定的社會地位與身份;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其在勞動力市場的定位也發生變化,其職業發展需求越來越強。
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實現了經濟獨立,減少了對家庭的福利/經濟依賴。但職業女性在工作中的投入影響了她們在家庭中作用的發揮,尤其是照顧工作的投入減少。勞動人口中女性數量的增加,引發兒童看護以及老年看護的社會化,公共服務需求增加[5]。而現有的福利體系尤其是公共服務沒有給予積極及時的回應補充,女性兼顧工作家庭這種多任務耦合的概率越來越低,導致家庭決策也更傾向于市場的選擇,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很多女性甚至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做起全職媽媽。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顯示,從事非農勞動的女性因生育中斷職業的比例不斷增加,并且逐年大幅升高,女性在1981~1990年生育的職業中斷比例為10.3%,1991~2000年生育的職業中斷比例為21.2%,2001~2010年的這一比例為35.0%。社會發展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女性卻無力平衡工作-家庭沖突而被動退出勞動力市場,大部分職業女性深陷勞動力市場與家庭的矛盾之中,工作-家庭矛盾平衡成為新社會風險下女性所面臨的核心命題。
三、平衡工作-家庭沖突的國內外實踐經驗
質高價廉的公共服務可以讓父母將工作和育兒結合起來,豐厚的育兒津貼可以減輕家庭照顧負擔,讓家庭有更強能力從市場上購買照顧服務,從而保障育齡女性的勞動就業權,也可以更好地保障15~64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外通常將與生育相關的女性就業權利保護作為政府實現平等就業和反歧視、家庭-工作平衡支持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進行了嬰兒照顧津貼的探索,1950年代雙職工家庭開始大量涌現,尤其是197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城鎮雙職工家庭成為主流,黨和政府出臺系列法律政策,減輕婦女家庭照顧責任,使她們能夠安心從事社會勞動,較少工作-生活沖突。
(一)公共服務支持解除職業婦女的后顧之憂
對積極參加有薪酬工作的母親給予社會支持,其主要體現在國家在減輕家庭照顧的負擔上提供服務支出的水平,特別是花費在家庭主婦照料兒童和老人上的支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主要是采取發展多種多樣的托兒組織來為雙職工家庭提供照顧支持的,尤其是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舉辦的托兒所、幼兒園,為了方便職工接送子女,除了在職工居住集中的地點和辦公地點開辦比較正規的托兒所、幼兒園外,還會在工地開辦臨時托兒所,以減少職工送托子女往返路程的勞頓和時間,托兒所和幼兒園的費用直接由職工所在企業支付,少數單位不方便建托幼園所的職工,可以將子女送往個體托兒所或幼兒園,管理費則由職工所在工作單位報銷。據北京市統計,1949年初有托兒所11處,收托兒童340名,到1955年底,托兒所、幼兒園發展到791處,是1949年的近72倍,收托兒童4萬名,是1949年的117倍[6]。這些托兒機構,對于發揮婦女的勞動積極性,提高生產和工作效率發揮了極大的積極作用。
平衡有酬工作和家庭責任早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就是德國關注的問題了,當時政府認同并強調男女平等和婦女自立,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綠黨都主張增加婦女對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度,承諾要“平衡協調工作和家庭關系”,主張擴大公共社會服務。法國在支持照顧兒童方面較為突出,1999年此方面的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3%,比如政府通過稅收減免方式鼓勵企業建立自己的托兒所。在英國,主要通過稅收減免和私人機構提供護理支持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在2000年正式注冊的63.4萬個兒童護理機構中,有55%是由注冊的私人兒童護理員提供的,41%是由私人托兒所提供的[7]。
采取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提供公共育兒服務,減輕女性育兒負擔,以擴展女性潛在工作空間,也是一些發達國家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的方式。比如,韓國政府向在工作場所建設育兒設施的雇主提供不超過7億韓元的長期低息貸款,給予育兒中心建設和運行必要的信息、咨詢及部分開支支持等①。法國政府向工作的父母提供廉價高質量的育兒服務,比如開放免費的保育院②。1970年代,瑞典通過擴大社會服務和日間護理機構解決兒童照料問題,并實施了6小時工作制,支持夫婦雙方都工作的家庭,幫助婦女從母親和家庭主婦轉變成為獨立的個體。
(二)育兒補貼減輕家庭照料負擔
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對嬰兒照顧補貼進行了探索。1931年勞動法規定,由社會保險基金支付嬰兒補助金,用來購買小孩十個月所必需的物品和牛奶。1941年陜甘寧邊區規定,生育婦女可以領取分娩津貼及小孩津貼,女工所帶小孩每月發給帶乳費。太行區在1948年的規定中增加了雇傭人的費用支付項目,為太行區工作的婦女干部產前產后提供假期、糧食待遇,并且提供麻紙50張,棉花1市斤,小米70斤,作為生產及雇傭人的花費;男干部之妻生產時則一律給小米50斤,作為雇人之用[8]。為雇人提供費用,在保障孕產婦自身權益的同時,也為嬰兒享受更好的看護提供了基本條件,這在當時世界范圍內都是難得的高水平的保障。
國外尤其是歐洲很多國家政府通過稅收減免和直接補貼來降低育兒服務的相對價格,增加育兒服務的可及性,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法國2004年對有3歲以下孩子的家庭增加了育兒補貼,Givord和Marbot在2015年研究發現,這項改革平均減少了家庭50%的育兒開支,增加了女性大約1%的勞動參與率。Bettendorf 等(2015)對荷蘭2005年改革[9]的研究顯示,改革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2.3%,每周工時平均增加1.1小時。挪威政府對于找不到育兒中心的1~2歲兒童提供超過9000美元的現金補貼。澳大利亞通過實施育兒津貼和育兒稅政策來幫助家庭減輕育兒成本。在法國,1980年代擴大了對公共日間護理中心的投資,1987年政府還提供了兒童津貼,鼓勵婦女在家照看子女,1990年代,政府對雇用他人照顧子女的家庭提供補助,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家庭護理。
(三)靈活辦公時間,為家庭照顧提供支持
國外在靈活辦公方面有著比較豐富的經驗。一方面是削減工時,即生育女性在一段時間內可以每天工作,但工作較短時間。這樣既避免了女性長期遠離勞動力市場,也便于其保持自身工作技能以及重返工作崗位,對于保障女性就業權利有較好作用。在瑞典,生育女性可以以削減3/4、1/2、1/4或1/8正常工作時間的形式休產假(分別享受3/4、1/2、1/4或1/8的產假補貼),也可以以削減最多1/4正常工作時間的形式,休產假直到孩子滿8歲②。新加坡還推出了兼職計劃,每天正常工作,但每周工作時間減少;每天工作,但是工作更短時間;也可以自選工作時間,如一周工作一周休息;也可以混合采用。
另一方面是靈活工作時間,即指除“核心”時間外,靈活掌握上下班時間。早在1998年,新加坡Abacus國際私人有限公司就規定,雇員可以在7:30~9:30的任意時間開始工作,在4:30~6:30的任意時間下班。這種工作方式在不增加企業工資成本的同時,延長了工作場所的運作時間,也為女性雇員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提供了機會,對增強女性工作動機、提高企業生產率和員工忠誠度都有積極作用。
中國目前的削減工時主要針對育有未滿1周歲嬰兒的女職工,用人單位在每天的勞動時間內為女職工安排1小時哺乳時間,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1個嬰兒每天增加1小時哺乳時間,哺乳時間算工作時間。為女性緩解嬰幼兒照顧與工作沖突提供了較好的支持。每天減少的勞動時間可以分開哺乳使用,也可以晚到或早退相應時間。對于有學齡兒童的家長,有的地方有家長會假,比如北京市規定可以在工作時間去開家長會,工資照發,評獎不受影響③。
四、新風險下中國婦女福利發展的應對策略
在公共領域更受重視的社會中,作為促進社會穩定與性別關系兩性發展的動力機制,婦女福利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已有保障女性就業權的系列法規政策,但平衡工作-家庭的政策措施明顯不足,新社會風險下,不僅需要轉變婦女福利發展理念,還需要政府、市場與家庭共擔福利責任,將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納入性別視角,制定可持續的家庭友好政策,為婦女提供高質量而且可以負擔得起的兒童照顧服務,考慮婦女“家庭照顧”的津貼,提供家庭照顧服務,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婦女福利[9]。
(一)轉變婦女福利發展的理念
中國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新社會風險的保障,新社會風險除了面對市場風險外,更多的是要滿足與人口再生產密切相關的需求,比如兒童照料。因此,需要新的社會福利理念和制度來化解。
一是將社會福利從基本權利向人力資本投資轉變。缺乏兒童照顧設施不僅是影響母親就業和女性職業發展的一大障礙,也是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的主要因素。應對新社會風險的平衡工作-家庭矛盾沖突的婦女福利、兒童福利政策,其實是通過擴大勞動力隊伍和勞動力的可雇傭性、提高市場效率以及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來支持經濟競爭力,通過支持性的社會供給創造社會投資,而不是補償性的福利轉移,僅僅增加福利消費的負擔[10]。因此,針對婦女尤其是家庭中兒童養育的福利,比如為幼兒提供照顧津貼,不僅僅是幫助家庭尤其是婦女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使其有更充沛的精力和更高的效率投入到全職工作中,充分發揮女性人力資本價值,而且是政府和社會對勞動力市場的一種補償和投資,是有利于勞動力市場有效運作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
二是將有酬工作與非正式照顧相結合。非正式照顧工作降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或者參與度,但是非正式照顧也是現階段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因此,重置有酬工作與非正式照顧的關系,通過增加工作生涯的彈性將有酬工作與非正式照顧結合起來,是目前化解工作-家庭矛盾的最有效方式。可以與私人服務提供者合作,引入非正式看護的福利以及正式與非正式捆綁形式的福利。
(二)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婦女福利
人口快速老齡化以及低人口出生率,使我國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推動中國勞動力市場迎來劉易斯拐點,要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轉向“人力資本紅利”的再創造,婦女成為化解這個問題的理想的勞動力后備庫。但是質高價廉可得的公共照顧支持或者是普惠性的育兒照料津貼的缺乏,成為影響婦女就業的主要障礙,需要政府幫助職工尤其是女性協調職業發展與家庭照顧負擔。因此,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家庭政策和性別平等問題實質是一個國民經濟問題。
一方面,要推動經濟發展,在發展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彌補婦女福利發展的短板。經濟發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水平也決定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客觀實力與能力[11]。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還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另一方面,需要提供針對女性的公共就業服務,創造平等的就業機會,保障婦女平等參與勞動力市場,減少女性在就業過程中的性別歧視,提高婦女人力資本投資,提供消除性別歧視的雇傭保護,促進女性多渠道就業創業,不斷提高婦女就業質量和收入水平,實現婦女更高質量的就業和更充分就業,縮小收入上的性別差距,使廣大婦女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三)國家回歸:為工作-家庭平衡提供支持
國家除依靠以就業為基礎的社會保險制度很難解決不平等和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外,還需要一系列的社會政策平衡社會發展與社會平等。因此,社會政策的設計不僅要滿足社會發展需要,也要兼顧家庭需要和婦女個體發展需要。
首先,將社會政策納入家庭視角,建立家庭友好型政策,提供更多的家庭服務支持。家庭穩定是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它為家庭成員提供必要的照顧與保護,因此,當家庭照顧功能弱化時,需要國家與社會給予一定的支持。一方面可提供更多的照顧補貼和靈活的工作時間與假期。時間和精力的沖突是工作-家庭沖突的核心,靈活的工作時間、工作方式和更多更靈活的休假——育兒假、陪產假以及家庭事務緊急假等可以較好地滿足照顧需求,而足夠的經濟支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市場服務替代家庭照顧服務,比如可給困難職工提供家庭照顧津貼或者補助。另一方面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支持,尤其是質高價廉易得的公共托幼及養老服務。人口老齡化與獨生子女政策,加重了核心家庭的照料工作,職業崗位對工作效率和工作時間的要求,需要創建更能適應在不斷變化的工作生活中照顧兒童的形式,比如時間更長、更靈活的照顧提供。獲得照顧應該是兒童的法定權利,政府需要整合資源強制性地組織這些照顧活動,這不僅能滿足兒童權利,也可滿足雙職工家庭的照顧需求。
其次,提高女性教育收益率以及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承認家庭照顧的社會價值。一方面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經與男性不相上下,但因為照顧家庭而選擇就低就業,降低了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和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國家需要給予平等就業政策,以充分發揮女性人力資本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為平衡家庭照顧,成為靈活就業、兼職就業的主體,導致其社會保障的缺乏,國家需要承認家庭照顧的社會價值,與有酬工作一樣,給予相應的社會保障,比如,將照顧兒童的成本“社會化”,對養育兒童的母親變相支付和增加養老金賬戶基金等。
(四)打破男權:平衡家庭照顧責任
家庭是福利的主要組織者和實施者,尤其在非制度化福利供給中,是福利資源最重要的來源,承擔著不可或缺的福利功能,其福利角色主要體現于老人照顧、子女養育、情感慰藉等。在我國,家庭照顧在福利中依然保留著傳統的基礎地位和提供模式,主要由女性承擔福利給予,尤其是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和責任絕大部分是由女性來承擔的,這些直接影響了她們在社會上從事有償勞動的時間和精力投入,也成為女性社會參與的障礙。缺乏有償勞動的機會,女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分享社會福利的權利。
新時代,廣大女性追求男女平等、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快速進入勞動力市場,并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與男性共同奮戰在社會各個領域的前沿,當女性的活動領域不再局限于家庭,家庭照顧責任在不同成員之間的分擔就成為平衡工作-家庭沖突的一個顯性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研究表明,經濟上不活躍而陷入貧困高風險的原因,男性主要是生病和殘疾,婦女則主要是家庭責任拖累④。因此,應協調工作和家庭生活,讓更多的男性參與到家庭事務中,更多地承擔照顧責任,讓更多的女性尤其是母親能從事有酬勞動,不僅為勞動力市場作貢獻,也可以減少婦女尤其單親母親貧困,為社會減貧作貢獻。
(五)社會支持:婦女福利責任的再平衡
家庭核心化趨勢使得家庭照顧功能弱化,作為基本照護服務供給和消費的最小單元,家庭提供照顧服務的能力不斷下降,社會介入兒童照料問題、彌補家庭照料不足成為必然。
在計劃經濟時期,單位為參與社會勞動的家庭提供了較好的公共服務支持,尤其是托幼服務,而且職工大部分能居住在單位附近,即使單位福利不足,女性也可以就近很好地照顧家庭,加之當時人均壽命相對較低,且有一定的單位福利,老年照顧負擔也較輕。改革開放以來,原本屬于政府責任的服務供給職責逐漸被轉移給家庭,同時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離工作場所較遠的地方,往返交通一方面占用了很長的有效時間,另一方面也使得單位保障功能難以實現。例如北京,嚴重擁堵的交通讓很多人選擇了更加有時間保障的公共交通出行,即使單位能夠提供托管服務,過度擁擠的公共交通工具也無法攜帶嬰兒到單位托管,這就需要社區提供相應的照顧支持服務,以替代家庭的部分照顧功能。
當然,用人單位的責任也不可推卸。當社會文化倡導女性履行大部分照顧孩子的責任,并鼓勵男性發展公共領域的能力時,必然會妨礙女性發展她們的潛能,導致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勞動力市場不僅要為女性參與社會生活和實現經濟獨立提供就業機會和途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還要在保證單位績效的情況下,為有家庭照顧需要的職工提供工作-家庭平衡支持,比如靈活的辦公方式、相對彈性的工作時間等。
注釋:
① 改革始于2005年,具體內容包括提高育兒補貼水平(減少家庭育兒開支50%,把補貼范圍擴大到幾種不常見情形,在接下來的5年增加3倍育兒公共開支),增強低收入父母稅收優惠力度等。
② 參見《SFS 2006:442》第四到第八部分內容。
③ 參見北京市頒布實施的《關于職工參加學生家長會可作公假處理的通知》,北京市勞資字第311號。
④ 參見ONS(2002b)NDLP: Statistical Release to September 2002。
[ 1 ] 余南平,梁菁.新社會風險下的西歐國家工會[J].歐洲研究,2009,(4):85-106.
[ 2 ] 黃桂霞.男女不平等:從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J].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7,(4):1-8.
[ 3 ] 吳小英.主婦化的興衰——來自個體化視角的闡釋[J].南京社會科學,2014,(2):1-8.
[ 4 ] 鄭秉文.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7——長期護理保險試點探索與制度選擇[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7.53-55.
[ 5 ] 安內莉·安托寧,陳姍.北歐福利國家遭遇全球化:從普遍主義到私有化和非正式化[J].社會保障研究,2010,(1):1-15.
[ 6 ] 1956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員會關于執行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代表關于“增加托兒所、托兒站數量,提高質量,加強對托兒所、托兒站的監督管理”提案執行情況的報告[R].北京市檔案局,檔案編號110-001-00566-211。
[ 7 ] Anne Daguerre.ChildcarePoliciesinDiverseEuropeanWelfareStates[A]. Klaus Armingeon,Giuliano Bonolieds.ThePoliticsofPost-industrialWelfareStates:AdaptingPost-warSocialPoliciestoNewSocialRisks[C].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06,216-221.
[ 8 ] 太行區嬰兒保育、產婦保健暫行辦法草案(1948年7月1日)[A].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C].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256-257.
[ 9 ] George , V., Page, R.ModernThinkersonWelfare[M].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5.236.
[10] [英]彼得·泰勒-顧柏.新風險、新福利:歐洲福利國家的轉變[M].馬繼森,譯.北京:中國勞動保障出版社,2010.167.
[11] 黨的十九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7.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