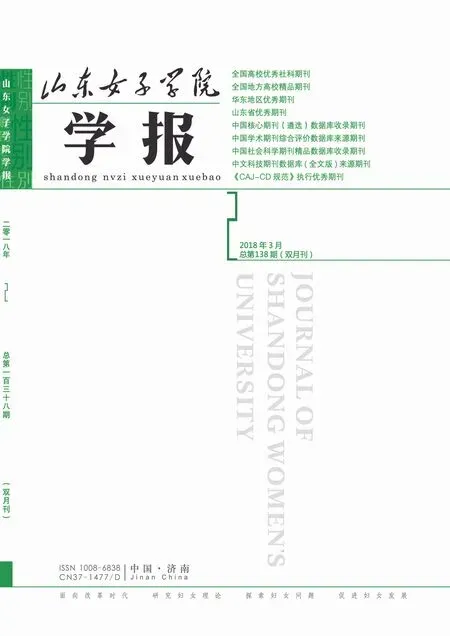近代蘇州鄉村女性的兼業
陳艷君
(安徽財經大學,安徽 蚌埠 233041;蘇州大學,江蘇 蘇州 215123)
學術界對近代江南鄉村女性的職業和生活情況已經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①,而民國時期蘇州鄉村女性的兼業,尤其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蘇州轎婦,還沒有充分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本文在廣泛收集留存的貧乏史料基礎上,以近代江南社會轉型為研究視角,從民國蘇州鄉村女性的兼業背景、兼業類型和特點及在家庭生計中的重要意義等方面考察民國蘇州鄉村女性的生活圖景。
一、近代社會轉型與蘇州鄉村女性兼業的變化
中國傳統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導致小農占有耕地的缺乏和普遍貧困化,小農生產的特性和貧困化壓力迫使農民必須尋求副業才能維持生存,兼營各類副業成為他們謀生的天然出路,幾乎所有的小農戶家庭都緊緊抓住兼業這一謀生手段,進行一些“如紡織業、小商業、小手工業等的具稟賦優勢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1]。這種兼業既可以在農戶住所中,也可以外出兼職,或者是從事小商小販等。農戶的兼業幾乎伴隨小農經濟存在的始終,與社會經濟生活的轉型和發展相互影響。
在近代以前,江南鄉村女性的兼業主要是從事絲棉紡織業,杭嘉湖寧紹以及蘇錫鄉村地區以絲織業為主,蘇松地區以棉紡織業為主。很明顯,這種職業分工“是與地區經濟作物類型相聯系的。”[2]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不斷沖擊和近代中國社會的大變革中,江南地區首當其沖,近代化因素不斷被引入江南社會,近代工業和交通的興起,社會生活的變化,使江南社會轉型日益深入,對鄉村女性的兼業既形成了沖擊,也帶來了機遇。
首先,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侵入和江南近代工業化的進程,沖擊了鄉村家庭手工業,改變了傳統家庭手工業的生存環境。由于產品價格、質量等競爭不過機制品,傳統家庭手工業遭到排擠,尤其是紡紗業及手工繅絲業衰落較為明顯,逐漸被排擠出市場,被機制品所代替。織布業亦發展艱難,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作為江南鄉村女性傳統兼業重要內容的絲棉紡織業,“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3]。“家家都把布機、紡車停止起來,藏到灰塵堆里去了”,所以,大部分女子“都拋下梭子,去做‘男人家’的事,即作長工,當‘腳色’,而男人們的勞力反而漸感多余無用起來。”[4]尤其是19世紀3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爭相向中國傾銷過剩的工農業產品,中國國內農產品價格急劇下降,而江南與世界市場的聯系較之國內其他地區更為密切。此外,隨著社會的進一步動蕩,江南鄉村經濟日趨蕭條,農民收入不斷減少,入不敷出,農村經濟日益破產。而苛捐雜稅繁重,各種支出又增多,農民負擔加重,在日益加深的貧困化壓力下,蘇州鄉村女性也不得不為家庭生計奔波勞作。作為小農家庭重要的輔助性謀生手段,鄉村女性的兼業必然出現此消彼長的發展。
其次,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既給鄉村女性兼業帶來了復雜沖擊,同時,近代社會轉型也為蘇州鄉村女性兼業的新發展提供了機遇。近代化帶來了交通和生活方式的顯著變化。隨著更方便的新式交通工具,如火車、汽車、輪船的通達,江南城鎮的外來旅游者越來越多。蘇州具有明顯的區位、交通優勢。蘇州北依長江,西抱太湖,依江瀕湖,河網如織,四通八達,又有大運河之便,地理位置優越。加之《馬關條約》簽訂后,蘇州被辟為通商口岸,以及作為上海的外圍地區,深受上海核心區的輻射,加快了社會近代轉型的進程。蘇州歷史悠久,名勝古跡頗多。“蓋蘇垣筑自吳王闔閭,閱時千百載,城郭依舊,然丘陵猶昔。湖山之勝,風物之美,既甲于吳,亦軼于浙。用是每逢春秋佳日,山塘七里,游人如織;而四方人士之來游天平、穹窿、靈巖諸勝者,尋幽探奇,踵趾相接”[5]。民國時期的蘇州,開始把旅游業“作為當地發展的一條主導性道路,吸引了很多城鄉冶游者們的目光。”[6]旅游業在客觀上為廣大蘇州鄉村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家庭外的就業機會,她們兼業與獲取收入的渠道更加多樣化。民國時期“在他處所不易經見”的甚至被視為奇風異俗的蘇州轎婦,便是蘇州天平山下附近鄉村女性兼業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蘇州轎婦的肩扛生活
每年的春秋兩季,是去蘇州天平山旅游的好時節,游人“終日不斷于送”。天平山在蘇州西南方向,從閶門雇船到楓橋鄉登岸,再有六七里路程即可抵達,但由于這段路程車馬不能通行,需要走路,或者乘坐當時唯一的交通工具——椅轎。因此,游人都會有一個出乎意料的發現——有很多女轎夫。每每船還沒有到天平山腳下,在路邊等著的轎婦就會跟著船在岸上跑著說價錢。她們一看見船在石橋邊靠岸,就飛快跑向岸邊,用吳儂口音搶著說:“轎子要吧?坐轎子上山去吧!”[7]如果有不坐者,她們必定尾隨其后,喋喋不休,并告客曰:“奴嘸不男人。苦惱。坐子去罷……”[8]她們輕巧而熟練地扛著椅轎,在沿途不停地向上山的游客爭攬生意。
那些特殊的轎子其實只是用一張竹椅子裝上兩根竹桿,周圍并沒有圍障,加上乘客的重量,都在一二百斤之間。都說“蘇州女兒嫩如水”,而蘇州天平山附近的那些轎婦,她們大多從十五六歲的時候便開始練習抬轎子,起初開始抬轎子的年輕女子,一般多選擇比較瘦小的女乘客,或是小孩子,等到慢慢地有了經驗,體力也增加了,她們一天便可以多抬幾趟,也不再挑選游客,只要是肯出錢的,她們都爭相接攬。她們的皮膚都粗糙枯黃,腿和手臂都很壯碩,襯托著寬闊的肩膀和臀部,已經絲毫沒有了人們想像中的蘇州女人的柔弱風度。
如果價錢說好了,客人坐上去,她們抬著轎子就走,如果客人太重,便由三個女人輪換著抬。她們抬轎的本領非常不錯,即使肩頭負荷著上百斤的重擔,上山下山,在曲折的山路上亦如履平地。1934年8月11日《申報》上的一篇游記生動地描繪了蘇州天平山下轎婦抬轎時的情景:上山的時候一共雇了4頂轎子。抬轎的人中女子占了6個,“伊們是一樣的壯健,……其余的二位男子漢,卻是一對煙霞城中的俘虜。憔悴,瘦弱,猥縮”。由他們的言談和稱呼中得知,兩個煙鬼竟然是其中兩個少婦的丈夫。翻過兩個山頭,走了大概十多里路,“一對煙鬼,當然是全不中用,累得要命。可是6個婦女,卻始終健步如飛。但大汗也已似潮水一般從額上滾到嘴邊,濕透了頸背,滲入了衣褲,全身如洗了個澡,熱氣蓬勃地發散著。伊們立刻把外衣脫去,只留著一件短小的襯衫,豐滿的乳峰,抖抖地似乎要跳出襯衫外面來了……”[7]這是一種艱苦的體力勞動,她們往往以停下讓乘客看風景為借口休息一會。1946年5月23日《申報》上的一篇游記便記載了游客的體會:久聞蘇州轎婦抬起轎子來健步如飛,而據自己的親身體驗卻并不盡然,“我注意到前面的那一個,盡是把轎桿在肩膀上移動著。她將轎桿斜放在兩肩上面(或者不如說她扭轉了肩膀承著那堅硬的轎桿),所以老是有點歪來歪去”,她們抬了沒有多長時間就停下了。問她們為什么停下來,她們異口同聲地說:“看景致呀”,我聽見別人的轎夫也是這么被她們放下來了。于是我們茫然地看了一會景致,然后又坐上轎去[8]。
由于春秋兩季正是農閑時期,轎婦們抬山轎可以掙得一筆不錯的收入。尤其是每到星期日,城里的人出外休閑旅游,便是轎婦掙錢的大好機會。力量大的轎婦一天可以抬三四趟,力氣最弱的一天也可以抬兩趟。最初要價僅一元半元而已,然而“迨至半山,則又索點心錢。及歸,再索不已。客憫其苦。慨然與之”[9]。但因為常年戰亂、災荒等導致經濟蕭條,大部分游客都不大肯坐轎,往往一整天沒掙到錢的轎婦也很多,她們空等乘客的焦慮,自然也都是可以想得到的。《申報》上曾記載了1946年蘇州轎婦的收入:由于“抗戰以來當推今年的游客為最盛”,她們平均每天約有15000至16000元收入,如果雨水不多,天氣好,“就能扯到兩三萬了”[10]。
三、家庭貢獻與家庭地位的不對等
蘇州天平山轎婦的本職工作是耕田,是像別的地方的男子那樣下田工作。“在那田間,有點點的青布頭巾一起一伏,這是農婦在播種,一撮撮的豆或是一撮撮的麥,從她們手中點入土中,埋伏著未來的萌芽,而為人類的養料所仰給。”[11]即使下雨了,雨水打濕了她們的衣服和身體,她們也依然繼續在雨中勞作。秋收打稻的工作,也全是由婦女完成。但是天平山附近多山,土地生產力薄弱,游人多的春秋二季,抬山轎,就逐漸成了她們的一個兼業。雖然辛苦,至少終有幾毛錢可掙。
除了抬山轎的兼業外,蘇州轎婦還有一些零碎的兼業,例如紡織、刺繡、砍柴和織草鞋等等,有的就在山腳下擺一個小攤,貨品有她們用樹枝砍成的手杖、水果、糕餅、汽水和香煙,這是“她們傾銷自己的土產,招攬顧客的必需品”[12]。刺繡的兼業,是她們世傳的技藝。上海暢銷的顧繡,實際上全是出自她們之手。顧繡莊派跑街下鄉,把工作交給她們,再約定時間來取。但是工資很低,一天只有二三百錢。所以天平山的游客會見到那些等活的轎婦,她們身旁都架放著繡花的繃子,沒有游客或者價錢談不好,她們就坐在那里刺繡,可謂粗活細活樣樣拿手。她們唯一的目的,“便是用勞力換取‘老爺’‘太太’‘先生’‘小姐’荷包里的金錢以補生活之不足”[13]。
那么,天平山附近的男人們在做些什么呢?他們除了種些山田之外,以打獵為副業,……他們把打獵換回的金錢,“除了捐外,便在‘太白遺風’的小酒店里消磨整年的傍晚,晚上呢?給卅二張骨牌迷住了心”[12]。他們大部分時間都不出去工作,很多人都有煙癮、嗜好紅丸,要么就是泡在茶館里。他們能找到的工作就是為人開山搬石頭,而開山搬石頭的男人,更是沒有一個不吃鴉片或吞紅丸的,他們的工資是三天一元錢,可是一元錢只夠他們在鴉片或吞紅丸方面消費兩天。因此,“不僅他們衣食住的費用,要逼迨著妻子們做牛做馬來供給,便是他們的鴉片煙,也要熬煎著妻子們的血汗來吞吸”。而在蘇州的這些旅游名山附近的村落中,營業特別興旺的便是酒館、茶館以及煙館等場所。“年青的漢子們,盡有整天的盤桓在內的。高興時,還可暢快地賭一陣子。這么著消耗掉的金錢,卻都不是用自己的血汗去換來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向出賣著勞力的妻子們,所壓榨得來的。自然,家中的開門七件事,不用說得,是完全由妻子們維持著的。”[13]
蘇州轎婦的勞動對家庭生計的維持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她們在家中的權利與此卻是極不相稱的。她們的丈夫“毫無羞愧地從勤苦的女人手中不勞而得來錢,養活自己,而更令人發指的是,他們一點不知儉省,一味縱任著自己的劣性情,吃喝呀,嫖賭呀,任所欲為,假使賭輸了,或受了外邊的氣,回家還找尋老婆出出怨,不是打就是罵,做女人的,總是忍受,除了自嘆命苦之外,是不加以些微反抗。她們雖是粗糙女子,但因為出身良家,對于服從丈夫的傳統觀念,不敢也絕沒有存心去破壞它”[14]。
四、經濟地位與家庭地位
外界的變化對近代蘇州鄉村女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惡劣的生活環境下,她們并沒有自怨自艾,也沒有將商品經濟的浪潮拒于千里之外,而是以各種方式向傳統農業以外拓展新的就業渠道。蘇州轎婦兼業的發展是近代社會轉型引發的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她們的兼業具有多樣性、重要性的特點。她們對家庭生計具有重要的意義,保障了家庭的基本生計需要。都說蘇州人是享樂的,蘇州女人是嬌生慣養的,可蘇州天平山附近的鄉村女性幾乎比任何地方都勞苦,為了養家,她們總是不停息地出賣著自己的勞動,貼補一年的家用,難有片刻清閑。
近代社會轉型對婦女地位的變遷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婦女就業“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變革之一”[15],為婦女地位的變遷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蘇州轎婦無疑應該享有平等權,可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由形式上瞧來,這種出賣勞力而維持丈夫吃喝的妻子,不啻是丈夫們的奴隸”,但是事實上呢,“丈夫們由妻子們供應著吃喝,那分明妻子們,應處于主人的地位。但是相互著的主子奴才,卻大家能相安無事,而且能頗有歷史的維持著這么個制度,這真不能不說是蘇州風土志中的一個奇跡。”[13]
這種畸形的家庭制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傳統父權制家庭結構的影響下,我國傳統法律沒有賦予女性財產繼承權,宋元明清時期,女兒在分家制度中的權利也僅限于“在成長時受撫養和出嫁時得到一份嫁妝”[16],確切說是賜予,而不是女性的法定權利。“非其父母特別給予,不許在遺產上主張任何權利”[17]。在婚姻家庭中,女性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與父為女綱、夫為妻綱、子為母綱對應的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近代社會轉型的影響下,出于反封建的需要,提倡遺囑自由,但是男女繼承權仍然不平等。女性意識的覺醒也推動婦女界不斷進行爭取財產權和繼承權等法律權利的斗爭。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案》明確規定了女子有財產繼承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也積極貫徹這一主張。但只是部分承認了女子的繼承權,仍然排斥已婚婦女的財產繼承權,以財產論“應指未出嫁女子與男子同一繼承權”[18]。至1930年,才正式確認女子的繼承權,規定配偶與子女一樣有繼承權,同時也承認“女子對個人財產有完全處分權”[19]。盡管民國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女子的繼承權,但在現實生活中女性財產繼承權并沒有獲得良好的保障。
盡管近代鄉村女性通過各種兼業途徑,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甚至整個家庭生活依賴她們的收入貼補才得以維系。但是在中國農業社會中,土地才是家庭的主要財產,而土地是按照男系原則傳遞的,由于女性沒有土地的繼承權,經濟地位也就沒有保障。因此在家庭地位方面,沒有土地的妻子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和丈夫相提并論。她們“一方面是生育孩子,一方面是擔任烹飪針線等家里的雜務”,此外,“還要下田,(負責)曬谷子,喂豬等較輕的農作”[20]。儒家傳統倫理道德要求她們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應盡的職責只是孝女、賢妻、良母以及順婦,甚至是成為節婦。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是和傳統父權制家庭結構下的經濟地位相統一的,所以在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中,鄉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仍然是相當困難的。蘇州鄉村女性竭力適應近代社會轉型的沖擊,為家庭生計艱難而堅韌地奔波勞作,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破除封建舊習,提升女性家庭和社會地位依然任重而道遠。
注釋:
① 主要成果有:小田《江南鄉村婦女職業結構的近代變動》,《歷史檔案》,2001年第3期;小田《論近代性江南村落女紅》,《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3期;張佩國《近代江南鄉村婦女的“財產權”》,《史學月刊》,2002年第1期;王慶國《以竹枝詞為視角看近世以來江南鄉村婦女生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小田《近代江南村婦的日常空間》,《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第2期。
[ 1 ] 王亞娟.傳統農業社會農戶兼業化行為趨向的效率分析——兼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J].人文雜志,2002,(1):65-70.
[ 2 ] 小田.江南鄉村婦女職業結構的近代變動[J].歷史檔案,2001,(3):107-113.
[ 3 ]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M].北京:三聯書店,1957.165.
[ 4 ] 陳凡.寶山農村的副業[J].東方雜志,1935,(18):104-106.
[ 5 ] 陸璇卿,顏大圭.旅蘇必讀:首集[Z].吳縣市鄉公報社,1922.16.
[ 6 ] 馮賢亮,林涓.民國江南城鎮的現代化變革與生活狀態[J].學術月刊,2012,(10):146-154.
[ 7 ] 朱維明.蘇州天平山下的抬轎婦女[N].申報,1934-08-11(15).
[ 8 ] 蔡釣徒.蘇行拾趣[N].申報,1929-05-03(21).
[ 9 ] 錢公俠.蘇州的女轎夫[J].雜志,1944,(6):46-47.
[10] 君宜.蘇州的女轎夫[N].申報,1946-05-23(8).
[11] 孟暉.蘇州散記——農業都市的剪影[J].民間,1936,(2):18-20.
[12] 沈右銘.山游拾得[J].十日談,1934,(29):187-189.
[13] 周賢.蘇州的女轎夫[N].申報,1936-04-11(14).
[14] 江鳥.蘇州天平山的女轎夫[J].婦女雜志,1941,(4-5):28-30.
[15] 王紀芒.女性的角色變遷及其對婚姻家庭的影響[J].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1,(3):14-17.
[16] 白凱.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33.
[17] 鄭全紅.民國時期爭取女子財產繼承權的社會思潮與觀念變遷[J].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6,(1):45-50.
[18] 劉王立明.中國婦女運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57.
[19] 梁景和,等.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嬗變研究(1919~1949)[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58.
[20] 費孝通.祿村農田[A].費孝通文集:第二卷[C].北京:群眾出版社,1999.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