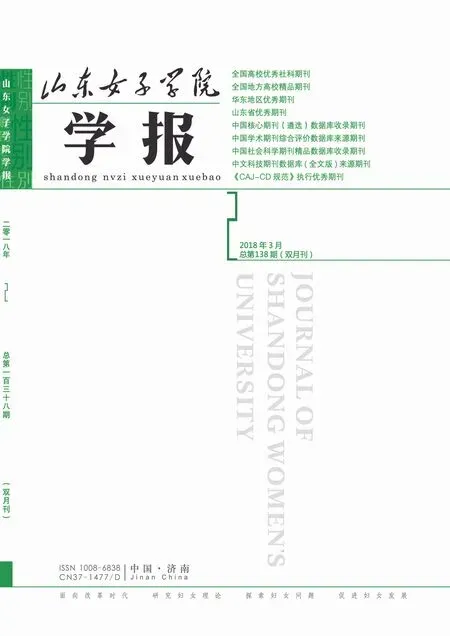明清時(shí)期《女論語(yǔ)》版本考述
王丹妮,李志生
(北京大學(xué),北京 100871)
《女論語(yǔ)》是一部出現(xiàn)于晚唐的女教書(shū),最早見(jiàn)于五代成書(shū)的《舊唐書(shū)》[1],北宋時(shí)編修的《新唐書(shū)》也載有此書(shū)[2]。但在宋元時(shí)期,其書(shū)的刊印和流傳總體不明,諸家書(shū)目中也鮮有蹤跡,唯《玉海》和《通志》兩書(shū)有所著錄,但襲用的仍是兩《唐書(shū)》的內(nèi)容①。今見(jiàn)《女論語(yǔ)》皆為明清刻本,作者通常署名宋若昭或宋尚宮,凡十二章,使用四字韻文,其篇數(shù)、體例、作者與史傳、宋若昭墓志[3]的記載均互有出入。因此,今見(jiàn)《女論語(yǔ)》是否為宋氏姐妹原作、原作如何流傳,就成為了存在爭(zhēng)議且尚待解決的問(wèn)題,也成為了研究者探討的熱點(diǎn)②。
本文暫且擱下《女論語(yǔ)》作者與內(nèi)容的討論與爭(zhēng)議,而關(guān)注《女論語(yǔ)》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明清時(shí)期。我們知道,明末清初以后,《女論語(yǔ)》成為了《女四書(shū)》中的一部,“這部《女四書(shū)》不脛而走地傳遍了妝樓繡閣”[4],其影響之巨、范圍之廣,足應(yīng)使我們對(duì)它更為重視、對(duì)它的刊刻與流傳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就將考察明清時(shí)期《女論語(yǔ)》的版本情況,以期縷析出這一時(shí)期《女論語(yǔ)》流傳的脈絡(luò)。
筆者收集并查閱了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館、北京大學(xué)圖書(shū)館、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日本筑波大學(xué)圖書(shū)館等處收藏的《女論語(yǔ)》,所見(jiàn)版本共計(jì)25種。所見(jiàn)雖仍不夠博洽,但已大略涵蓋了各類(lèi)重要版本。
一、《名媛璣囊》本
今見(jiàn)刊刻年代最早的《女論語(yǔ)》,收錄于明人池上客所編女子詩(shī)歌總集《鐫歷朝列女詩(shī)選名媛璣囊》中。此書(shū)(以下簡(jiǎn)稱(chēng)“國(guó)圖本《名媛璣囊》”)藏于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館,共五卷,刻于萬(wàn)歷二十三年(1595年)。此書(shū)編選上古至明代女子的詩(shī)歌佳作,首卷為《女論語(yǔ)》。
國(guó)圖本《名媛璣囊》半頁(yè)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雙魚(yú)尾。版心處刻“名媛璣囊”四字,中部刻各卷內(nèi)容,首卷《女論語(yǔ)》版心有缺失,刻“論□□卷”,根據(jù)第一至四卷版心之“忠集”“孝集”“廉集”“節(jié)集”,首卷版心或?yàn)椤罢撜Z(yǔ)首卷”四字。近一半的書(shū)頁(yè)版心下方有“宗文堂書(shū)”四字,有些則無(wú)。小序首頁(yè)、全書(shū)末頁(yè)有“北京圖書(shū)館藏”朱長(zhǎng)方印,首卷首頁(yè)有“葉國(guó)”白方印,小序首頁(yè)、卷一首頁(yè)有“長(zhǎng)樂(lè)鄭振鐸西諦藏書(shū)”朱長(zhǎng)方印,全書(shū)末頁(yè)有“長(zhǎng)樂(lè)鄭氏藏書(shū)之印”。末頁(yè)牌記云:“萬(wàn)歷乙未年孟冬月書(shū)林鄭氏云竹繡梓。”首卷《女論語(yǔ)》僅存第一至第十章及第十一章前兩行,至“子侄團(tuán)圓”四字,凡七頁(yè)。第十一章“子侄團(tuán)圓”之后的內(nèi)容及第十二章——即第八頁(yè)至首卷終,皆不存。
是書(shū)原為鄭振鐸藏書(shū)。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他將自己的藏書(shū)悉數(shù)捐獻(xiàn)給國(guó)家,繼由北京圖書(shū)館收藏。隨后,北京圖書(shū)館在鄭振鐸原有藏書(shū)目的基礎(chǔ)上,整理、考察全部藏書(shū),編定《西諦書(shū)目》。其中有關(guān)《鐫歷朝列女詩(shī)選名媛璣囊》的著錄[5]十分簡(jiǎn)略,沒(méi)有超出牌記所提供的信息范圍。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另藏有兩種《名媛璣囊》,其中之一與國(guó)圖所藏相同,題名《鐫歷朝列女詩(shī)選名媛璣囊》,記為明萬(wàn)歷二十三年鄭云竹刊本。另一本題名《名媛璣囊》,記為明代宗文書(shū)堂刻本③。高彥頤曾參閱兩書(shū),稱(chēng)宗文書(shū)堂本《名媛璣囊》刻于萬(wàn)歷二十年(1592年),而萬(wàn)歷二十三年刻本的印刷質(zhì)量要優(yōu)于萬(wàn)歷二十年刻本;又言“因裝訂有誤,《女論語(yǔ)》的第7~9章從前一個(gè)版本(指1592年版)中消失;第10~12章則與第9章的最后一行混在了一起,并且,它們又在后一個(gè)版本(指1595年版)中消失”[6](P321)。宗文書(shū)堂為元代鄭天澤所設(shè)書(shū)坊,遞經(jīng)元明兩代,刻書(shū)甚多。萬(wàn)歷年間,鄭氏后人鄭云竹主持宗文書(shū)堂的刊刻事業(yè),《名媛璣囊》便是眾多付梓書(shū)籍中的一部。
國(guó)圖本《名媛璣囊》中的《女論語(yǔ)》內(nèi)容并不完整,不過(guò),據(jù)高彥頤的描述,內(nèi)閣文庫(kù)藏萬(wàn)歷二十三年刻本中,第10~12章的內(nèi)容與第9章最后一行混在一起,這一部分內(nèi)容中,恰恰包含了國(guó)圖本缺失的部分。也即是說(shuō),《名媛璣囊》本《女論語(yǔ)》的內(nèi)容,能夠使用國(guó)圖本和內(nèi)閣文庫(kù)藏本配補(bǔ)完整。
《女論語(yǔ)》為何被置于列女詩(shī)選之前,編者池上客并未明言,也難有其他線(xiàn)索可尋。但在宋元以來(lái)的社會(huì)觀念中,詩(shī)歌不利于女德的培養(yǎng),因而女性讀詩(shī)、作詩(shī)并不會(huì)得到特別的贊賞和鼓勵(lì),司馬光即言:“至于刺繡華巧,管弦歌詩(shī),皆非女子所宜習(xí)也。”[7]不過(guò),歷朝歷代仍有許多詩(shī)詞佳作出自女子之手,好事之人在欣賞之余,將其匯編成集,付梓刊印。池上客認(rèn)為此種限制女子讀詩(shī)、作詩(shī)的“貞教”未免過(guò)于嚴(yán)苛,他在序中即言道:
憚?wù)吣酥^朱紫并陳,雅鄭兼收,用以忘倦則可,非所以訓(xùn)也。嗟嗟,阿谷援琴,東山攜麈,迄今以為美談,而賦閑情、傳孽嬖,寧以誨淫也,亦宣尼氏不刪鄭衛(wèi)意耳。何必斤斤程度,尺寸不踰,乃稱(chēng)貞教哉[8]!
這說(shuō)明了他選編《名媛璣囊》時(shí),人們對(duì)于女子讀詩(shī)、作詩(shī)仍持否定態(tài)度。既不能恣意贊賞女性才性,又想好好欣賞她們的娟辭麗語(yǔ)、彤管佳作,這種矛盾心理如何處理,就成為其時(shí)社會(huì)道德規(guī)范的制定者所需面臨的問(wèn)題。為了化解此一矛盾,《女論語(yǔ)》才被安置于名媛詩(shī)集之前,以昭告世人,在詩(shī)作之外,女德才是第一要事。面對(duì)道德訓(xùn)誡與詩(shī)歌合流這一令人費(fèi)解的現(xiàn)象,高彥頤根據(jù)《名媛璣囊》至少有萬(wàn)歷二十年和萬(wàn)歷二十三年兩個(gè)刻本而認(rèn)為,“女誡的附錄是想,也確實(shí)達(dá)到了增加銷(xiāo)售的目的”[6](P61)。無(wú)論編者出于何種考量而將其置于首卷,《女論語(yǔ)》都憑借著這樣偶然的因素保留了下來(lái),成為至今能夠見(jiàn)到的最早的版本,而它也成為叢書(shū)本《女論語(yǔ)》之外的一個(gè)特別的版本。
二、重編《說(shuō)郛》本與《綠窗女史》本
一些學(xué)者在論及《女論語(yǔ)》版本時(shí),都談到了《說(shuō)郛》本和《綠窗女史》本。而所謂“《說(shuō)郛》本”,實(shí)指明末重編《說(shuō)郛》本,而非陶宗儀原本,準(zhǔn)確的叫法應(yīng)為“重編《說(shuō)郛》本《女論語(yǔ)》”。我們通過(guò)詳細(xì)比勘,發(fā)現(xiàn)重編《說(shuō)郛》本《女論語(yǔ)》是所有版本中篇幅最長(zhǎng)、字?jǐn)?shù)最多的一種,具有很高的文獻(xiàn)價(jià)值和史料價(jià)值。另外,重編《說(shuō)郛》與《綠窗女史》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也尚未得到學(xué)界關(guān)注。就《女論語(yǔ)》一書(shū)而言,這兩個(gè)版本實(shí)為同版印刷而成,是前后印本的關(guān)系,并非兩個(gè)獨(dú)立的版本系統(tǒng)。
(一)重編《說(shuō)郛》非陶宗儀原本
《說(shuō)郛》為元末明初人陶宗儀所編,其書(shū)“取經(jīng)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shuō)之書(shū)千余家”[9],包含多種后世不傳之書(shū),因而具有較高的文獻(xiàn)價(jià)值。
遺憾的是,陶宗儀原本在編成之后很快散佚,沒(méi)有刻本保留,流傳至今的基本都是散卷殘篇的抄本。明中后期出現(xiàn)一百二十卷本《說(shuō)郛》,另附《續(xù)說(shuō)郛》四十六卷,雖然書(shū)前題有“天臺(tái)陶宗儀纂、姚安陶珽重輯”等字,書(shū)目也與陶本有重合之處,但此后出《說(shuō)郛》的規(guī)模和內(nèi)容已與陶本差異甚大,后世多稱(chēng)其為“重編《說(shuō)郛》”。其書(shū)迭經(jīng)刪削重印,演變?yōu)榍宕ㄐ斜尽墩f(shuō)郛》,后入《四庫(kù)全書(shū)》。無(wú)論陶本《說(shuō)郛》還是重編《說(shuō)郛》,因其篇幅巨大,校訂、刊印及保存版片都成為十分艱辛的事情。即使有印本行世,也很少有人能夠完整收藏一套。重編《說(shuō)郛》雜糅竄亂之處頗繁,多遭詬病。民國(guó)時(shí)期,張宗祥因重編《說(shuō)郛》非陶宗儀原本,便憑借主持京師圖書(shū)館職務(wù)之便,匯集六種明抄本,意欲恢復(fù)陶宗儀本原貌[10]。書(shū)成之后,由涵芬樓排印,凡一百卷,是為涵芬樓本《說(shuō)郛》,被認(rèn)為是與陶宗儀原本最接近的版本。
清人陳師曾作《說(shuō)郛書(shū)目考》,欲探求通行本《說(shuō)郛》中各書(shū)之源流,然僅有抄本存世,且為殘卷④。對(duì)于《說(shuō)郛》較為全面的考察,肇始于法國(guó)漢學(xué)家伯希和。1924年,他在《〈說(shuō)郛〉考》一文中談及了陶宗儀的生平、《說(shuō)郛》的編纂與校訂以及版本源流等問(wèn)題[11],但因他身在法國(guó),資料缺乏,論述難免有誤。其后,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學(xué)者渡邊幸三作《〈說(shuō)郛〉考》[12]、中法漢學(xué)研究所圖書(shū)館館員景培元作《說(shuō)郛版本考》[13]、日本京都大學(xué)教授倉(cāng)田淳之助作《〈說(shuō)郛〉版本諸說(shuō)與己見(jiàn)》[14],三人分別根據(jù)所見(jiàn)諸本《說(shuō)郛》,對(duì)《說(shuō)郛》的版本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討。1979年,臺(tái)灣學(xué)者昌彼得《〈說(shuō)郛〉考》一書(shū),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針對(duì)與《說(shuō)郛》相關(guān)的諸多問(wèn)題,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是為《說(shuō)郛》版本研究的一大力作。昌彼得之后,與《說(shuō)郛》版本相關(guān)的討論數(shù)量不多,而且均在昌氏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細(xì)微的闡發(fā)和修正。近年,美國(guó)印第安納大學(xué)艾騖德(Christopher P. Atwood)在研究《圣武親征錄》時(shí),旁及了《說(shuō)郛》的版本問(wèn)題,作《〈說(shuō)郛〉版本史》,詳細(xì)闡發(fā)了明代《說(shuō)郛》諸抄本之間的譜系關(guān)系[15]。
以上的諸多《說(shuō)郛》版本研究,幾乎均將考察的重點(diǎn)集中在陶宗儀原本《說(shuō)郛》的編纂和流傳方面,而詳細(xì)梳理重編《說(shuō)郛》的成書(shū)及流傳狀況者,唯有渡邊幸三、景培元、倉(cāng)田淳之助和昌彼得四人。渡邊幸三之說(shuō)發(fā)表年代較早,不及昌彼得的闡釋精確,景培元雖參看了不同的版本,但他多沿用渡邊的看法,“其文鮮有發(fā)明”[16](P2)。因此,有關(guān)重編《說(shuō)郛》可以參考的學(xué)說(shuō),只剩倉(cāng)田淳之助和昌彼得兩家。
重編《說(shuō)郛》的編纂及流傳狀況之所以引人關(guān)注,是因通常所言的“《說(shuō)郛》本《女論語(yǔ)》”實(shí)指重編《說(shuō)郛》本,而非陶宗儀原本。明確這一點(diǎn),方可判斷《女論語(yǔ)》收錄于《說(shuō)郛》的時(shí)間。既然張宗祥所輯涵芬樓本《說(shuō)郛》是最接近陶宗儀原本的版本,那么,若將重編《說(shuō)郛》的目錄與涵芬樓本《說(shuō)郛》的目錄兩相對(duì)比,便可知兩個(gè)版本所收書(shū)目的同異。而景培元也已完成了《說(shuō)郛》目錄的對(duì)比工作,詳見(jiàn)其《說(shuō)郛版本考》文后所附《說(shuō)郛子目異同表》。景氏所采之本共五種:(1)涵芬樓本;(2)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藏明刊本,《說(shuō)郛》120卷,《續(xù)說(shuō)郛》46卷;(3)中法漢學(xué)研究所圖書(shū)館藏明刊本,《說(shuō)郛》120卷,《續(xù)說(shuō)郛》44卷;(4)清初印本;(5)《四庫(kù)全書(shū)》本。其中,后四種均屬重編《說(shuō)郛》版本系統(tǒng)。查閱此表,《女論語(yǔ)》一書(shū)未收于涵芬樓本,其余四種皆收錄于“七十”[17]。近年,汲古閣藏明鈔六十卷本《說(shuō)郛》披露于學(xué)界,是當(dāng)年張宗祥編訂涵芬樓本《說(shuō)郛》時(shí)未及參考的明鈔,對(duì)此,張氏《鐵如意館隨筆》云:“《說(shuō)郛》(指涵芬樓本)印成后,知臺(tái)州圖書(shū)館尚有六十卷,亦明鈔本,王子莊先生曾為題記,且目錄亦全,但未寓目,不敢斷定為何時(shí)寫(xiě)本。”[18]此本現(xiàn)藏于浙江臺(tái)州臨海市博物館,徐三見(jiàn)《汲古閣藏明鈔六十卷本〈說(shuō)郛〉考述》一文認(rèn)為,此明鈔本即以陶宗儀原本為底本而成[19]。徐氏在文末附此明抄本的目錄,為學(xué)之人得以略窺其貌。目錄之中,沒(méi)有《女論語(yǔ)》的條目。由是可以得出結(jié)論,《女論語(yǔ)》入重編《說(shuō)郛》為明中后期之事,陶宗儀本人沒(méi)有將《女論語(yǔ)》收入《說(shuō)郛》之中。
那么,隨之而來(lái)的問(wèn)題是,《女論語(yǔ)》因何收錄于重編《說(shuō)郛》?何人將《女論語(yǔ)》收錄其中?所據(jù)底本為何?倉(cāng)田淳之助在《〈說(shuō)郛〉版本諸說(shuō)與己見(jiàn)》一文中,著重討論了重編《說(shuō)郛》(倉(cāng)田文中稱(chēng)為《重較說(shuō)郛》)的問(wèn)題。他首先注意到《重編百川學(xué)海》《續(xù)百川學(xué)海》《廣百川學(xué)海》《廣漢魏叢書(shū)》《唐宋叢書(shū)》《五朝小說(shuō)》等叢書(shū)的行格字體與重編《說(shuō)郛》近乎一致,均為九行二十字,左右雙邊,單魚(yú)尾,且這幾部叢書(shū)中的大部分書(shū)目與重編《說(shuō)郛》目錄相同。同時(shí),他比對(duì)了日本所藏以上諸叢書(shū)與重編《說(shuō)郛》中相同的版面,發(fā)現(xiàn)兩者的區(qū)別在于,重編《說(shuō)郛》挖削了版片上原有的校閱者姓名,遂認(rèn)為以上諸叢書(shū)的書(shū)版刻成后,大部分旁用于重編《說(shuō)郛》。因而得出“重編《說(shuō)郛》是從萬(wàn)歷末年至崇禎年間,以各種形式出現(xiàn)的刊版合集”[14]的結(jié)論。但是,《重編百川學(xué)海》《續(xù)百川學(xué)海》《廣百川學(xué)海》《廣漢魏叢書(shū)》《唐宋叢書(shū)》《五朝小說(shuō)》等諸多叢書(shū),并非由同一家書(shū)肆刊印,它們之間應(yīng)該是互相獨(dú)立的關(guān)系。因何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的幾套叢書(shū),會(huì)使用完全相同的行格字體?對(duì)此,倉(cāng)田淳之助卻沒(méi)有作出說(shuō)明。
與倉(cāng)田淳之助全然相反,昌彼得認(rèn)為先有重編《說(shuō)郛》之版,諸叢書(shū)后取用之。對(duì)于重編《說(shuō)郛》的成書(shū)過(guò)程,他詳細(xì)比勘了臺(tái)灣“中央”圖書(shū)館所藏《廣漢魏叢書(shū)》《重編百川學(xué)海》《續(xù)百川學(xué)海》《廣百川學(xué)海》《熙朝樂(lè)事》和《游藝備覽》六部叢書(shū)與明印本重編《說(shuō)郛》的異同。他認(rèn)為,重編《說(shuō)郛》纂于萬(wàn)歷年間,編成后刻板。何人主持編纂之務(wù),今已無(wú)考。但是,當(dāng)時(shí)寓居武林(今杭州)的諸多讀書(shū)人,分別承擔(dān)了校訂重編《說(shuō)郛》的工作,刻板之時(shí),于每一書(shū)名下標(biāo)示校閱者姓名。但因無(wú)初印本傳世,彼時(shí)是否印刷,尚存疑問(wèn)。天啟元年(1621年),杭州城發(fā)生火災(zāi),重編《說(shuō)郛》板片旋即分散,遂為書(shū)商所購(gòu)。書(shū)商以這部分板片為基礎(chǔ),修補(bǔ)增刻,編印數(shù)種叢書(shū),如《廣漢魏叢書(shū)》《重編百川學(xué)海》《續(xù)百川學(xué)海》《廣百川學(xué)海》《熙朝樂(lè)事》《游藝備覽》等。崇禎年間,重編《說(shuō)郛》的書(shū)版被人搜集起來(lái),由分而合,挖削增補(bǔ),特別是挖去了校閱者姓名,其后重新印售。明亡,重編《說(shuō)郛》板片仍存于杭州。順治三年(1646年),浙江提學(xué)道李際期整理舊版,重定印行,是為清代通行本《說(shuō)郛》的祖本。此后板片遞有損毀,并且因其中部分書(shū)目關(guān)涉違礙禁忌之語(yǔ),重編《說(shuō)郛》屢經(jīng)刪改,各個(gè)印本互有不同,康熙年間,其板最終由合而分[16](P29-31)。
重編《說(shuō)郛》較陶宗儀原本《說(shuō)郛》而言,所收書(shū)目的數(shù)量大大增加,其中有四百余種與陶宗儀原本相同,其余則為重編者所增。對(duì)此,昌彼得認(rèn)為,這是抄本之誤所致:
楊維楨《說(shuō)郛序》云:“陶九成取經(jīng)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shuō)一千余家”,此處“一千余家”,重編《說(shuō)郛》本楊序刻作二千余家,殆其所據(jù)抄本之訛。重編《說(shuō)郛》者既未能獲見(jiàn)郁本之全書(shū)與全目,因此序有二千余家之說(shuō),于是廣搜博采,流傳之叢刻雜纂,無(wú)不囊括,欲符其數(shù)[16](P34)。
由是,《女論語(yǔ)》本非陶宗儀原本所錄之書(shū),而是出版重編《說(shuō)郛》的人在“廣搜博采”的“湊數(shù)”過(guò)程中收入其中的。而其所據(jù)的底本,亦如重編者不知何人,無(wú)從考究,或?yàn)楸藭r(shí)坊間流行之本。
(二)重編《說(shuō)郛》本與《綠窗女史》本為同版印刷
在重編《說(shuō)郛》本《女論語(yǔ)》之外,《綠窗女史》本《女論語(yǔ)》亦頗受關(guān)注。《綠窗女史》,明末秦淮寓客輯,凡十四卷,是一部以婦女為主題的叢書(shū)。內(nèi)容以前代傳奇和筆記小說(shuō)為主,另涉女子儀范、妝容、勞作、撰著等。《女論語(yǔ)》位列全書(shū)首卷,類(lèi)屬《閨閣部·懿范》。
國(guó)家圖書(shū)館藏有《綠窗女史》數(shù)種,多為殘卷,僅有兩明刻本為足本,兩書(shū)內(nèi)容完全一致,應(yīng)為前后印本。印成時(shí)間較早的明刻本(簡(jiǎn)稱(chēng)“國(guó)圖本”),凡十四卷,板框大小不一,行格不盡相同,應(yīng)使用多種版片合印。但是行格多為半頁(yè)九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yú)尾。封面有“選工繡像”“心遠(yuǎn)堂藏板”字樣。前有秦淮寓客所撰的《綠窗女史引》,小引首頁(yè)有“萬(wàn)卷樓”朱橢圓印、“青宮之師”白方印、“國(guó)立北平圖書(shū)館珍藏”朱長(zhǎng)方印,另有一朱方印模糊不清,較難辨識(shí)。《女論語(yǔ)》首頁(yè)有“王鐵仙曾觀”白方印。
比對(duì)《綠窗女史》和《說(shuō)郛三種》影印本兩書(shū)的《女論語(yǔ)》可知,國(guó)圖本《綠窗女史》的行格字體與重編《說(shuō)郛》完全一致。除清晰程度有所差別,版裂之處亦完全相同。初步判斷,兩書(shū)中的《女論語(yǔ)》應(yīng)為同版印刷。
如此,《綠窗女史》與重編《說(shuō)郛》的關(guān)系,就需作進(jìn)一步考量。重編《說(shuō)郛》與同時(shí)期的許多叢書(shū),都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昌彼得的推想是,萬(wàn)歷末年重編《說(shuō)郛》版片刻成后,因天啟元年杭州的火災(zāi)而散入書(shū)商之手,書(shū)商繼而用以別印他書(shū)。不久之后,重編《說(shuō)郛》版片又被重新收集起來(lái),遂有崇禎年間重印的重編《說(shuō)郛》。而《廣漢魏叢書(shū)》《重編百川學(xué)海》《續(xù)百川學(xué)海》《廣百川學(xué)海》《熙朝樂(lè)事》《游藝備覽》這六部叢書(shū)的印刷時(shí)間,要早于崇禎年間搜集重印的重編《說(shuō)郛》。昌彼得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是因?yàn)樗l(fā)現(xiàn)六叢書(shū)中,“所收四百余種書(shū)中,約四分之三逾三百種,《說(shuō)郛》即據(jù)此舊版重印”[16](P26)。而比較六叢書(shū)與重印本重編《說(shuō)郛》重出的書(shū)目,雖然使用同版,但也有不同之處。重編《說(shuō)郛》原為武林文人校訂,因此每書(shū)作者之下,均有校閱人的姓名。校閱人的姓名在六叢書(shū)中有存,在崇禎年間重印本重編《說(shuō)郛》中,幾乎不存。除了少數(shù)地方忘記刪削,大部分校閱者姓名均被挖除。
依照這樣的思路,也可將《綠窗女史》與重編《說(shuō)郛》作一番比較。影印本《說(shuō)郛三種》為明刻本,且較易獲得,我們暫且使用國(guó)家圖書(shū)館所藏明刊本《綠窗女史》與《說(shuō)郛三種》中的重編《說(shuō)郛》進(jìn)行對(duì)比。
這里關(guān)于《綠窗女史》還需作出一點(diǎn)說(shuō)明。《綠窗女史》的版本流傳情況,今亦不甚明晰。除國(guó)圖本之外,臺(tái)灣的明清善本小說(shuō)叢刊,也收錄了影印的明刻本《綠窗女史》⑤(簡(jiǎn)稱(chēng)“叢刊本”)。相較叢刊本,國(guó)圖本少收書(shū)18種,其中15種無(wú)目無(wú)書(shū),另外3種有目無(wú)書(shū)。而這18種書(shū)的目錄編次,無(wú)一例外地位于其所屬小類(lèi)的最后。仔細(xì)翻看國(guó)圖本各小類(lèi)目錄部分,小類(lèi)名稱(chēng)大字單行,書(shū)目名稱(chēng)小字雙行,書(shū)目名稱(chēng)與小類(lèi)名稱(chēng)中無(wú)空行。若小類(lèi)中所收書(shū)目為單數(shù),則最后一書(shū)目與下一小類(lèi)名稱(chēng)中空出半行。《青樓部上·志節(jié)·徐蘭傳》《青樓部上·志節(jié)·義妓傳》和《青樓部下·品藻·秦淮士女表》三書(shū),叢刊本有目錄處,國(guó)圖本皆無(wú),但是后者留有挖削未凈的痕跡。或可以說(shuō)明,國(guó)圖本的印刷時(shí)間,晚于叢刊本。當(dāng)時(shí)主持重印《綠窗女史》的人,因?yàn)槟撤N原因,想要?jiǎng)h掉一些書(shū)目,又不想被人發(fā)現(xiàn),因此直接刪去每一小類(lèi)最后的一種或兩種,并挖除了相應(yīng)的目錄。刪削卷末的部分,遠(yuǎn)比去除卷首、卷中的部分容易得多,這樣做,便很難在目錄上發(fā)現(xiàn)異常。有目無(wú)書(shū)的3種,應(yīng)該是印刷之人一時(shí)疏忽大意,忘記挖削所致。考叢刊本《綠窗女史》,凡收書(shū)208種,見(jiàn)于重編《說(shuō)郛》者,共30種,見(jiàn)于《續(xù)說(shuō)郛》者,共12種。雖然國(guó)圖本《綠窗女史》較叢刊本收書(shū)較少,但是除了《焚椒錄》和《秦淮士女表》2種之外,其他見(jiàn)于重編《說(shuō)郛》者,均存其中。叢刊本與國(guó)圖本既為同版印刷,在叢刊本效果不甚理想、國(guó)圖本得見(jiàn)原書(shū)的情況下,暫用國(guó)圖本與《說(shuō)郛三種》進(jìn)行比對(duì)。
考兩書(shū)重見(jiàn)書(shū)目,可知《綠窗女史》的印刷時(shí)間晚于明末重印本重編《說(shuō)郛》,理由有五:(1)據(jù)昌彼得推論,重編《說(shuō)郛》重印之時(shí),挖削了原書(shū)作者之下的校閱者姓名。《綠窗女史》中,作者之下,均無(wú)校閱者姓名。(2)兩書(shū)重出書(shū)目,集中分布在重編《說(shuō)郛》七十、一百十一至一百十四以及《續(xù)說(shuō)郛》卷四十三、卷四十四。重編《說(shuō)郛》雖無(wú)明確的分類(lèi)標(biāo)準(zhǔn),但內(nèi)容相近的書(shū)目,多集中排列。《綠窗女史》編纂者根據(jù)需求,分別取用了重編《說(shuō)郛》與《續(xù)說(shuō)郛》中的部分書(shū)目,后借版印刷。(3)《綠窗女史》版片模糊漫漶之處,較重編《說(shuō)郛》更加嚴(yán)重,有些書(shū)頁(yè)幾不可閱,也出現(xiàn)了筆畫(huà)掉落的現(xiàn)象。如《女誡》葉五b前六行上半部分、葉六a第五、六行上半部分十分不清晰。葉三b“守節(jié)”的“節(jié)”字、“婦德”的“婦”字,分別掉落一半;《同昌公主傳》葉四b最后一行第一字“珍”連同部分板框均磨損不見(jiàn),重編《說(shuō)郛》中尚存。(4)《綠窗女史》與重編《說(shuō)郛》版面裂縫處相同,前者裂縫更大,更有甚者分裂為兩部分。如《劉無(wú)雙傳》最后一頁(yè),《綠窗女史》版片的裂縫更大,且橫向貫穿,裂縫上下的界格并沒(méi)有對(duì)齊,或已徹底斷開(kāi)。(5)《綠窗女史》補(bǔ)版之處,與重編《說(shuō)郛》原版有所不同。《綠窗女史》中,《趙飛燕外傳》全書(shū)的版面狀況都十分糟糕,重編《說(shuō)郛》情況稍好,單頁(yè)模糊不清。《綠窗女史》刊刻之時(shí),版面狀況已劣于重編《說(shuō)郛》重印之時(shí),因此在非常糟糕的地方,模仿重編《說(shuō)郛》進(jìn)行了重刻。葉三b“愛(ài)死非姊教愿以身易”“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方成白發(fā)教授宮中號(hào)”二十七字為補(bǔ)版部分,字體較重編《說(shuō)郛》更為纖細(xì)。
明末書(shū)坊,甲乙互鬻屢有發(fā)生,同一套版片,可能被不同的書(shū)肆用以印刷,出現(xiàn)在不同的書(shū)籍之中。重編《說(shuō)郛》版片被人重新搜集起來(lái)之后,保存于書(shū)肆,《綠窗女史》編纂之時(shí),借用了重編《說(shuō)郛》的部分版片,稍稍進(jìn)行了補(bǔ)版、重刻,再行印刷,于是才出現(xiàn)了今天可以看到的《綠窗女史》與重編《說(shuō)郛》中的《女論語(yǔ)》為同版印刷的情況。因此,重編《說(shuō)郛》和《綠窗女史》兩書(shū)中的《女論語(yǔ)》應(yīng)為前后印本的關(guān)系。
三、《女四書(shū)集注》本
《女論語(yǔ)》為世人所熟知,多藉由明末清初人王相的《女四書(shū)集注》(簡(jiǎn)稱(chēng)“《女四書(shū)》”),但是《女四書(shū)》的成書(shū)時(shí)間,至今不能確定。王相選擇哪一版本的《女論語(yǔ)》作為底本,今亦無(wú)考。收入《女四書(shū)》的《女論語(yǔ)》可泛稱(chēng)“《女四書(shū)集注》本”或“《女四書(shū)》本”。《女四書(shū)》成書(shū)之后,迭有刊印,逐漸形成了一個(gè)較為獨(dú)立的版本系統(tǒng)。明天啟四年(1624年)多文堂刊本、清初奎壁齋本、書(shū)業(yè)堂本及清末諸多印本,均是《女四書(shū)》本版本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不過(guò),不同版本的《女四書(shū)》,多少存在相異之處,《女論語(yǔ)》也因《女四書(shū)》的版本差異而發(fā)生了些微變化。
(一)多文堂本
每論及王相《女四書(shū)集注》,多文堂本《閨閣女四書(shū)集注》必是最先受到關(guān)注的。原因在于,它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女四書(shū)集注》刊本。但是,得見(jiàn)此本者似乎僅有胡文楷一人,旁人均是通過(guò)他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中的敘述,才了解了此本的情況。胡氏于自序中言道,《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著錄的書(shū)目,其經(jīng)眼者,或向全國(guó)各圖書(shū)館借鈔,或遍觀諸家私藏。而“見(jiàn)于正史藝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縣志者,藏書(shū)目錄提拔者,詩(shī)文詞總集及詩(shī)話(huà)筆記者”[20](P5-6),也一一采錄。其凡例又云:
書(shū)囊無(wú)底,聞見(jiàn)有限,著錄各書(shū),或僅著初刻,而覆刻重刻之本,未見(jiàn)著錄;亦有僅據(jù)重刻,而原刻不詳者。而坊間石印之本,前以其不甚珍貴,未經(jīng)采集,故未能一一著錄[20](P10)。
胡氏所閱之書(shū)雖多,但仍有許多書(shū)籍未得經(jīng)眼,故其所見(jiàn)者,于條目后標(biāo)示“見(jiàn)”字,未得見(jiàn)者則標(biāo)示“未見(jiàn)”。關(guān)于《女論語(yǔ)》,胡文楷著錄云:
《女論語(yǔ)》一卷,唐宋若莘、宋若昭撰,《新唐書(shū)·后妃傳》著錄。(見(jiàn))
明末多文堂刊本,列入《閨閣女四書(shū)》,瑯琊王相箋注。書(shū)凡十篇:立身、學(xué)作、學(xué)禮、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訓(xùn)男女、營(yíng)家、待客。前有自序。又《說(shuō)郛》本[20](P22)。
又《閨閣女四書(shū)集注》條云:
《閨閣女四書(shū)集注》,明天啟四年甲子多文堂刊本。
(明)王相箋注。相字晉升,瑯琊人。是書(shū)前有萬(wàn)歷八年神宗皇帝御制序。卷首題莆陽(yáng)鄭漢濯之校梓。九經(jīng)堂刊曹大家《女誡》、仁孝文皇后《內(nèi)訓(xùn)》二種。后多文堂刊《女論語(yǔ)》及《女范捷錄》,為《女四書(shū)》[20](P843)。
胡文楷于《女論語(yǔ)》條目后書(shū)“見(jiàn)”字,表明他過(guò)眼了天啟四年(1624年)多文堂刊印的這部《女論語(yǔ)》,如此,至少在二十世紀(jì)中葉,此書(shū)仍留于中國(guó)大陸。遺憾的是,胡氏沒(méi)有明言《閨閣女四書(shū)集注》的來(lái)源和去向,并且自他之后,也再無(wú)人見(jiàn)過(guò)此書(shū),其書(shū)至今下落不明。因此,關(guān)于此版本《女論語(yǔ)》的情況,僅能依靠胡氏只言片語(yǔ)的記載得以了解。
胡文楷所見(jiàn)的《閨閣女四書(shū)集注》由兩個(gè)版本配補(bǔ)而成,而非九經(jīng)堂或多文堂最初刊刻的足本。其中,《女論語(yǔ)》由多文堂所刊,而此本最大的特點(diǎn)即其為十章,而非通常所見(jiàn)的十二章。除此之外,所有版本的《女論語(yǔ)》皆為十二章。
(二)奎壁齋本
奎壁齋本《女四書(shū)集注》藏于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館,清初刻本。板框大小約18cm×12.8cm,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白口,無(wú)魚(yú)尾,方體字。版面模糊漫漶處頗多。此本封面除書(shū)名外,另有“奎壁齋訂本”“金陵鄭元美行梓”等字。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誡序》,《內(nèi)訓(xùn)》末頁(yè)、《女范捷錄》末頁(yè)牌記曰“莆陽(yáng)鄭氏訂本 金陵奎壁齋梓”。《女誡》首頁(yè)、《宋若昭女論語(yǔ)》首頁(yè)、全書(shū)末頁(yè)分別有“北京圖書(shū)館藏”朱長(zhǎng)方印。文字不避康熙、乾隆之諱。《宋若昭女論語(yǔ)》凡十二章,卷首題“瑯琊王相晉升箋注 莆陽(yáng)鄭漢濯之校梓”,前有宋若昭本傳和《女論語(yǔ)序傳》。
關(guān)于“奎壁齋”,《中國(guó)古籍版刻辭典》“奎壁堂”條云:“一作‘奎壁齋’。明萬(wàn)歷間金陵人鄭思鳴、鄭大經(jīng)的書(shū)坊名,在狀元坊。”[21](P425)則《女四書(shū)集注》牌記中所謂的“金陵奎壁齋”,即指此書(shū)坊。而關(guān)于鄭元美,《中國(guó)古籍版刻辭典》認(rèn)為,鄭思鳴字元美,故鄭元美就是鄭思鳴[21](P425),但對(duì)于這種看法,尤海燕進(jìn)行了辯駁。她認(rèn)為,鄭元美的刊刻活動(dòng)時(shí)間主要在明末清初,其立論的證據(jù)如下:(1)奎壁齋刻《奎壁齋增訂評(píng)注廣日記故事》正文首頁(yè)標(biāo)注“瑯琊王相晉升增注 莆陽(yáng)鄭鉁元美校梓”,可視為鄭元美非鄭思鳴的直接證據(jù)。(2)《歌林拾翠》刊于“己亥年”,書(shū)中收錄的《紅梅記》的流傳時(shí)間在萬(wàn)歷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晚于此前的己亥年——萬(wàn)歷二十七年(1599年),遂排除了萬(wàn)歷二十七年刊刻的可能。(3)除《歌林拾翠》外,鄭元美奎壁齋所刻諸書(shū)如《廣日記故事》《女四書(shū)集注》,完全不避康熙、乾隆之諱,因而《歌林拾翠》應(yīng)刻于康熙之前的己亥年,即順治十六年(1659年)[22](P59-63)。
此外,由于《奎壁齋增訂評(píng)注廣日記故事》首頁(yè)標(biāo)注“瑯琊王相晉升增注 莆陽(yáng)鄭鉁元美校梓”,尤海燕認(rèn)為此書(shū)的刊刻由鄭元美主持,實(shí)際增訂評(píng)注工作則由王相完成,因此鄭元美和王相是同時(shí)代的人[22](P62-63)。這一推論有一定道理,那么鄭元美和王相可能生年有所重合,進(jìn)一步而言,王相或許還見(jiàn)到過(guò)奎壁齋本《女四書(shū)集注》。
尤海燕關(guān)注到的奎壁齋本《女四書(shū)集注》,即為我們所見(jiàn)之本。《女論語(yǔ)》書(shū)前編錄宋若昭本傳,正文十二章,卷首題“莆陽(yáng)鄭漢濯之校梓”之外,另題“瑯琊王相晉升箋注”。在多文堂本不知去向的情況下,奎壁齋本是目前所見(jiàn)最早的《女四書(shū)》本《女論語(yǔ)》,又因其刊刻之時(shí)王相可能尚在人世,所以文本內(nèi)容應(yīng)比較準(zhǔn)確、可信。
另外,還有以奎壁齋本為底本的書(shū)業(yè)堂本《女四書(shū)》,藏于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書(shū)業(yè)堂,明萬(wàn)歷年間蘇州金閶地區(qū)的書(shū)坊[21](P85),入清后,刻書(shū)、售書(shū)活動(dòng)仍繼續(xù)。據(jù)書(shū)業(yè)堂本《女四書(shū)》封面“奎壁齋訂本”“乾隆六十年秋鐫”“書(shū)業(yè)堂梓行”等字可知,書(shū)業(yè)堂本《女四書(shū)》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以奎壁齋本為底本而成。此本板框大小約17cm×12cm,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白口,無(wú)魚(yú)尾。首頁(yè)有“淺草文庫(kù)”“書(shū)籍館印”和“日本政府圖書(shū)”等印。書(shū)業(yè)堂本雖本自奎壁齋本,但《女誡》《女論語(yǔ)》《內(nèi)訓(xùn)》和《女范捷錄》四書(shū)的排列順序與奎壁齋本稍異,奎壁齋本的順序?yàn)椤杜]》《內(nèi)訓(xùn)》《女論語(yǔ)》和《女范捷錄》,而書(shū)業(yè)堂本則為《女誡》《女論語(yǔ)》《內(nèi)訓(xùn)》和《女范捷錄》。書(shū)業(yè)堂本的順序以四部書(shū)產(chǎn)生的年代順序排列,而奎壁齋則將本朝(明朝)徐皇后的《內(nèi)訓(xùn)》前提,這一編排頗具時(shí)代特點(diǎn)。另外,在現(xiàn)存的《女四書(shū)集注》中,清末印本較多,明代及清代中前期印本稀少,作為清中期刻本的書(shū)業(yè)堂本,可視為《女四書(shū)》在清代迭有刊印的確證。
(三)《校訂女子四書(shū)箋注》與《狀元閣女四書(shū)》
《狀元閣女四書(shū)》系指清末李光明莊所刻的《女四書(shū)》及其他書(shū)坊據(jù)此覆刻之本。李光明莊是其時(shí)南京城內(nèi)頗具盛名的書(shū)坊,印售各種童蒙讀物,十分暢銷(xiāo),流傳頗廣。20世紀(jì)90年代末,黃永年先生至蘇州,于舊書(shū)鋪內(nèi)購(gòu)得一部《香山詩(shī)選》,書(shū)后附有一頁(yè)售書(shū)廣告:“江南聚寶門(mén)三山大街大功坊郭家巷內(nèi)電線(xiàn)局西首秦狀元巷中李光明家自梓童蒙各種讀本,揀選重料紙張裝訂,又分鋪狀元境,狀元境口狀元閣發(fā)售,實(shí)價(jià)列下。”[23]而“自梓童蒙各種讀本”中,便包括了《狀元閣女四書(shū)》。
《狀元閣女四書(shū)》印成發(fā)售之后,頗受時(shí)人歡迎,其他書(shū)坊相繼仿刻,并沿用《狀元閣女四書(shū)》之名。不過(guò),《狀元閣女四書(shū)》的校訂刊印,并非李光明莊的創(chuàng)舉,而是肇始于蘇州崇德書(shū)院。李光明莊以崇德書(shū)院的《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為底本,或另參照其他坊間流傳的《女四書(shū)》,進(jìn)行了簡(jiǎn)單校勘,雖然修正了崇德書(shū)院本的個(gè)別字詞錯(cuò)誤,但有多處原本正確的地方,《狀元閣女四書(shū)》卻現(xiàn)為錯(cuò)字。事實(shí)上,當(dāng)時(shí)流傳甚廣、今天仍為許多研究者所重的《狀元閣女四書(shū)》,并不如崇德書(shū)院本精良,可以說(shuō),崇德書(shū)院《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才是清末流行的諸多《狀元閣女四書(shū)》的祖本。由于李光明莊在刊印童蒙讀物方面知名度較高,所以坊間覆刻之作較多,人們也多愿選讀《狀元閣女四書(shū)》,而漸漸遺忘了它的祖本——崇德書(shū)院《校訂女四書(shū)集注》的存在。
1.蘇州崇德書(shū)院本《校訂女四書(shū)集注》。此本刊刻于光緒三年(1876年),封面題名《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首頁(yè)題“瑯琊王相晉升箋注 莆陽(yáng)鄭漢濯之校梓”等字。內(nèi)封牌記曰:“光緒丁丑刊于蘇州崇德書(shū)院”。板框大小約17.6cm×13cm,半頁(yè)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或四周單邊,白口,無(wú)魚(yú)尾。前有潘遵祁《序》,《序》文開(kāi)頭紙頁(yè)破損,缺“詩(shī)三”兩字。其中的《女論語(yǔ)》書(shū)為《宋若昭女論語(yǔ)》,前有宋若昭《唐書(shū)》列傳及《女論語(yǔ)序傳》,共十二章。
潘遵祁(1808—1892),字順之,號(hào)西圃,吳縣人(今蘇州吳縣)。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jìn)士,任庶吉士,授編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翰林,后無(wú)意仕途,回鄉(xiāng)隱居,著有《西圃集》。潘遵祁《序》作于光緒二年(1876年),其云:
詩(shī)三百篇,首求淑女。易六十四卦,爰著家人,此關(guān)雎所以為王化之始,而正家所以可定天下也。閨門(mén)之教,今之人忽焉不講,而古圣人重之如是。善乎陳文恭公之言曰:“有賢女然后有賢婦,有賢婦然后有賢母,有賢母然后有賢子孫。”于是乎有《教女遺規(guī)》之刻。近日坊間所傳《女誡》《女論語(yǔ)》等,流風(fēng)善政,猶有存者,無(wú)如翻刻麤陋,增損失真,僅供村塾師口授,而詩(shī)禮之門(mén)、庠序之士,反為未見(jiàn)之書(shū)。世風(fēng)日下,中饋不嚴(yán),休其蠶織,嘻嘻終吝。每觀一家之興替,系乎內(nèi)助之賢否者甚多。讀文恭之書(shū),慨焉有思古之懷。適坊友重謀剞劂,因?yàn)樾U谥⒁詴?shū)[24]。
陳文恭公是為編纂《教女遺規(guī)》的陳宏謀,潘遵祁有感于陳宏謀對(duì)于閨門(mén)之教的重視,又因坊間流傳的《女誡》《女論語(yǔ)》等書(shū)翻刻丑陋,粗鄙失真,故在崇德書(shū)院的邀請(qǐng)下,重新校訂了王相所注的《女四書(shū)》,翌年,這部潘校《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便付梓刊印。
以奎壁齋本《女四書(shū)集注》中的《女論語(yǔ)》與崇德書(shū)院本(簡(jiǎn)稱(chēng)崇本)校勘,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相異之處。如《女論語(yǔ)序傳》部分,“深惜后人”,崇本作“深夫后人”;《學(xué)禮章》中“迎來(lái)遞去”,崇本作“迎來(lái)送去”;《訓(xùn)男女章》中“家鄉(xiāng)不顧”,崇本作“家庭不顧”;“酗酒歌唱”,崇本作“酌酒歌唱”;《營(yíng)家章》中“擾亂四鄰”,崇本作“擾亂西鄰”;《守節(jié)章》中“女德昭明”,崇本作“女德聰明”。這些與奎壁齋本具有明顯差異的文本,均被諸本《狀元閣女四書(shū)》繼承下來(lái),也可以作為判斷版本源流的依據(jù)之一。
2.李光明莊本《狀元閣女四書(shū)》。此本刻于光緒六年(1880年),封面朱墨題名《狀元閣女四書(shū)》,內(nèi)封刻朱色廣告詞“江南城聚寶門(mén)三山大街大功坊郭家巷內(nèi)秦狀元巷中李光明莊重復(fù)校對(duì)自梓童蒙各種讀本揀選重料紙張裝訂發(fā)兌”一段。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誡序》,序文刻于紅靛套印龍鳳圖框正中,半頁(yè)五行,依序文內(nèi)容提一格、兩格、三格不等,凡四頁(yè)。葉四b牌記曰“光緒六年八月”,另有“天子萬(wàn)年”四字。《曹大家女誡》首頁(yè)、全書(shū)末頁(yè)有“北京圖書(shū)館藏”朱長(zhǎng)方印。板框大小約18.4cm×13cm,半頁(yè)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魚(yú)尾。版心上方邊框下凹一字,版心下方刻“李光明莊”四字。正文及注文部分有圈點(diǎn)句讀。書(shū)后附潘遵祁跋,實(shí)為崇德書(shū)院本《女四書(shū)》中潘遵祁序。
李光明莊《狀元閣女四書(shū)》中的《女論語(yǔ)》部分,整體承襲崇德書(shū)院本,于個(gè)別之處予以校改。對(duì)比兩書(shū),第六章《事舅姑》末尾,狀元閣本添加“恣音自”的音釋?zhuān)绫緹o(wú)此三字,年代更早的奎壁齋本亦無(wú),說(shuō)明此為李光明莊所添,非王相原注。其他與崇本不同之處,如《唐書(shū)》列傳,“德宗”,狀元閣本作“德宋”;《女論語(yǔ)序傳》,“深夫后人”,狀元閣本作“懼夫后人”。《學(xué)禮章》“當(dāng)起不起”,狀元閣本作“待起不起”;“湯干醋盡”,狀元閣本作“湯干酬盡”。
自潘遵祁校訂、蘇州崇德書(shū)院印行《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后,王相箋注的《女四書(shū)》在清末社會(huì)中迅速流傳開(kāi)來(lái),對(duì)這一流傳起關(guān)鍵作用的,就是李光明莊所刻《狀元閣女四書(shū)》。其后,文成堂、江左書(shū)林、共賞書(shū)局、善成堂、江陰寶文堂等,直至民國(guó)時(shí)期的錦章書(shū)局、會(huì)文堂書(shū)局,相繼據(jù)李光明莊本覆刻或重刻此書(shū),諸書(shū)的祖本實(shí)際都應(yīng)是崇德書(shū)院的《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清末諸多書(shū)坊更直接沿用了李光明莊“潘遵祁跋”的說(shuō)法。
綜此,我們看到,目前傳世的數(shù)十種《女論語(yǔ)》,均為明清刻本。這些刻本實(shí)分為了《名媛璣囊》本、重編《說(shuō)郛》本和《女四書(shū)集注》本等3個(gè)系統(tǒng)。《鐫歷朝列女詩(shī)選名媛璣囊》首卷所收明萬(wàn)歷年間刻《女論語(yǔ)》,是為目前所見(jiàn)年代最早者。重編《說(shuō)郛》本為明末坊間之作,其非陶宗儀《說(shuō)郛》的原本;《綠窗女史》本與重編《說(shuō)郛》本實(shí)為同一書(shū)版的前后印本。《女四書(shū)集注》本中,清初奎壁齋本的年代最早。清末諸多《女四書(shū)》本的祖本,是崇德書(shū)院的《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而《狀元閣女四書(shū)》則是流傳最廣、翻刻重刻次數(shù)最多的版本。
注釋:
① 見(jiàn)王應(yīng)麟《玉海》卷五五《藝文·唐女論語(y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49頁(yè);鄭樵《通志》卷五六《藝文略·列女》,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年,志779頁(yè)下。唯《通志》雖沿用前代之說(shuō),但卻誤將“篇”作“卷”。
② 如高世瑜認(rèn)為,宋若莘的《女論語(yǔ)》原作已散佚,傳世的《女論語(yǔ)》前十章為宋若昭的申釋之文,后兩章“和柔”“守節(jié)”的內(nèi)容或?yàn)楹笕怂?氏著《宋氏姐妹與〈女論語(yǔ)〉論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趨勢(shì)》,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huì)》,上海: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2003年,第148頁(yè));李志生認(rèn)為,《女論語(yǔ)》十二章均為宋若昭作,前十章為申釋之文,后兩章為總結(jié)之文,隨著宋若昭注釋的流傳,位于結(jié)尾處的總結(jié)之文漸被冠以十一章和十二章(氏著《中國(guó)古代婦女史研究入門(mén)》,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第108頁(yè));日本學(xué)者山崎純一推測(cè),傳世的《女論語(yǔ)》或是薛蒙妻韋氏的《續(xù)曹大家女誡》(氏著《教育からみた中國(guó)女性史資料の研究》,東京:明治書(shū)院,1986年,第109頁(yè));黃嫣梨認(rèn)為,《女論語(yǔ)》作者確為宋若莘、宋若昭,但今傳本或并非原本之制(氏著《〈女孝經(jīng)〉與〈女論語(yǔ)〉》,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huì)》,第189頁(yè))。
③ 據(jù)內(nèi)閣文庫(kù)館藏檢索系統(tǒng)獲取兩書(shū)信息,見(jiàn)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④ 陳師曾《說(shuō)郛書(shū)目考》,現(xiàn)存1~3卷,抄本,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館藏。
⑤ 參見(jiàn)秦淮寓客的《綠窗女史》,臺(tái)灣“國(guó)立”政治大學(xué)古典小說(shuō)研究中心《明清善本小說(shuō)叢刊·初編》,第2輯,天一出版社影印明刻本,1985年。
[ 1 ] 劉昫,等.舊唐書(shū)[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5. 2198.
[ 2 ] 歐陽(yáng)修,宋祁. 新唐書(shū)[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5. 3508.
[ 3 ] 趙力光,王慶衛(wèi).新見(jiàn)唐代內(nèi)學(xué)士尚宮宋若昭墓志考釋[J].考古與文物,2014,(5):102-103.
[ 4 ] 陳東原. 中國(guó)婦女生活史[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8. 184.
[ 5 ] 北京圖書(shū)館. 西諦書(shū)目[M].北京:北京圖書(shū)館出版社,2004.266.
[ 6 ] [美]高彥頤. 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7 ] 司馬光. 家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kù)全書(shū)本,1992.34上.
[ 8 ] 池上客. 鐫歷朝列女詩(shī)選名媛璣囊[M].明萬(wàn)歷二十三年鄭云竹刊本,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館藏.序2.
[ 9 ] 陶宗儀,等. 說(shuō)郛三種·楊維楨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
[10] 陶宗儀,等. 說(shuō)郛三種·張宗祥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11] [法]伯希和.《說(shuō)郛》考[A].馮承鈞,譯. 應(yīng)再泉,徐永明,鄧小陽(yáng). 陶宗儀研究論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276-295.
[12] [日]渡邊幸三.《說(shuō)郛》考[A].陳越,譯. 應(yīng)再泉,徐永明,鄧小陽(yáng). 陶宗儀研究論文集[C].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02-377.
[13] 景培元. 說(shuō)郛版本考[J].中法漢學(xué)研究所圖書(shū)館館刊,1945,(1):19-32.
[14] [日]倉(cāng)田淳之助.《說(shuō)郛》版本諸說(shuō)與己見(jiàn)[A].賈莉,譯. 應(yīng)再泉,徐永明,鄧小陽(yáng).陶宗儀研究論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38-354.
[15] [美]艾騖德.《說(shuō)郛》版本史[J].馬曉林,譯.國(guó)際漢學(xué)研究通訊,2014,(9):387-438.
[16] 昌彼得.《說(shuō)郛》考[M].臺(tái)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17] 景培元.說(shuō)郛子目異同表[J]. 中法漢學(xué)研究所圖書(shū)館館刊,1945,(1):43.
[18] 張宗祥.鐵如意館隨筆[M].浙江省文史研究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9.
[19] 徐三見(jiàn).汲古閣藏明抄六十卷本《說(shuō)郛》考述[J].東南文化,1994,(6):112-127.
[20]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1] 瞿冕良.中國(guó)古籍版刻辭典[M].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1999.
[22] 尤海燕.《歌林拾翠》刊刻年代考論——兼論奎壁齋鄭元美的刊刻活動(dòng)時(shí)間[J].文獻(xiàn),2010,(3).
[23] 黃永年.介紹一個(gè)世紀(jì)前的童蒙讀物[J].陜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7,(4):164-165.
[24] 王相.校訂女四書(shū)箋注·潘遵祁序[M].蘇州崇德書(shū)院刊本,中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