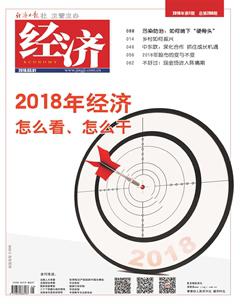農民工鄭世高的返鄉路
王芳
鄭世高,40來歲,個頭不高,身材健壯,頭發濃密、直立,夾雜著不少白發。在北京開往菏澤的Z601次擁擠的車廂過道里,記者跟這位返鄉的農民工兄弟聊了起來。在城鎮化和農民兼業化的道路上,他的經歷或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鄭世高是河北省衡水市棗強縣唐林鄉東徘徊村的村民,小學畢業。從16歲開始便在外闖蕩,20多年,天南海北,他跑遍了大半個中國。
“我都記不清換過多少個工作、多少個老板了。長的兩三年,短的一兩個月。”他訕笑著說。
兩年前,他到新疆烏魯木齊侄子的工程隊裝空調。冬季停工,他臨時接到在北京的活,又干了一個多月。
“我是電焊工,年輕時在工地上邊干邊學,沒有專門師傅教,基本上是自學的,也就能焊個水管,要求高的咱也干不了。干得時間長了,自然就會有人找你了。老板怕出事,一般都給買個意外險,一年兩三百塊錢吧。工地上基本都管吃住,每天要干9到11個小時,反正干一天有一天錢,不干就沒有。每天收入100多塊錢,工資基本都能結清。都是體力活,沒什么周六日、節假日。業余時間也就看看手機、電視,偶爾喝頓酒。”從烏魯木齊到濟南的火車路過衡水,要跑36個小時,鄭世高會選擇臥鋪,不過,趕上過年買不到票也只能坐硬座了,還能省些錢。
經過多年打拼,兩年前,鄭世高在縣里買了房。雖然如此,由于缺少長期穩定的收入保障,他依舊無法完全脫離農村的土地。鄭世高說:“村里還有12畝地,其中有幾畝種的我哥家的地,一半種小麥和玉米,去掉成本一畝地能劃五六百塊錢,另一半種的薄皮核桃樹,當時說有專家指導,結果全村幾百畝核桃,越種皮越厚,連年減產,第一年收了6000斤,去年只收了一麻袋!樹死了一大半,樹干里都空了,也沒人要。土地流轉費一畝200元,高了沒人要。村里種地的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年輕的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有了錢都住到縣城上,要么在其他地方買了房子。啥都能干,就是地不能種了!”
說到兩個女兒,鄭世高的臉上現出一些喜悅。“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小學。上學是不要錢了,可光補習費一年就要三四千元。一個月零花錢也得兩三百塊。明年我就不打算出來了,想著回家干點什么吧。孩子大了不聽話了,我老婆讓我回家管管她們。”鄭世高的微信里出現最多的是和孩子有關的話題。一篇文章“告訴孩子:幾年的放縱,換來的是一生的卑微”被他細心收藏;一張煎雞蛋和饅頭片的照片,也被他驕傲地曬了一把,因為那是姑娘親手給他做的。
鄭世高的微信頭像寫著一句話:“奮斗吧,青春。將來的你會感謝現在拼命的自己。”許許多多像鄭世高一樣在外打拼的人用勤勞的雙手在創造自己的幸福。事實上,鄉村振興戰略中,需要的就是這些有技能、肯吃苦又年富力強的農民工,他們是主力軍,但絕大多數農村地區顯然還缺乏足夠讓他們下決心回鄉創業的吸引力。充分地釋放人的生產力,為這些農民工以及下一代農民工提供更多教育、學習和就業的機會,我們的鄉村、城市才會建設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