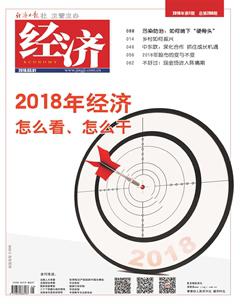上市并購新退路
于佳樂
在大盤低迷及去年6月證監會取消重組上市配套融資,提高重組門檻,全面收緊“炒殼”后,不少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方案“流產”。且在并購重組委上臺短短一周內,已經否決掉了新文化、電光科技、寧波華翔、*ST商城4家上市公司的并購重組方案。一時間,自2015年井噴的并購重組市場到2017年6月開始驟然轉寒。監管層、券商、上市公司都在紛紛思考,未來的并購重組方案怎么才能玩得轉?
并購數量較上年同期下降40%
截至2017年11月底,上市公司并購涉及金額合計7843.17億元,而在2015年、2016年,這一數據分別高達9680.46億元、13333.02億元。2017年以來,啟動重大資產重組的公司數量降至360余家,較2016年的約600家下降超過40%。
“實際2006年-2017年期間,整個全球并購市場的發展,均與全球經濟整體趨勢密切相關。”硅谷天堂資產管理集團總裁鮑鉞向《經濟》記者表示,上一個并購交易活躍期是2007年,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而經歷金融危機和2015年后的股災,全球經濟始終處于療傷期,全球并購交易也處于低谷。但隨著以中國、美國以及歐洲經濟復蘇的帶動,全球并購交易的規模、數量,以及占全球GDP的比例還會逐漸進入新高峰。
申萬宏源證券并購融資部總經理洪濤也告訴《經濟》記者,并購重組市場從2013年爆發持續到2016年上半年算是高潮的一輪,而2016年到2017年實際是并購市場的低潮。
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主任張躍文向《經濟》記者表示,近期A股并購交易明顯在減少,主要是因為監管趨嚴,原有交易平衡被打破,買賣雙方都在觀望;投行合規壓力大,不再接手劣質的項目;股價對并購反應更為理性,驅動在降溫;IPO悄然提速,一些企業又去排隊;好資產一級市場價格不低,融資渠道通暢。
的確,張躍文所指出的監管趨嚴,也是導致當前國內上市公司并購數量趨冷的另一主因。
2015年A股外延式并購規模達到了歷史高點,但與此同時也不斷暴露出諸如忽悠式并購、花式借殼、圈錢式融資、套利式入股等市場套利行為,侵害上市公司利益。2017年,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和證監會的總體部署,上交所將防控市場風險、服務實體經濟中心任務,牢牢嵌入并購重組方案信息披露問詢中。全年累計審核重大資產重組預案99單,督促公司補充披露各類問題1100余項,要求中介機構發表意見800余次,監管約談財務顧問10余次。經過監管,十余單“類借殼”、標的資產質量疑點明顯和存在利益輸送嫌疑的重組方案主動終止。
“我們發現A股市場每一輪變化周期都是隨著監管政策的不斷變化而收緊。尤其對借殼上市的收緊,市場會產生很大的變化。”洪濤說,從2011年證監會制定借殼上市標準到2013年底證監會對借殼上市標準等同新股IPO規定,再到重組新規在實際控制人認定、交易資產標準、股份限售期限,以及權責追溯機制等多方面的監管要求,導致市場開始趨冷。再加上IPO在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的整體加速,使得并購標的迅速減少,投資公司借殼資產瞬間消失,并購市場出現結構性的改變。
政策與市場規律脫節
上市公司開展并購活動幾乎每天都在上演,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市值管理、擴大公司發展潛力,其中也不排除有些公司是在炒概念。但鮑鉞向《經濟》記者坦言,國內并購業務真正能做成功的非常少,成功率幾乎不超過50%。甚至可能做十個并購項目,最后也就成功一個,最多兩個。
分析其原因,無非是行業有很多的痛點需解決。比如新經濟行業迅速發展,大部分公司都需要其助力,但上市公司對新經濟行業收購目前還有一個障礙,就是證監會的意見和市場發展的規律存在脫節。“目前證監會并購估值一般在10倍到20倍之間,但是現在市場中新經濟行業的估值無限大,沒有一個界定標準。”鮑鉞說:“比如京東,成立14年至今沒有盈利,但現在其估值已經達到幾百億美元。又例如前些天我們看一個做芯片的公司,公司什么都沒有,設備生產線都是租別人的,估值還50個億。”
據他介紹,2016年主板、中小板及創業板已實施的重大資產重組中,并購標的平均值率分別為630%、815%、1031%。特別是游戲、互聯網、廣告影視等輕資產熱點產業,并購標的評估溢價率甚至超過50倍。
上市公司并購整合的目的是要達到1+1>2的效果。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同一個行業并購同一個企業,產生的變化都是不一樣的。設定的并購策略和交易價格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更何況,一些上市公司并購不是出于公司經營的實際需要,而是以資產上市溢價、利益輸送和財務扭虧為主要目的,脫離了并購重組的本源。這些重組活動除了具有短期價值效應,中長期來看對公司業績改善的意義不大。”張躍文表示。
改道現金收購成大勢
如何恰當選擇支付方式,一直是企業并購過程中關注的重要議題。支付方式的選擇,關系著企業并購是否順利完成和并購績效,甚至影響企業未來發展。
洪濤表示,隨著IPO的加速,以及結合去年頒布的減持新政、再融資新政等綜合因素,本應該導致IPO節奏有所減緩。但2018年開端卻發現IPO節奏反倒大部分提升了,這導致我們原本預測隨著IPO加速,二級市場,尤其是中小創企業估值的回歸,并購業務在未來2年-3年有個“耐克式拐點”的再平衡提前出現了,并購市場更有競爭性,尤其是在未來股市不明朗情況下,換股收購數量可能會有所下降,現金收購會有大幅度提升。
在鮑鉞看來,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100%現金支付的并購無需證監會審核。那么在并購審核趨嚴的背景下,現金收購將是一條捷徑。而且,現金收購可以將虛擬資本短時間轉化為現金,不必承擔證券風險,交割簡單明了。日后也不會受到兼并公司發展前景、利息率以及通貨膨脹變化的影響。
“但是,并購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動輒幾億元甚至幾十億元。如果完全使用現金支付需要動用巨大的資金,這對一般的上市公司來說也是不小的壓力。”鮑鉞說,同時現金收購目標公司不會淡化現有股東權益,企業將面臨沉重的現金流負擔,而且現金收購無法享受稅收優惠。
資產荒下新配置
洪濤認為,從上市公司的角度來看,雖然并購成功的數量比例是下降的,但并購的熱情并沒有大幅度減退。根據一行三會發布的銀行債權轉股權新規,使取得絕對收益的并購基金,包括債轉股基金,過橋融資基金大有可為,甚至是未來并購的主力軍。
晨暉資本合伙人張磊也有相同的觀點。他告訴《經濟》記者,目前上市并購策略有兩大方向,一個是把行業業務做好,通過并購去吸納市場客戶,吸納優質的資產,縱向整合。或者上市公司發展變遷,在尋求第二產業,橫向布局。
另外,隨著消費升級興起,海外的資產很便宜,也很優秀,所以上市公司做海外資產并購也不乏是一個好方向。
“我們之前在做制造業并購的時候就發現,并購海外資產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國內80%的制造業或者智能制造的公司上市后,在同業內實際沒有什么值得并購的了,因為它的技術很可能是同行業最好的。為了擴大市值,假如一家企業利潤為1億元,要想并購同行業利潤為5000萬元的企業,那么并購價格至少要在幾億元。實際上被并購企業的技術通常與并購方企業技術水平差不多,甚至還不如它,那就完全沒必要以這么高的價格并購。”同系資本創始合伙人朱鷖佳向《經濟》記者說,國外企業標價并不高,很多上市公司發現這一點后,都跑到國外找性價比高的技術。
邁向新臺階還需3年-5年
不難發現,現金收購、并購基金、海外收購都是上市公司并購未來的發展趨勢。至于并購行業的發展,朱鷖佳認為,即使目前并購環境趨冷,但未來并購趨勢不會減少。“至少從我從事的工業領域來說,制造業的升級,智能制造的普及,人工智能化,數據化要改變所有的傳統工業體系,所以里面的并購機會很大。而且并購的本源是進行效率提升,技術提升,創造價值,所以需求不會少。至于錢從哪里來,國內資本市場豐富,錢是不缺的。”
張躍文表示,近階段監管機構加強對上市公司重大重組監管,其目的是為了清理市場上的“跟風式”“忽悠式”等重組亂象,減少市場對重組題材的炒作,讓上市公司重組回歸本源。所以,未來玩概念、忽悠式的并購意圖沒辦法再繼續,市場不接受。
“同時,受制于再融資政策的約束,一些做大股本、做大市值需求的中小型上市公司或是2018年并購重組的主力。”張躍文說道。
而鮑鉞認為,有一天國內的上市公司之間能像美國一樣進行換股并購,這才說明我國并購重組環境趨向更加成熟,上了一個新的發展臺階。“就目前情況看,我們至少還有3年-5年的時間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