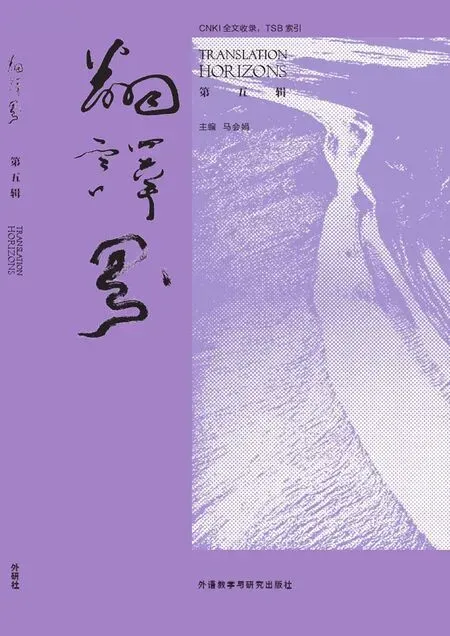論當代著名翻譯家董樂山*
陽 鯤
廣東財經大學
1.引言
董樂山先生(1924—1999)是我國當代著名的翻譯家,他才華橫溢,畢業于中國第一所現代高等教會學府——上海圣約翰大學。自1950年進入新華社外文部以來,從事翻譯工作近五十載,孜孜以求,在翻譯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董先生翻譯的體裁包括新聞、文學、歷史、社會科學,其譯著卷帙浩繁,代表譯作《西行漫記》《一九八四》為國內思想界廣為推崇,影響深遠。其他主要文學、歷史譯作均為譯界精品,包括《中午的黑暗》《奧威爾文集》《西方人文主義傳統》《探索的路上》《冠軍早餐》《囚鳥》《古典學》《蘇格拉底的審判》《巴黎燒了嗎?》《知識分子寫真》《太陽帝國》。與他人合譯學術作品《基督的最后誘惑》《馬克思和世界文學》。董先生還常為他人作嫁衣裳,曾負責校訂眾多巨著,如《第三帝國的興亡》《光榮與夢想》《美國志》《美國新聞史》。校訂這些由多人合譯的大部頭作品費時辛苦,可以說,是董先生的辛勤付出幫助成就了這些經典書目。
在翻譯研究領域,董樂山先生結合豐富的翻譯經驗,探索翻譯理論問題,涵蓋語言、文學、文體、詞典、文化翻譯等多方面,不僅涉及傳統翻譯理論的諸多方面,對翻譯的要求與本質、翻譯的方法和技巧都有精辟論述,而且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術語翻譯、翻譯批評、譯名改革等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有力地促進了當時中國翻譯理論的發展和建設。董樂山先生還與劉炳章先生共同編纂了《英漢美國社會知識小詞典》,共五百多頁,四千余詞條涉及天文、地理、軍事、政治、歷史等眾多方面,多數條目為一般詞典及百科全書所不載,是對我國英語讀者和譯者極為有用的一本工具書。
然而,翻譯學界對這位在翻譯實踐與理論均有建樹的學者型翻譯家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本文介紹董樂山先生的翻譯作品,彰顯其翻譯行為的時代意義與社會責任,并分析其翻譯思想,確認其在當代中國翻譯史上的重要地位,以此紀念這位離開我們近二十年的一代翻譯大家。
2.董樂山之譯作
2.1 文學譯作
董樂山早年接受私塾和教會小學的中西文化熏陶,中學時期開始大量接觸中國近代文學作品,并發表過詩作,創作過短篇小說、書評和影評。他在1942年至1944年近三年的時間里每月定期為上海一個大型綜合性文藝刊物撰寫劇評專欄,這些劇評筆鋒犀利,分析老到,至今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1942年他考入圣約翰大學文學系,主修英國文學,師從王文顯、姚克等名師,西方文學作品原著使他領略到世界文學之美。董先生在青年時代就經歷了扎實的中英文語言錘煉,具備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和思想深度,這類綜合修養無形中奠定了他成為文學翻譯佼佼者的堅實基礎。
年輕的董樂山熱愛文學,又懂英文,在大學期間開始試筆文學翻譯。他畢業后進入新華社從事新聞翻譯,但仍然鐘情于文學翻譯,于是向出版社毛遂自薦,要求翻譯一本外國文學作品,最終得以與人合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小說《紅光照耀著克拉德諾》195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但扉頁上未署董樂山的真名。1978年他受老一輩出版人范用、沈昌文之邀,翻譯埃德加·斯諾夫人記述剛剛逝世的斯諾與病魔斗爭的一本小冊子《我熱愛中國——在斯諾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這是董先生獨力翻譯完成的第一本書。1979年重譯斯諾的報告文學名著《西行漫記》,在董先生的文學翻譯事業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他的譯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初版即印30萬冊,極受歡迎,兩年左右即發行165萬冊(張小鼎,2006),之后國內各家出版社再版時都依據這一版本。董樂山譯本成為斯諾原著漢譯史上的經典(陽鯤,2015)。
此后董先生翻譯的文學作品包括著名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自傳三部曲之一的《傷殘的樹》(1983),英國作家奧威爾的《一九八四》(1985)、《奧威爾文集》(1997),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勒震撼世界的名著《中午的黑暗》(1988),當代美國黑色幽默大師馮納格特的《囚鳥》(1986)、《冠軍早餐》(1998),美國當代中短篇小說選《鬼作家及其他》(1987),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蒂的《赫莉小姐在旅行中》(1988),約翰·奧哈拉的《九十分鐘以外的地方》(1988),希臘名作家卡贊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誘惑》(1991)(合譯),美國作家拉萊·科林斯與法國作家拉皮埃爾記述二戰的28萬字報告文學巨著《巴黎燒了嗎?》(2002),英國作家勒卡雷的間諜小說《鍋匠,裁縫,士兵,間諜》(2009),英國作家巴拉德的長篇小說《太陽帝國》(2010)。董先生還翻譯了文集《探索的路上》(1997)和《知識分子寫真》(2010)。
董先生連續出版的一本又一本譯作,足以說明他在譯介西方文學和文化上的巨大貢獻。由于其突出的文學翻譯成就,1994年他與楊憲益、沙博理、趙蘿蕤、李文俊同獲“中美文學交流獎”。董先生的翻譯文筆雋永流暢,朗朗上口,評論界認為他的譯文“對我國翻譯文風從歐化到中國化的轉變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亦波,2001:7)。學術界、出版界對其評價也很高,“《讀書》雜志前主編沈昌文說董樂山先生的選書有思想性,不單純為翻譯而翻譯,董譯有啟蒙作用。作家王蒙說董樂山的翻譯作品得風氣之先、開國人眼界”(潘小松,1999)。1999年董先生逝世,中國文學翻譯界痛失一位馳騁沙場、卓建功勛的老將。
2.2 新聞譯作
大學畢業后,1947年至1949年間,董樂山先后在當時國民黨的機關報《東南日報》擔任新聞版編輯、在美國新聞處上海分處工作,此后他進入新華社外文部從事翻譯工作。新聞工作是他的老本行,英語又是其特長,因此他在這一崗位上如魚得水。董樂山從普通翻譯做起,英文嫻熟、工作出色,很快就獨立擔綱。當時一般翻譯每小時只能翻譯三四百字,而他每小時至少可翻譯七八百字,最快時可達千字,而且文字質量高。同事的評價是“一天譯一萬字,一般人難以置信。但以董樂山的英文底子,他確實能做到。”(曹德謙,2001:396)我國現在流行的許多外國名詞的翻譯,都是他那時確定的,譬如“超級市場”“威懾”(董樂山,2001b:153),“穆斯林”(董樂山,2001a:400)。資深新聞人、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李慎之認為,
老董對于提高新華社當時的翻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我現在回憶那個時候,英文比他好的大概就沒有。董樂山到新華社之前在美國新聞處干過翻譯,但他自己說新華社的工作經歷給了他很大好處。董樂山是有名的聰明人,原來翻譯主要憑才氣,比較隨意;到了新華社以后得一字一句地摳。翻譯部不但幾乎沒有大學生,而且還有在陜北延安學會英文的老鄉,摳是摳得比較細,缺點是一字一句都要對號,結果越是對號越是對不上。董樂山就有很大的優勢:既有對號精神,又能靈活運用。至今,老董都屬于新華社最好的翻譯之列。(李慎之,2001:385-386)
正是出于多年來對于新詞的敏感與愛好,董先生自20世紀70年代起每天讀書看報做筆記,一天要做二十余張卡片,日積月累,便有了自己編一本美國新詞詞典的想法。終于在1984年,他在劉炳章的協助下編纂出版了《英漢美國社會知識小詞典》,四千余詞條涉及天文、地理、軍事、政治、歷史、掌故、宗教、神話、學派、組織、商標、口號、新詞、縮寫、報紙雜志、電視節目、戲劇藝術、知名人物,以至外號、諢名、俚語、俗稱、賭博牌戲等眾多方面,其中多數條目為一般詞典及百科全書所不載,是對我國英語讀者和譯者極為有用的一本工具書。1995年,董先生對這一詞典進行了共兩千余詞條的修訂和增補。
新中國成立后,新華社是我國新聞翻譯的權威機構,而董樂山是當時新華社優秀的翻譯工作者。他從1949年冬天考入新華社外文部到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期間,歷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審稿、業務秘書,每天報上都有他的譯文發表,有時還占整版或半版的篇幅,雖然這些都是集體的翻譯工作,算不到個人頭上,他仍是我國新聞翻譯事業當之無愧的開拓者。
2.3 學術譯作
西方學術著作的譯介工作潛藏著譯者對中國社會的責任心和真知灼見,是一項意義非凡的事業,清末民初的大思想家嚴復正是憑借學術著作的翻譯來啟迪民智。20世紀60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董樂山讀到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撰寫的德國納粹通史《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他在兩周之內把這部長達一千多頁的書一口氣讀完,并致信世界知識出版社推薦此書。因為書的部頭太大,出版社決定由九人合譯,由董樂山領銜并校對。1963年,中文版《第三帝國的興亡》內部發行,不久它便成了外傳最廣泛的“內部書”。十年后董先生借該書重印的機會,重新逐字逐句校訂,足足花了一年時間。這部書膾炙人口,在中國知識界影響甚巨,也確立了董先生在翻譯界的地位。此后,董先生參與校訂了美國現代史巨著《光榮與夢想》(1978),與梅紹武、蘇紹亨和傅惟慈一道翻譯了牛津大學柏拉威爾教授50萬言的《馬克思和世界文學》(1980),傳播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摘譯)(1981),觀照人文主義源流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1997),關于西方文化傳統的普及讀物《古典學》(1998),以及美國著名左派老報人斯東(I.F.Stone)引人入勝的學術著作《蘇格拉底的審判》(1998)。他還單獨校訂了卷帙浩繁的《美國新聞史》(1982)和《美國志》(1987)等。
這些經久不衰的學術譯作無不滲透著博學的董先生的心血。他作為翻譯家對歷史學、新聞學、西學啟蒙的貢獻用“甘作嫁衣”“潤物無聲”來比喻再恰當不過。“他的譯作無一不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能對中國知識界和中國社會產生較深遠的影響。”(龐旸,2002)
3.董樂山的翻譯思想
董樂山先生在譯事之余,善于總結實踐經驗,關注翻譯熱點問題,在翻譯理論方面很有建樹。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表了多篇論文,針對當時突出的翻譯相關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翻譯主張,其翻譯思想可以歸納為:論如何翻譯,評英漢詞典,談翻譯批評,嘆翻譯職業。
3.1 論如何翻譯
董先生在翻譯研究方面的論文對如何進行英漢翻譯的問題著墨最多,重點論及新名詞的翻譯和翻譯的要求兩大主題。
思想家嚴復有言:“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一名之立,旬月踟躕。”(1984:137)。可見,新名詞的定譯實屬不易。對于新詞的翻譯,董先生亦是“旬月踟躕”,深有感觸,為此他寫作了近十篇論文,探討外國地名、人名、商標名、外來語、新名詞的翻譯,既有舉例,又有論證。有關新名詞的翻譯,他主要有三點認識:(1)學術詞匯翻譯需要創新的同時亦要保持慎重,避免出現將“朝陽門”改為“向陽門”的幼稚錯誤(董樂山,2001b:274-275)。(2)一個外文名詞的翻譯和解釋是兩回事,解釋可以用三言兩語把一個詞盡量簡潔地說清楚,而翻譯則只能用一個或兩個對等或相當于對等的字,把它翻譯出來(同上:286)。(3)譯名可以中國化。
所謂“中國化”,并不是一定要選用中國人名中常用的漢字來譯外國人名,這樣的確會產生金發碧眼的洋人穿上長袍馬褂這種不倫不類的效果。……但是為什么不能來一個折衷,比如說把人名地名用字縮短一些,只用三個漢字或四個漢字?因為外語人名地名中,有的雖然很長,也并不是每個字母都發音,即使發音,也不是每個音節都是重讀的。……我懇切希望提出反對的意見的同志,除了堅持“名從主人”這一條原則以外,也要為讀者尤其是從未接觸過外文的讀者著想著想,這樣才能有希望找到兩全其美的辦法。如此,則對溝通中外,功莫大焉。(同上:116-117)
上述觀點在今天仍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意義。董先生譯著頗豐,譯出的文字不止千萬,他對于翻譯的要求見解深刻,既有語言學角度的反思,也有文化層面的參悟。在《形合與意合》(董樂山,2001b:98-99)和《概念的對等和字面的對等》(董樂山,2001b:96-97)中,他精辟地指出英語和漢語的結構差異及其對翻譯的啟示。通過《人名的借喻》(同上:300-301)、《當代英語中的借喻》(同上:109-114)、《翻譯與知識》(同上:85-89)、《學些中國近代史知識》(同上:238)這些文章,他著重強調翻譯工作者需要具備各種學科和社會生活的豐富知識。在《關鍵在于理解》(同上:92-95)、《翻譯與政治》(同上:90-91)、《統一與多樣》(同上:100-102)中,他反復強調忠實理解英語原文的重要性。在《翻譯的要求》(同上:81-84)中,他提出做好文學翻譯的三個要求,即:對原文要有透徹的理解,提高漢語表達能力,要有淵博的知識。
董先生的上述翻譯思想在其譯作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主譯的《第三帝國的興亡》被評論界譽為“對我國翻譯文風從歐化到中國化的轉變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王東風(2014)詳細分析了該譯作中的一個片段的“得意忘形”、出神入化。
3.2 評英漢詞典
董樂山先生因工作與興趣的雙重原因,接觸到不少英漢詞典,但真正感到得心應手的卻不多,因此每當遇到在他看來好用的詞典,不免進行一番介紹與評論。他曾對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綜合英漢大詞典》(董樂山,2001b:153)、1984年的《英華大詞典》修訂第二版(同上:156-161)、1991年三聯書店的《新知識英漢詞典》(董樂山,1992)、1997年的《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四版(董樂山,2001b:162)以及《藍登書屋韋氏英漢大學詞典》(同上:154)作過評介。他對詞典出版求快與求全的矛盾,給出了以下對策:
一本詞典的出版存在著快與全的矛盾。表面看來,似乎要快就不能求全,但在實際上,若是單純求全,總想盡可能多收一些新詞,出書就慢,結果也就越落后于語言的發展,這樣反而越不能達到求全的目的。因此出版英語詞典,恐怕要打破一勞永逸的求全思想,只有靠勤修快出,才能跟上語言的發展,才能做到相對的全。最好是三五年出一修訂本。當然,這樣做在目前國內的技術條件下可能有困難,但是要迎接信息革命的到來,出版印刷工作在體制上和技術上就需要來一場革命。(董樂山,2001b:156-161)
董樂山先生對英語詞匯敏感細心、見多識廣,對于詞典編纂更是身體力行。從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開始收集材料,終于在1984年出版了《英漢美國社會知識小詞典》,并于1995年完成對該詞典的修訂和增補。如前介紹,這是一本于翻譯工作者大有助益的工具書。董先生從未受過詞典編撰的訓練,編纂該詞典純粹出于個人興趣,但他偶然發現,他編的詞典原稿的體例甚至排樣都竟然與一家以出詞典著名的美國書局所出詞典《1962年以來的英語》(English Since 1962)一模一樣(董樂山,2001b:165)。如此巧合只能說明董先生的天賦與用心。
3.3 談翻譯批評
董樂山先生對翻譯批評的見解主要體現在1995至1998年間發表的五篇論文當中。歸納起來,他在文中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問題:(1)出版部門的責任;(2)如何開展翻譯文學批評;(3)如何評選翻譯人才。其中出版社的問題最為突出,這首先體現在出版的譯作質量堪憂。出版社的有些編輯未能對譯文的質量嚴格把關,導致市場上充斥著大量錯誤百出的偽劣產品。其次,出版社大量翻譯出版流行小說、重譯經典作品。就如何開展翻譯文學批評,董先生所提出的兩個困境頗具代表性:
翻譯批評的稿子不易約到,主要原因是因為翻譯質量不高,認真批評起來不免挑錯,而把別人的錯誤亮出來,是要得罪人的。寫文學批評,哪怕你批評的是如王蒙那樣的大家,即使過火一些,他聽了不高興,也無可奈何。……而翻譯批評則不同了,批評者不懂外文,沒有翻譯經驗,是無法批評別人譯文的對錯和優劣的,你一旦得罪了對方,對方也搬出你的譯作來挑錯,誰能保證自己譯文中一個錯也挑不出來的呢?《尤利西斯》蕭乾、文潔若譯本和金堤譯本的比較,除了上述顧慮以外,還有一個常人很難逾越的障礙,即《尤利西斯》之艱深難懂,讀懂——哪怕是讀譯本——已不容易了,更何況一評短長!(董樂山,2001b:128)
翻譯批評要就語言轉換后的譯品與原作在思想、形象、風格、手法諸方面的差距大小以及造成差距的原因加以探討(王克非,1994),批評者必須領略原作及譯作效果同異之處,了解原作者及譯者相同或不同的動機,需要兼備理論素養和翻譯實踐,董先生的上述評價確實反映了翻譯批評是我國翻譯學界至今仍未有較大突破的一個領域。
3.4 嘆翻譯職業
董樂山先生從事翻譯工作將近半個世紀之久,他把自己的心理狀態分為三個階段:“從不知天高地厚,到自以為得心應手,最后是深感力不從心”(董樂山,2001b:129-130),對翻譯是“又恨又愛”(同上,82),這“恨”很大程度源自對這一職業現有問題的感慨與擔憂。例如,他深感翻譯報酬過低(同上:118-119),譯者署名問題敏感(董樂山,2001a:305-309),為人校訂譯稿,不如自譯(董樂山,2001b:120-121),翻譯工作者在社會上不受重視(同上:105-106)。早在1981年,他就撰文《大家一起來重視翻譯工作》呼吁:
根據翻譯工作者本身的學術性質和要求,在社會科學院系統下成立一個翻譯研究所,對翻譯工作進行歷史的、全面的、發展的研究。這里牽涉到自古以來中外翻譯理論的研究,經驗的總結,比較語言學的研究,詞典的編纂,電腦翻譯的研究和試驗,等等。
……
成立翻譯家協會或翻譯學會之類的學術團體,對內團結全國翻譯工作者,切磋業務,加強聯系,保障權益;對外與世界各國相應組織進行聯系和交流。(董樂山,2001b,103-104)
一年之后,董先生的第二條建議得以實現:翻譯工作者自己的群眾性學術團體——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于1982年正式成立。1983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創立的《翻譯通訊》改為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會刊《中國翻譯》正式出版。而董先生期待的第一條至今仍任重道遠。
董先生作為翻譯界的前輩,對翻譯人才的選拔也曾作過思考。他認為,
人才肯定有,只是沒有被發現而已。這就牽涉到發現的過程,也就是評選的過程。評選方式恐怕需要效法美國的普利策或全國圖書獎,組織一個評委會,到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僻靜之地,住上個把月,關起門來中外文對照仔細評讀由各出版社初步推選的作品,然后討論評定最后人選,這樣不僅方法嚴謹,而且一定會發現“后繼有人”!(董樂山,2001b:133-134)。
4.結語
《中國翻譯家研究》的編者方夢之和莊智象(2016:6-8)這樣總結中國翻譯家的特質:他們有使命感、責任感,他們的譯作經世致用,翻譯內容與其專業雙雙映照,他們中西融通,精益求精。這些特質董樂山先生無一不具備,他以文學青年出道,在社會動蕩的三四十年代積極愛國、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中堅守志趣,終于迎來改革開放后個人翻譯事業的巔峰。他終其一生徜徉在英漢語言文字的世界,翻譯不同學科門類的優秀作品,同時著書立說,總結經驗,啟迪后人,構建了自己的翻譯思想,成為當代翻譯大家,為中國的翻譯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董樂山先生對當代中國翻譯事業的貢獻是中國翻譯史、翻譯家研究中不應忽視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