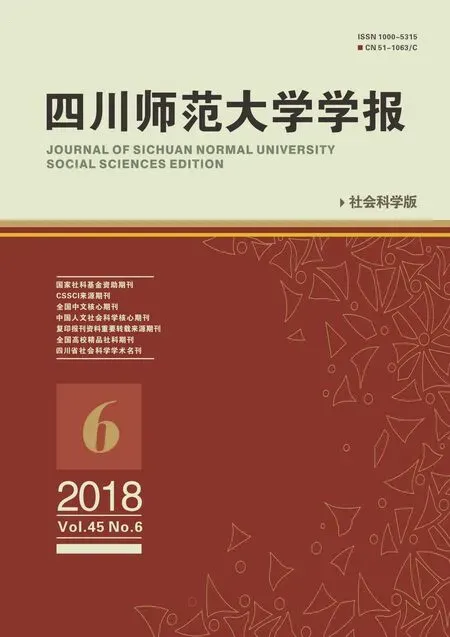刑訴法制發展與冤假錯案糾正40年④
(四川大學 法學院,成都 610207)
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我國刑訴法制發展的不同階段,一直都伴隨著對冤假錯案的治理。依循刑訴法制發展的三個階段,我國的冤假錯案治理大體上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7—1985),集中性的政治治理階段。在此階段,對冤假錯案的治理主要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冤假錯案的治理主體主要是黨的組織部門,治理對象則主要是被錯劃為“右派”的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尤以“惡毒攻擊”案件[注]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編《最高人民法院歷任院長文選》,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居多),治理工具主要是依靠黨的組織手段與干部政策。第二階段(1986—2011),常態化的治理階段。在完成大規模的政治平反之后,我國對冤假錯案的治理開始進入常態化。在此階段,刑訴法制成為推動冤假錯案治理的主要參照對象與適用依據,標志著我們對冤假錯案的治理開始由“政治性”的治理轉向“法律化”的治理。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舊的刑訴法制尤其是刑事證據規則、程序保障機制在防范冤假錯案方面的局限性也日益顯現。加之這一時期的冤假錯案治理始終受到“犯罪控制”目標的影響,在一些司法機關內部甚至興起了以消滅無罪判決為目的的改革,由此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的產生。第三階段(2012—),綜合治理階段。2012年,立法機關再次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訂,新刑訴法確立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構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制定了其他司法人權保障措施,上述規范有望進一步預防冤假錯案的產生。與此同時,黨中央、中央政法機關相繼發布了冤假錯案的防治意見,我國的錯案治理開始進入龍宗智教授所指出的“新刑訴法證據規范的實施與防止冤假錯案的專項行動互相促進”[注]龍宗智《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半年初判》,《清華法學》2013年第5期。的階段。此后,對冤假錯案的治理開始進入由單純依靠法條到依靠法條和司法政策相結合、由單方參與到多方參與、由個案治理到系統性治理、由被動治理到積極預防的新階段。
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40年的刑訴發展歷史進程中,對冤假錯案的治理一直貫穿始終,由此形成了刑訴法制發展與冤假錯案治理相互影響、互相推動、共同促進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刑訴法制發展水平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冤假錯案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技術,刑訴法制的發展則進一步推動了錯案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方面的變遷;另一方面,冤假錯案的產生以及圍繞典型冤假錯案所展開的治理實踐,又為刑訴法制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規則治理經驗和強大發展動力,成為刑訴法制變遷的重要推動因素。在刑訴法制不斷進行調整以更好地適應錯案治理形勢的過程中,刑訴法制的現代化程度與理性化水平得以顯著提升。
一 刑訴法制發展對我國錯案治理實踐的影響
其一,刑訴法制發展杜絕了大規模人為制造冤假錯案的可能。
在建國后的30年里,中國一直缺乏一部正式的刑事訴訟法典,“這使刑事訴訟實踐尤其是國家權力的行使缺乏明確有效的規范與指引,進而導致國家權力的形式缺乏明確有效的規范與指引,進而導致國家權力受到的制約相當有限,公民權利遭到不同程度的蔑視甚至踐踏”[注]郭松《試點改革與刑事訴訟制度發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頁。。這一局面的存在,導致文革期間“一些人錯捕、錯押或錯判,人民的民主權利受到侵犯”[注]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頁。。正如已故最高法院院長江華于1978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刑事審判會議上所指出的:“冤假錯案如此之多,所占比例之大,是建國以來沒有的。把這么多無辜的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判刑勞改,甚至殺了頭,這真是觸目驚心啊!”[注]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編《最高人民法院歷任院長文選》,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頁。據不完全統計,在1979年到1982年,經中共中央批準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即有30多件;從全國范圍來看,則有多達300萬干部蒙受了冤屈,更有數以千萬計的因與這些干部有親屬關系或工作關系的干部群眾受到牽連[注]張愛茹《鄧小平與重大歷史事件》,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頁。。正是看到法制缺位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巨大災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決心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其中恢復和重建法制(尤其是刑事法制)則是重中之重。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并決定于198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1979年刑訴法確立了我國刑訴法制的基本框架,為我國刑訴法制發展奠定了基本脈絡和重要基礎。1979年刑訴法確立了人民法院的審判主體地位,規定:“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與此同時,1979年刑訴法還規定了證據制度、偵查程序、審理程序等。這些規范的確立,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有法可依、依法辦案的制度格局”[注]郭松《試點改革與刑事訴訟制度發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頁。,有效避免了大規模冤假錯案的產生。而1996年刑訴法則在1979年刑訴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辯護制度,進一步保障了被告人的辯護權;明確了證據的審查判斷標準,要求“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強調證據的合法收集運用,“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等。這些內容,對于防范冤假錯案的產生,特別是在防止人為制造冤假錯案方面,無疑將發揮重要的遏制作用。
其二,刑訴法制發展提升了冤假錯案的防治水平。
1996年刑訴法首次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根據1996年刑訴法第十二條的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根據新法,“人民法院審理后,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注]景致遠《刑事訴訟立法三十年的國家記憶》,《檢察風云》2012年第7期。。這為真偽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新的裁判準則,體現了“疑罪利益歸于被告人”的法治精神,符合時代潮流。此外,1996年刑訴法還明確了檢察機關對特定案件享有不予起訴的權利,使得疑似無罪案件得以在審查起訴階段得以分流處理,從而進一步豐富了冤假錯案的消解機制。對于這些創制,陳光中教授等評價到,“集中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精神,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注]陳光中、曾新華《中國刑事訴訟法立法四十年》,《法學》2018年第7期。。2012年刑訴法在防范冤假錯案方面有著更大的突破。例如,2012年刑訴法正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增加了羈押必要性審查、改進了二審程序、修改了開庭審理案件的范圍、完善了發回重審制度等,進一步健全了冤假錯案的防治體系。可以看到,從1979年刑訴法到1996年刑訴法再到2012年刑訴法,刑訴法制在規則構建方面越來越重視對冤假錯案的防范。近年來,無罪判決數量一直處于較低水平,某種意義上也顯示出刑訴法制發展在預防和糾正冤家錯案方面的積極效果。
上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刑訴法制發展對于我國冤假錯案治理的積極影響。可以看到,刑訴法制發展不僅杜絕了大規模制造冤假錯案的可能,也大大提升了我國冤假錯案的防治水平,推動了我國冤假錯案治理向法治化、規范化、理性化方向不斷邁進。然而,我們應當意識到,刑訴法制發展往往也面臨階段性、滯后性等方面的問題,這就提醒我們在關注刑訴法制對錯案治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應理性看待刑訴法制在防治冤假錯案方面的局限性。例如,刑訴法制的不完善,尤其是刑事證據制度方面的缺陷,就時常誘致冤假錯案的產生。誠如熊秋紅教授所指出的:“刑事證據制度不嚴格、不完善,是司法實踐中出現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注]熊秋紅《完善證據立法 提高案件質量——刑事證據兩規定評析》,(2010-06-14)[2018-09-07],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06/14/172717.shtml。又如,作為“理性建構”的產物,刑訴法制亦難免同司法實踐產生某種抵牾、脫節,從而削弱刑訴法制的指引評價功能,進而對冤假錯案的防治產生不利影響。
二 錯案治理實踐對刑訴法制發展的影響
其一,錯案治理實踐促進了刑訴法制變遷的“思想啟蒙”。
一部法律在正式修改前,往往會經歷一個較長的醞釀、權衡和博弈周期。在此期間,立法機關主導的專項調研、司法機關展開的利益博弈、專家學者的建言獻策以及社會公眾的意見表達等都能對法律文本的內容修訂產生重大的影響。進入2000年以來,產生于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諸多冤假錯案,在多元化網絡傳媒的傳播下逐漸為社會公眾所知曉。圍繞著對冤假錯案的持續討論,為刑訴法制變遷匯聚了重要的民意基礎與制度資源,有力地促進了刑訴法制變遷的“思想啟蒙”。在對冤假錯案的討論過程中,黨政機關、社會公眾、法學專家等紛紛表達對冤假錯案的治理需求,推動了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在錯案治理方面形成共識,使得刑訴法制在規則建構方面更加凸顯對冤假錯案的防范。事實上,有論者曾談到,2012年刑訴法“排除合理懷疑”等相關規定的產生,某種意義上即是學界、民意與媒體合力推動的結果(在該論者看來,1996年刑訴法與疑罪從無要求相距甚遠)[注]邢馨宇《有利被告的當下中國程序話語——兼及〈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之評價》,《環球法律評論》2015年第6期。。左衛民教授也談到,冤假錯案的產生及其治理,促進了程序正義觀念的深入人心。在其看來,這種社會共識構成了第三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深刻的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背景[注]左衛民《背景與方略:中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次修改前瞻——基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的思考》,《現代法學》2015年第4期。。可以說,冤假錯案的大量出現,集中暴露了刑訴法制在防治冤假錯案方面所具有的局限性,而對冤假錯案積弊的批評性話語,又促進了刑訴法制變遷的“思想啟蒙”,進而推動了刑訴法制的局部變遷及整體發展。
其二,錯案治理實踐推動了證據規則的發展。
進入2000年以來,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冤假錯案相繼發生,引發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這些冤假錯案的產生,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客觀中立”形象,引發了政法部門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中央政法機關對此高度重視。2010年,在中央司法體制改革精神的指引下,“兩高三部”共同制定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關于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證據規定”)。從內容上看,“兩個證據規定”確立了證據裁判原則、明確了證據的審查判斷標準、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彰顯了中央政法機關在預防和糾正冤假錯案方面的決心。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正是在此冤獄治理的司法背景下,‘兩個證據規定’才應運而生。在此意義上,認為趙作海冤案是促使我國出臺‘兩個證據規定’的直接原因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注]林喜芬《“兩個證據規定”頒行背景的理論解讀》,《北方法學》2012年第1期。2012年,新修訂的刑訴法全面吸收了“兩個證據規定”所確立的內容,建立起較為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與證據審查標準,試圖從完善證據規則方面加強對冤假錯案的源頭治理。2017年4月,“兩高三部”再次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認定標準以及排除程序,切實防范冤假錯案產生”[注]羅沙、楊維漢《加強人權司法保障 切實防范冤假錯案 五部門聯合出臺非法證據排除相關規定》,(2017-06-27)[2018-09-0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27/c_1121217459.htm。。同年底,最高院印發了“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三項規程”(分別涉及庭前會議、非法證據排除、第一審法庭調查),等等。上述事實說明,冤假錯案的產生及其治理實踐,以一種“反作用”的方式極大地推動了刑事證據規則的向前發展,標志著我國針對冤假錯案的預防和糾正開始進入新的階段。
其三,錯案治理實踐推動了程序法制的變革。
冤假錯案的產生及其治理實踐,除了促進刑訴法制變遷的“思想啟蒙”、推動刑事證據規則的發展之外,也極大地促進了刑事程序法制的發展與完善。仍以2012年刑訴法為例,2012年刑訴法在律師會見、審查逮捕、羈押必要性審查、庭前會議、發回重審等程序方面展開了大規模的創制。從內容上來看,不少法條的內容都汲取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教訓,強化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法制保障,有助于實現全方位、全過程的冤假錯案防范。2013年,中央政法委制定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因應于此,公安部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執法辦案工作切實防止發生冤假錯案的通知》,最高檢制定并下發了《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最高院印發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2014年,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也曾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就在于“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產生”[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第2版。。左衛民教授也認為,為了“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等內容,就必須適時修改《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將這些原則性規定予以細化,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規范[注]左衛民《背景與方略:中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次修改前瞻——基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的思考》,《現代法學》2015年第4期。。可以看到,冤假錯案的產生,對刑訴法制特別是程序法制的完備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一內在要求客觀上為刑事程序法制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發展動力。
上文分析表明,我國的刑訴法制發展與錯案治理之間事實上始終處于交互影響、互相作用、共同促進的關系之中。在刑訴法制發展的40年中,我國的錯案治理實現了由集中治理到常態化治理、由政治性治理到法律化治理、由被動治理到主動預防、由主要依靠法條到依靠法條與司法政策相結合的治理。這種轉變背后反映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這種轉變反映了我國刑訴法制為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司法現實而進行的調整,顯示出我國刑訴法制在促進司法人權保障方面具有較強的回應性,凸顯了執政黨、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在推進刑事領域的規則治理方面的銳意進取和與時俱進;另一方面,這種轉變也體現了錯案治理在我國政治治理體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正因如此,冤假錯案的產生及其治理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撬動并改變刑訴法制本身僵化性,進而在短短40年間推動刑訴法制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從不成熟到日臻完善的變遷。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刑訴發展歷史,相當程度上就是一部深刻反思冤假錯案、不斷推進司法人權保障的歷史。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我們要更加重視對冤假錯案的源頭治理與規律總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刑訴法制朝著更加有利于防治冤假錯案、更有利于促進司法人權保障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