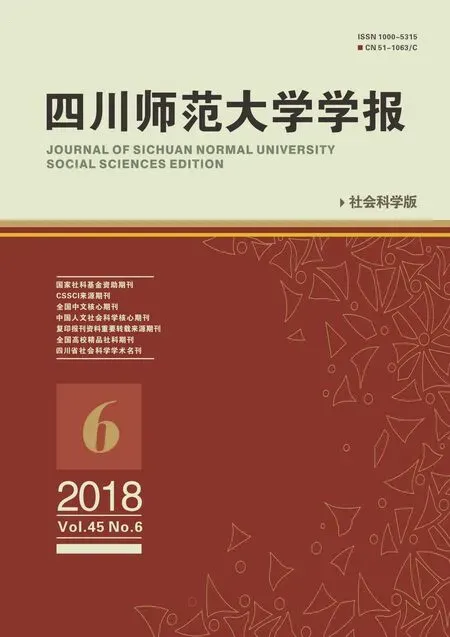從偵查到監察:職務犯罪查辦機制40年
(四川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成都 610064)
職務犯罪是國家公職人員利用手中職權實施的犯罪行為,包括貪污、受賄、瀆職、侵權等。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急速的社會轉型中,我國職務犯罪呈高發多發態勢。為有效打擊職務犯罪,我國職務犯罪查辦機制也經歷了一個從偵查到監察的深刻轉型。有必要回顧我國職務犯罪查辦機制變革之歷程,總結其特點,前瞻其未來。
一 歷程之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務犯罪查辦機制先后經歷了檢察機關一般化查辦模式、檢察機關專門化查辦模式和監察機關專責化查辦模式等多個階段。
(一)檢察機關一般化查辦模式(1978-1997)
1978年,我國開始重建各級檢察機關。1979年,《刑事訴訟法》頒布,規定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瀆職罪以及人民檢察院認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隨著各級檢察機關的重建,我國職務犯罪偵查的檢察機關模式也得以全面重建。但是,在這一階段,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的專門化水平并不高。首先,在司法職能上,檢察機關同時承擔著職務犯罪偵查與批捕、起訴等其他檢察職能。在很長時間內,這些職能在檢察機關內部也缺乏專業化的分工。比如,1988年以前,職務犯罪從立案偵查到偵查終結再到提起公訴,都由一個部門的檢察人員負責,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嚴重缺乏[注]何家弘《論職務犯罪偵查的專業化》,《中國法學》2007年第5期。。其次,在受案范圍上,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并不限于公職人員,同時1979年《刑事訴訟法》還賦予了檢察機關自主確定受案范圍的裁量權,這使得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大大超出了職務犯罪的范圍。此外,1979年《刑事訴訟法》并未針對職務犯罪的特點為檢察機關創設特別的偵查手段,相反還對檢察機關的偵查權限有所限制。比如,1979年《刑事訴訟法》并未賦予檢察機關刑事拘留權。
(二)檢察機關專門化查辦模式(1997-2016)
1996年,我國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第一次修訂。雖然職務犯罪偵查仍由檢察機關負責,但在職能和人員的專業化方面卻有了相當的發展。首先,1996年《刑事訴訟法》將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基本限定在職務犯罪案件上。一方面,收縮檢察機關法定的偵查權限,僅將貪污賄賂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犯罪納入檢察機關法定的偵查權限范圍;另一方面,嚴格限制檢察機關認為需要自己直接立案偵查的案件范圍,將其限定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犯罪上,且須經省級以上檢察機關批準。其次,在檢察機關內部,隨著自偵部門與批捕、公訴、民行等其他部門的分立,以及反貪污賄賂和反瀆職侵權等部門的分化,職務犯罪偵查的專業化在不同層次上均有較大的發展。此外,檢察機關的偵查手段也有所強化。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其自行偵查的案件決定適用拘留;2012年《刑事訴訟法》進一步授權檢察機關在特定案件中可以采取必要的技術偵查措施。但是,受制于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檢察機關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傾向于將職務犯罪偵查權作為其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保障性措施。這樣一種制度定位很大程度上隔離了職務犯罪偵查與公務人員廉潔性和勤勉性之間的關系,既扭曲了訴訟監督權,也弱化了職務犯罪偵查權。就前者而言,它使檢察機關在行使法律監督權時可能凌駕于審判機關之上,從而對正常的訴訟程序構成沖擊;就后者而言,它使檢察機關在查處職務犯罪時可能回避查處起來更為棘手的黨政機關公職人員,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的效果并不理想。事實上,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在反腐敗領域取得的成績,主要由檢察機關之外的紀檢監察部門強勢推動[注]李奮飛《檢察再造論——以職務犯罪偵查權的轉隸為基點》,《政法論壇》2018年第1期。。
(三)監察機關專責化查處模式(2016-2018)
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決定組建監察委員會對本地區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依法實施監督、調查和處置,并將檢察機關的反貪污賄賂、反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偵查部門轉隸到監察委員會。2018年,《監察法》頒布,明確規定各級監察委員會是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從性質上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在整合原監察部門行政監察權、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等權力元素的基礎上,創設了一項不同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獨立權力類型。因此,這種“轉隸”并不僅僅只是組織人事關系的調整,同時也伴隨著權力屬性的重塑。由此,我國職務犯罪查辦機制也進入了監察機關專責化調查模式。在職能上,監察機關主要聚焦公職人員履行職責的廉潔性和勤勉性,與檢察機關主要指向其他機關尤其是司法機關的違法行為具有質的差異性。在對象上,監察機關將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納入監察范圍,比刑法上的“國家工作人員”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加寬泛。在手段上,改革充實了監察委員會的調查權,監察機關可以針對涉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采取留置、搜查、技術調查等強制措施。雖然這些措施在強度上與偵查相當甚至更甚,并且,這些措施實際所發揮的功能亦與偵查無異,但就其性質而言,它并不是“偵查”,因為2018年《監察法》已經明確將職務犯罪的查辦機制構建在“監察權”這一全新的權力類型之上,進而將檢察機關司法性質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改造為監察機關非司法性質的調查權。
二 發展之軌跡
從改革開放40年我國職務犯罪查辦機制的發展歷程看,在黨對職務犯罪查辦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的同時,職務犯罪查辦工作本身也在不斷走向專業化。
(一)黨對職務犯罪查辦的集中統一領導
改革開放40年,黨對職務犯罪查辦工作的領導方式不斷改進,總體趨勢是全面加強黨對職務犯罪查辦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在檢察機關負責查辦職務犯罪的階段,無論采一般化模式還是專門化模式,堅持“黨管政法”都是一項基本原則。但是,在這一階段,黨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領導主要通過在各級黨委設政法委員會聯系指導檢察機關的工作,以及在檢察機關內設立黨組討論決定本單位重大問題來實現。總體上看,這種領導體制加強了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能力,但面對十八大以來形成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的現實需要,這種外生型的領導體制為檢察機關提供的政治支持還不夠堅強有力,同時反腐敗斗爭的資源分散于紀檢監察部門和檢察機關,也不利于形成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體制。在這種背景下,中央進一步推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改造為監察機關的職務犯罪調查權,并將1992年以來實行的紀檢監察合署辦公體制擴展到新組建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從而將黨的領導內生性地嵌入到監察機關的職務犯罪調查活動之中,大大加強了黨對職務犯罪查辦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二)職務犯罪查辦的專門化專業化發展
作為一種權力型、智能型犯罪,職務犯罪的查辦活動有其特殊性。比如,受賄案件中“一對一”的待證事實,凸顯了“口供”在職務犯罪查辦中的特殊價值,增加了職務犯罪調查對口供的依賴性;而瀆職案件中復雜的因果關系,又加大了職務犯罪案件中證明被調查人有罪的難度。同時,由于職務犯罪被調查人一般具有較強的反調查能力且人際網絡通常比較復雜,由專門機關依靠專業手段開展調查活動,往往可以更有效地查明案情。因應這些特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務犯罪查辦逐步走向專門化、專業化。一方面,圍繞“職務犯罪”這一核心構造統一的調查體系。將非公職人員實施的非職務犯罪逐步從檢察機關直接立案偵查的案件中剝離出來,使其偵查權逐步收縮到典型的職務犯罪之中;同時,將檢察機關管轄權之外的公職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犯罪行為歸并到公職人員職務犯罪范疇,進而構造一個覆蓋所有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調查體系。另一方面,提升職務犯罪查辦機制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將職務犯罪的查辦主體從權力受到更多制約的檢察院轉移到對權力的限制更少、因而可以更大的力度打擊職務犯罪的監察機關,以提升職務犯罪查辦的獨立性和抗干擾能力;同時,進一步豐富監察機關法定的查辦手段,使其無須司法機關批準或者同意即可自主決定對被調查人采取留置、搜查、技術調查等強制措施,以提升職務犯罪查辦的有效性。
三 未來之展望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職務犯罪查辦機制經歷了一個從司法權到監察權的深刻變遷。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實踐證明,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極大地提高了職務犯罪偵查的能力和效率。但是,由于職務犯罪在認定標準上仍有一些模糊之處,同時對監察機關職務犯罪調查權的程序控制亦在發展之中,在未來職務犯罪查辦機制的演進之中,仍然有一些未競的改革議程:一是如何實現對監察機關的監督和制約?二是如何實現紀委執規與監委執法的銜接聯動?三是如何實現監委調查與刑事訴訟的有機銜接?
(一)對監察機關的監督和制約
隨著監察機關專責化查辦模式的確立,我國賦予了監察機關非常強大的調查權限。這不僅體現在賦予監察機關自主決定采取留置、搜查、技術調查等強制措施的權力,而且體現在《監察法》為上述措施所設定的條件和程序遠較新加坡等國家寬松[注]熊秋紅《監察體制改革中職務犯罪偵查權比較研究》,《環球法律評論》2017年第2期。。這些措施天然地潛藏著權力被濫用的風險,未來改革的深化必須著力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誰來監督和制約監察機關?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國的背景下,監察機關專責化的職務犯罪調查也必須堅持法治原則。要通過加強黨委領導、完善人大監督、強化社會監督、改進監察機關內部監督、推廣全程錄音錄像等新技術應用等多種方式,構建一個專門針對監察機關的監督體系,切實解決監察機關“燈下黑”問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閉環。
(二)紀委執規與監委執法的銜接聯動
由于各級監委實行與紀檢機關合署辦公的體制,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之后,紀委執紀和監委執法深度交織在一起,一些此前被歸入刑事司法領域的案件可能被代之以黨紀處分或政務處分,進而導致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職務犯罪案件減少。在這種背景下,應當進一步理順紀委執紀和監委執法的關系,明確二者在規范屬性、規整強度和運行機理上的同與不同,并在此基礎上正確區分違反黨紀和違反國法的界限,由紀檢機關和監察機關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依據不同的規范系統對不同的監督對象開展工作,實現紀檢行為與監察行為的有機銜接和有效聯動。
(三)監委調查與刑事訴訟的有機銜接
監察機關不是司法機關,職務犯罪調查也不是刑事訴訟,無論是監察機關收集證據的過程,還是監察機關采取強制性措施的過程,均無檢察機關介入和干預的空間[注]左衛民、唐清宇《制約模式:監察機關與檢察機關的關系模式思考》,《現代法學》2018年第4期。。但是,對監察機關移送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案件,檢察機關應當依法審查、提起公訴;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后,審判機關應當依法審判,這就使得監察機關的職務犯罪調查權與刑事訴訟發生了關聯,但這種關聯的內涵在當下的改革議程中尚未充分展開。未來,應當合理劃分職務犯罪調查權與公訴權、審判權的邊界,在刑事訴訟的架構內通過檢察機關的公訴權、審判機關的審判權對監察機關的職務犯罪調查權進行制約,實現監委調查與刑事訴訟的有機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