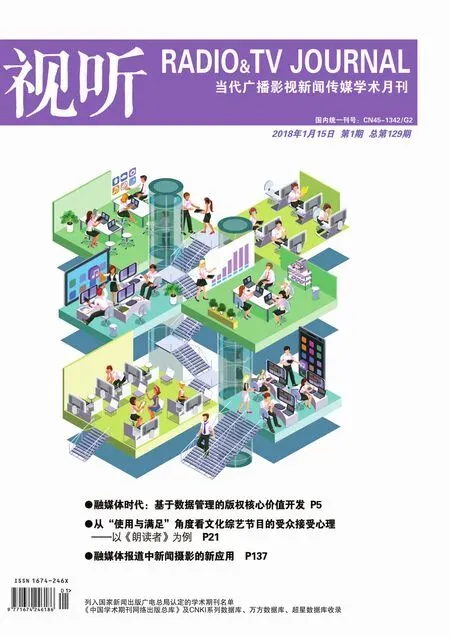新互聯網環境下對有害信息判定和治理的反思
□黃子洋
新互聯網環境下對有害信息判定和治理的反思
□黃子洋
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一方面方便了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使得網絡有害信息傳播加劇。尤其是社交媒體日益成為人們進行網絡活動的主要平臺,網絡有害信息的傳播變得傳播主體更多樣、傳播速度更快、傳播渠道更廣。面對不斷變化的網絡環境,其治理手段也應不斷調整。作為治理的基礎和前提,準確、合理地判定網絡有害信息的范圍也成為應有之義。從立法上明確網絡有害信息的范圍,多措并舉,針對網絡有害信息展開治理,是構建文明、和諧的網絡環境的必然要求。
互聯網;有害信息;判定;治理
在當今我國的互聯網發展中,隨著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及網民自我表達訴求的不斷增強,社交媒體已逐漸成為網絡信息傳播的主戰場,新的互聯網環境正在形成。網絡有害信息的傳播因此變得更加迅速與復雜,從而其治理也就愈發重要。縱觀我國的互聯網治理現狀,對網絡有害信息內涵及外延的判定尚未達到法律制度層面上的統一,且在實踐中對其治理也存在著不統一、不科學等不足。本文對我國互聯網有害信息的既有制度進行梳理,并結合當前的網絡環境對其治理提出建議。
一、當前我國網絡有害信息研究的思路分析
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每個網民都正在從單純的信息閱讀者轉變為集信息制作者、傳播者和閱讀者為一體的網絡主體。言論自由的權利在網絡世界中延伸和擴大,但與此同時,網民們也將隨之深陷有害信息侵擾的泥淖。基于此,加強對網絡信息傳播的監督和管理也就勢在必行。2016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正式發布,這是我國第一部網絡安全領域的基本法,但這部框架性法律在對網絡有害信息的治理上并沒有過多的明確性條款。所以,對于網絡有害信息的判定與治理還有需要學者的進一步研究以及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誠然,目前對網絡有害信息的研究并非空白之地,相關著作成果近年來持續增加。在中國知網上輸入關鍵詞“網絡有害信息”,檢索出相關文獻近百篇,且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就其研究內容而言,縱向上,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網絡有害信息的刑事打擊上,而這一階段網絡有害信息的范圍也多指觸犯刑法限制的信息如涉黃、涉恐等。而近年來相關研究的內涵和外延都不斷擴大,網絡有害信息的范圍不再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規定,其治理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刑法規制。橫向上看,對網絡有害信息的研究多是圍繞治理策略展開,對有害信息本身含義及范圍的判定卻涉獵甚少,且未達到統一共識。鑒于此,本文將梳理網絡有害信息的既有類型,總結現行法律法規中對其范圍的判定及規制,并為我國網絡有害信息的類型構建和治理方式提出建議。
二、當前我國有害信息判定范圍的厘析
近年來,我國對網絡有害信息范圍的判定遵循著從嚴到寬的解釋口徑,越來越多的信息類別被納入到有害信息的范圍中。但有害信息的含義究竟是什么,其劃定標準的依據又來自于何處,諸如此類的問題在現有的研究中并未得到準確的解答。
(一)互聯網有害信息類型化現狀
我國雖已就網絡安全制定了《網絡安全法》,但其中并沒有對網絡有害信息的范圍做出明確判定。此前,涉及到網絡有害信息的相關條文已散見于與互聯網治理相關的部分法律、法規、規章等之中。其中1997年通過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第5條,2000年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第2條第一項和第三項,同年通過的《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第9條、《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15條,2004年通過的《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第19條,2011年通過的《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第16條,201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56條,這些條款明確指出了在互聯網信息傳播中禁止的內容,即網絡有害信息。此外,2017年開始施行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第3條和第16條以概括性條款的形式也規定了禁止傳播的信息內容。梳理上述既有條款可發現,我國對網絡有害信息劃分為政治類、犯罪類、謠言類、侵犯私權類等類別。
(二)網絡有害信息范圍判定的實踐反思
從既有條款中我國網絡有害信息判定存在的問題可窺見一斑。首先,既有立法位階偏低,與現行規定之間不能達到統一。我國既有的涉及到網絡有害信息的規定多是法規、規章以及政策性文獻,基礎性法律目前只有一部《網絡安全法》,其中并未對網絡有害信息的范圍做出明確判定。盡管規定及規章在相關問題的法律適用上更具有針對性,但如果沒有高位階的法律條款加以保護,當同等位階的條款出現矛盾或無法選擇時,就很難進行統一的法律適用。其次,既存的有害信息類別中多為政治性有害信息限制條款,且其范圍界定不明確。在實踐中,網絡信息被屏蔽、刪除、禁發等情況多出現在對政治性有害信息的管制上,但其中很多被限制的信息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政治性有害信息,而僅僅是相關政治事件的“邊緣信息”,如評論信息、調侃信息等,但在實踐操作中卻被作為有害信息而進行限制。由此表明,我國既有條款中對政治性有害信息的劃分邊界還不夠清晰,在實踐中更加容易使法律適用產生爭議并增加法律解釋的隨意性。第三,從現有規定中難以區分有害信息、不良信息和垃圾信息的差異及規制區別。我國現行法規中并沒有對上述概念做出明確界定,從文意上看,幾類信息的范圍極易有重合之處,且不良信息和垃圾信息在某一層面上都有可能是合法的信息,但因其存在某些迫害或有害性從而成為網絡安全需規制的對象。據此,只有清晰界定上述幾類信息的概念邊緣,才能準確制定其相應規制辦法。
(三)網絡有害信息判定向度及達成路徑
有害信息判定的不全面、不準確,不僅會導致相關治理規則的不科學、不完備,更會使網絡表達自由難以得到良好保障。因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對既有規范文本的用語進行再規范,對判定范圍進行統一解釋。現行的法律規范中,對網絡有害信息的規定多以法規、規章和政策性文件居多,但彼此間的法律用語并不能達到統一。這就容易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產生相關條款的解釋口徑不同、條款解釋空間過大等弊端。所以,相關部門應當修訂并整合已有的法律、法規、規章,并統一做出相應的解釋。第二,對政治性有害信息的判定從嚴解釋,為網絡言論自由松綁。在制度上,相關法律規范對政治性有害信息的限制條款遠多于對社會性有害信息的限制。在實踐中,對政治性言論的管制也遠多于對網民網絡言論中私權的保護。建議重新考量政治意見、政治評論等信息的內涵及法律邊界,從而為民眾的自由言論松綁。第三,發布指導案例和參考案例,以補充成文立法的不足。隨著網絡信息的不斷繁復,成文立法總是很難完全覆蓋實踐中的爭議問題,因此應當不斷對典型個案的處理方式加以整合與總結,形成指導案例和參考案例并發布,執法部門及時學習并靈活運用于實際操作,促進執法的公平公正。
三、網絡有害信息治理的反思與建議
目前,我國在網絡的信息治理上已取得初步成效,但隨著網絡信息傳播的方式及途徑不斷發生變化,伴隨而來的更多問題也亟待解決。
(一)當前網絡有害信息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法律規制的角度上看,現有法律依據供給不足且執法主體分散。目前,我國既有的涉及到網絡有害信息治理的規定多是法規、規章以及政策性文件,這些法規、規章來自于與之相關的不同部門,規制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其弊端就是,在部門立法的過程中會追求權力的最大化,把部門利益以法制的方式固定下來,最終導致不同規定之間條款產生矛盾,行政權力沖突,法律難以適用。從整個互聯網行業來看,還未能形成良好的行業自律。結合目前實踐中的情況,有些服務商為了實現經濟效益不惜成為網絡有害信息的滋生土壤,傳播低俗信息、制造謠言甚至侵害他人隱私;也有些服務商雇傭“網絡水軍”來惡意炒作,或是參與非法公關進行有償刪帖等活動。在行業中大量服務商忽略了自身的主體責任,在自我監管上力有不逮。
(二)網絡有害信息治理的規制思路
互聯網治理是一個長期又艱難的過程,欲從根本上治理網絡有害信息的傳播,需從法律層面、監管主體層面、行業自治層面以及網民大眾層面共同考慮、多方發力,才能取得成效。因此,筆者從三個層面提出以下建議。法律上要完善體系,促進現行法規之間的銜接與統一。目前,我國針對互聯網環境治理的基礎性法律只有2017年開始實施的《網絡安全法》,因其屬于框架性立法,故需要處理好其與相關法律性文件的銜接問題。一方面《網絡安全法》中有關信息安全的條款的實施需要援引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另一方面在網絡信息安全規則上,《網絡安全法》需要和《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做好銜接。行政管理上,需明確監管部門的責任劃分,規范其監管模式。我國互聯網治理的責任主體和監管部門并不唯一,主要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信息產業部、文化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安部等。因此要明晰管理部門的權責,避免在互聯網監管和治理上出現矛盾、重復處罰或治理空白等現象。部門之間要加強協作與信息共享,完善工作銜接與協調,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有效地進行互聯網的監管和治理。監管部門還要積極發揮引導作用,發揮預防職能,積極與服務商展開合作監督治理,與網民展開交流、聽取建議。行業本身要增強自律能力,發揮公眾力量。要明確服務商作為責任主體的具體權責,制定自身的監管規則和處理標準,對有害信息的發現、識別、查處等形成完整又嚴謹的操作流程,使其在本身的監管上高效且規范。此外,也不應忽視網民群眾的力量,鼓勵網民之間相互監督,增強網民在網絡空間傳播信息的規范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從源頭杜絕有害信息的傳播。
當前,互聯網的發展正朝著更加繁復多樣的方向演進,人們的生活會因為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而變得豐富多彩,但同時也會因此而面臨更多負面信息的侵害。網絡有害信息的治理必然是一個復雜又長期的過程,需要法律保障、技術保障,更需要市場監督、社會監督。只有多方發力、多措并舉,才能構建和諧、文明、安全的網絡環境,使互聯網更好地服務于我們的生活。
1.張新寶,林鐘千.互聯網有害信息的依法綜合治理[J].現代法學,2015(02):53-66.
2.尹建國.我國網絡信息的政府治理機制研究[J].中國法學,2015(01):134-151.
3.尹建國.我國網絡有害信息的范圍判定[J].政治與法律,2015(01):102-113.
4.尹建國.政府與網絡新媒體相互關系的反思與重構[J].科技與法律,2013(03):26-30.
5.鐘瑛,劉海貴.網絡有害信息管理中的沖突與困境[J].國際新聞界,2004(04):44-48.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