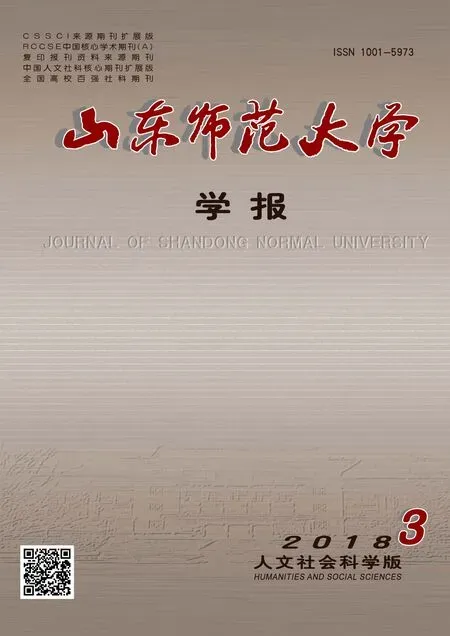徐福與海上絲綢之路考辨*①
張 煒 祁 山
( 1.山東省作家協會,山東 濟南,250002;2.魯東大學 膠東文化研究院,山東 煙臺,264025 )
秦代方士徐福(徐巿)東渡,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外文化交流。徐福率領著包括各種工匠在內的大批人員,給處于原始生活狀態的朝鮮和日本列島帶去了造船航海、銅鐵冶煉、絲綢織染等先進技術,以及先進的耕作方式與文明的生活習俗等。徐福東渡不僅使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質的飛躍,推動了當地各方面的文化進步,也拓展和繁榮了中韓日海上絲綢之路。
開展徐福東渡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不僅可以還原《史記》記載的徐福兩次大規模東渡的歷史真相,也會進一步確立徐福東渡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和影響,促進中日韓文化交流,增進中日韓民間的傳統友誼。
一、徐福東渡航線考辨
徐福東渡起航的地點及開始的一段航程,《史記》記載甚詳,但后一段航程和目的地,因《史記》未予交待,給后世史學留下一宗懸案。
(一)《史記》關于徐福東渡的記載
有關“徐福東渡”的原始史料,主要來自《史記》。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42-247頁。
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山東半島,從嶧山來到“瑯琊”,即今青島市所轄黃島區瑯琊鎮沿海一帶。秦始皇在此羈留三月,筑瑯琊臺,并命李斯刻石銘文。齊地方士徐福上書秦始皇,稱海中有三座神山,山上住著仙人,特請命到海里尋仙。秦始皇遂令徐福帶領“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徐福究竟是確信海上有仙山、仙人,還是以此欺騙秦始皇,《史記》沒有明示。但徐福作為一名方士,又是生活在山東半島的齊人,應該非常熟悉當地沿海一帶關于仙山、仙人的傳說,所以能夠利用自己掌握的方術道行說服秦始皇,令其信以為真。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可以肯定徐福首次東渡的起航地為青島瑯琊。但這次起航后究竟駛向何方,卻未明其詳。不過再次敘及徐福第二次東渡時,則交代了自瑯琊起航后的走向: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并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愿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駑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并海西。*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0-263頁。
徐福首次“入海求仙人”九年之后,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東巡來到瑯琊。徐福到海中尋找仙山、仙人和仙藥,多年無果,且耗費大量錢財。因害怕秦始皇追責,徐福便謊稱海里有蓬萊仙藥,但有大鮫魚阻擋,無法到達海中仙山。恰巧秦始皇夢與海神交戰,占夢博士也建議除掉化作大魚的惡神。于是,秦始皇就命人攜帶捕捉大魚的器具,親自率領弓弩手去射殺大魚。一行人從瑯琊出發,向北到達榮成山,即今威海市所轄榮成市成山頭沿海一帶,未見大魚蹤影。又從榮成山西行至“之罘”,即今煙臺市芝罘區芝罘島沿海一帶,則真的遇到“巨魚”,并射死了一條。接著秦始皇和徐福一行又沿海岸西行。
關于徐福第二次東渡“入海求仙人”,《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另有記載: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谷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086頁。
這里徐福用來搪塞秦始皇的“偽辭”,與《史記·秦始皇本紀》有所不同,也沒有交代其東渡路線,卻透露了第二次東渡的兩個重要信息:一是徐福帶走了三千童男女和各類工匠,還有五谷雜糧的種子;二是徐福在海外找到一片“平原廣澤”,在那里稱王,再也沒有回來。雖然沒有說明徐福找到的“平原廣澤”在什么地方,但可以確定的是,徐福一行到了海外,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太史公司馬遷是嚴謹的史學家。既然他多次提到徐福“入海求仙人”,我們就應當重視《史記》里的相關記載,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
關于徐福兩次東渡共帶走多少人,學界沒有定論。從《史記》可知,第一次帶走“童男童女數千人”,第二次帶走“男女三千人”和“種種百工”。有學者據此認為:“《史記》中記載徐福的兩次出海,每次出海的人數應有上萬人。古代出海,船的動力靠人工搖櫓,遠航需要的水手還會更多,從日本遣唐使船我們可以了解到,水手和勤雜人員能占到總人數的一半多,……除水手和勤雜人員外,管理和看護數千童男童女的官員和隨從人員也不會是小數目。徐福東渡遠航,沿途要停靠許多地方,保衛數千人安全所需的士兵數量也不會太少。”*劉鳳鳴:《山東半島與古代中韓關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73頁。
徐福東渡,“每次出海的人數應有上萬人”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徐福一行遠航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在海上航行的時間較長,隨船帶的糧食等補給也要充分。補給越多需要的船只就越多,所需水手和勤雜人員也要隨之增加。徐福第二次東渡,明確記載了童男童女“三千人”,還有各種工匠。雖說“種種百工”,不一定是百種工匠,但工匠的種類肯定應有盡有。下面將會提到,徐福東渡將鐵器制造、高檔絲綢織造、印染等先進技術帶到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在那個年代,僅一件鐵器的完成,從采礦、冶煉到成品的制造,都需要多道工序、很多人手來實現。徐福集團在朝鮮半島東南部建成了鐵器制造基地,出產的鐵器銷往周邊地區,包括越海銷往日本,這都不是少量人員能夠完成的。
(二)芝罘以西航線的考辨
徐福東渡,從今青島瑯琊沿海一帶出發,沿海岸線北上,到了今山東半島最東端的榮成市成山頭沿海一帶,再繞過成山頭西行至今煙臺市芝罘島沿海一帶。這一段航線,《史記》記載得很清楚。但其后“遂并海西”,沿海岸線繼續向西到哪里,則沒有記載。
徐福的船隊,肯定是要離開海岸線進入大洋的。這是因為他要向秦始皇履行諾言,就必須駛向經常出現仙山的大海。芝罘島以西的大海之中,哪里經常出現仙山呢?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名曰蓬萊、方丈、瀛洲”的“三神山”,在《史記·封禪書》中另有這樣的描述: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69-1370頁。
這說明,在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時期,就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說,他們還曾派人到勃(渤)海去尋找過三座神山。但海中的“三神仙”看似不遠,然而當船只快要靠近時,神山卻被大風吹到遠處。遠遠望去,“三神山”就像在一片云霧之中,可是一到跟前,就馬上消失了。這一景象,顯然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海市蜃景。而芝罘島以西的渤海中出現海市蜃景最多的地方,就是現今煙臺市所轄蓬萊市以北,廟島群島周邊海面。這也是當年漢武帝派人尋找仙山的海域,蓬萊縣(今蓬萊市)、蓬萊閣等名字由來,就是因當年漢孝武帝東巡此地,“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76頁。,在此瞭望“蓬萊”仙山而得名。
既然徐福奉命到海中去“求神異物”,他率領的船隊就必然朝著“三神山”的隱現之地,即海市蜃景多發的海域駛去。更何況徐福第二次東渡,還有秦始皇率領的弓弩手和大批船隊也一并來到今蓬萊市沿海一帶,徐福要自圓其說,不在秦始皇面前露出破綻,只能假戲真做,向子虛烏有的海中仙山進發。秦始皇應是在蓬萊一帶海域與徐福告別,并且目送其船隊向廟島群島海域駛去。
那么,徐福的船隊進入茫茫大海之后,會再駛向何方呢?
顯然,徐福第二次東渡時,已經意識到不可能找到仙山、仙藥了。第一次“入海求仙人”,有可能真的相信海里有仙山、仙藥,但尋找了多年,并未如愿以償。第二次見秦始皇時,只好用謊言瞞天過海,所以再一次“入海求仙人”,顯然明知沒辦法回來交差,只能逃到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擺脫秦皇帝的統治。可見,徐福第二次東渡既是為了逃避罪責,也是為了去海外拓殖,否則,就很難理解他為什么要帶領那么多的童男童女、各類工匠和五谷種子等,甚至連善射的兵員都準備得非常充分,這一切,正是開拓新的疆土所必需的。
徐福的船隊進入廟島群島海域后,最近的登陸地是遼東半島,但徐福一行不可能在遼東半島登陸,因當時這里已在秦的統治之下。秦朝遼東郡的轄區,東至今朝鮮半島以西朝鮮灣沿海一帶。也就是說,徐福的船隊至遼東半島近海后,只能“循海岸水行”*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4頁。,行駛至朝鮮半島北部沿海一帶也不敢停下來,只有繼續沿海岸線南下。
下面我們會提到,徐福的船隊到達朝鮮半島南部,包括濟州島,后來有部分人員又從朝鮮半島南部輾轉到達日本九州島,再進入日本本州島等。這樣一條航線,就是《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的“循海岸水行”航線:沿朝鮮半島北部西海岸南下,“歷韓國”,即現在的韓國西部地區。再“乍南乍東”到達朝鮮半島南部,沿海岸線向東,“始渡一海”,過“對馬國”,即今日本對馬島。再過“一大國”,即今日本的壹岐島。“又渡一海”,登陸“末盧國”,今日本九州島佐賀一帶。從末盧國到“伊都國”,今日本九州島福岡一帶。再經過幾個小國后,進入日本本州島,到達倭國“女王之所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還記載說:“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4頁。說明自漢代以來,這樣一條“循海岸水行”的航線,就是當時中韓日官方往來的主要通道。
雖然《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只記載了從朝鮮半島北部到日本這一段航程,沒有提到從山東半島到朝鮮半島這一段的航路,但《新唐書·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非常具體地記載了這一段路線,即“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 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47頁。“登州”,指當時的登州駐地,今煙臺市所轄蓬萊市。“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分別是今長島縣所轄的長山島、大欽島、小欽島、南隍城島、北隍城島,均屬廟島群島中的島嶼。“烏湖海”,指今大連老鐵山海峽。“都里鎮”,在今大連旅順一帶。“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均系遼東沿海一代的港灣。“烏骨江”,指今鴨綠江入海口。“烏牧島”,今朝鮮身彌島。“貝江口”,今朝鮮大同江口。《舊唐書·志第十八·地理一》記載的這一段航線,即從登州出發,沿廟島群島的島嶼北上至遼東半島今大連附近的海岸,然后仍是“循海岸水行”至朝鮮半島。這說明,即使到了唐代,中韓間海上往來仍然要經廟島群島,然后“循海岸水行”。
這條航線是否由徐福船隊開辟,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徐福船隊走的也是這條航線。當時遠海航行的導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目視,船的動力也只能靠海風吹送或人力搖櫓。秦代的航海條件,只能是“循海岸水行”。沿海岸線航行不僅可以及時補充淡水和給養,而且一旦遇上風浪和惡劣天氣還可以及時靠岸躲避,船只受損也可以及時靠岸維修。不用說秦代,即使到了唐初,當時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水平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中韓日之間的海上官方往來也仍然要經廟島群島。日本的遣隋使和唐初的遣唐使走的就是這條航道,后期的日本遣唐使開始橫渡黃海直通揚州,是因為當時日本和朝鮮半島的新羅關系緊張,不得不走南路直通揚州,但這是“一條最危險,遇難率極高的航路”*[日本]藤家禮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俊彥、卞立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99頁。。所以,后期的遣唐使有時也走“循海岸水行”的古航道,如第12次遣唐使即從“登州登陸”,第18次遣唐使“曾在今乳山、文登、榮成海岸停泊數日”*楊蔭樓、王洪軍:《齊魯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26、527頁。。所以說,徐福東渡的航線只能是《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的“循海岸水行”的航路。實際上這條海上航線,即使到了明代,造船技術和航海水平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后,中朝(韓)官方海上往來走的也是經廟島群島然后“循海岸水行”的航路。這在中韓史料中都有具體記載。因為這是一條最安全的航道,更何況秦代徐福東渡,以當時的航海條件,又帶領著大批人員和輜重,包括“五谷種種百工”設施等,必須選擇一條在當時認為最安全的航道,這就是《舊唐書·志第十八·地理一》和《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的中韓日海上航線。
由上得出結論,徐福一行在芝罘島射殺大魚之后,“遂并海西”,到了今蓬萊市一帶海域后,便向北行駛,沿廟島群島諸島嶼,到達遼東半島今大連一帶海域,然后,沿海岸線向東北駛向朝鮮半島,到達鴨綠江口海域后,再沿海岸線南下至朝鮮半島南部,又從朝鮮半島東南部借助巨濟島、對馬島、壹岐島等島嶼,渡過朝鮮海峽進入日本。
二、徐福東渡目的地考辨
徐福東渡的目的地是哪里?《史記》沒有記載,但從后來的史書,包括其他一些相關記載和考古成果分析,徐福東渡的目的地首先是朝鮮半島東南部,即今韓國東部一帶,并有大批人員在此定居下來。然后,徐福集團的部分人,或是第二次東渡的部分人員,進入了日本的九州島,并在那里定居下來。之后,又有部分人員進入了日本本州島、四國島。
(一)徐福東渡目的地的史料記載
記載徐福東渡目的地的最早史料是《后漢書·東夷列傳》和《三國志·吳書·孫權傳》,因《三國志》成書早于《后漢書》100多年,兩書的相關記載又基本相同,故這里僅引用《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的記載:
(黃龍)二年(230)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36頁。
以上記載可說明:徐福一行到了“亶洲”;“亶洲”是一個較大的島嶼,上有“數萬家”居住;“亶洲”的人曾到東吳的“會稽貨布”,會稽東縣的人也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會稽”指會稽郡,郡治在今浙江紹興城區;“亶洲”離東吳“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東吳的航船和人員去不了亶洲。當時東吳轄今長江口及以南沿海地區,包括今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吳主孫權派萬人出海都沒找到,或到不了“亶洲”,但“亶洲”的人卻到了東吳會稽郡,今杭州灣一帶,這說明“亶洲”來東吳做生意的人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線。“夷洲”指的是今臺灣島,東吳的船隊有“數千人”到了“夷洲”。比臺灣島更遠且比較大的島嶼,有菲律賓的呂宋島和日本的九州島。菲律賓的呂宋島,三國時期東吳的船隊都無法到達,更何況400多年以前從山東半島起航的徐福船隊呢。日本的九州島,東吳的船隊也不可得至,但徐福的船隊從山東半島起航,“循海岸水行”則能到達。三國時期來東吳做生意的“亶洲”人走的也應是徐福一行“循海岸水行”的航線。所以說,“亶洲”指的應是日本九州島。唐代詩人皮日休在《重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一詩中寫道:“云濤萬里最東頭,射馬臺深玉署秋。無限屬城為裸國,幾多分界是亶州。”*《全唐詩》卷六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091頁。這里的“射馬臺”“裸國”“亶州”,均指日本。“射馬臺”應為“邪馬臺”,《后漢書·東夷列傳》記載:“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裸國”是“倭種”之一。這說明唐代人也認為,“亶洲”就是日本。從日本到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如果走徐福東渡的“循海岸水行”的航線,以當時的船只和航行條件足可通達,但如果從東南沿海橫渡大海直達日本九州島,其結果只能是“不可得至”。
五代后周時期,濟州開元寺高僧義楚在《義楚六貼》(又名《釋氏六貼》)中也明確提到徐福到了日本:
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又顯德五年,歲在戊午,有日本國傳瑜伽大教弘順大師賜紫寬輔。……又東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聳,頂有火煙。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即卻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釋氏六貼》卷二十一《國城州市部第四十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3頁。
顯然,高僧義楚關于徐福到了日本富士山一帶,其“子孫皆曰秦氏”的記載,其信息是來自日本來華高僧弘順大師。這說明,當時的日本,或者更早時期就有了徐福到了日本的說法。
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在長詩《日本刀歌》中提到,因徐福東渡,日本“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張春林:《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15頁。。這說明徐福東渡日本帶去了“百工五種”,使日本的“器玩皆精巧”,也使中日官方之間“屢往來”,日本“士人”還“工詞藻”,善于做中國傳統的詩文。歐陽修還第一次提到,因徐福東渡帶走了一些春秋戰國時期的著作,這些著作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在中國國內已經失佚了,而在日本得以保存下來。
中國元朝時期,日本官方編纂的《神皇正統記》記載:“(秦)始皇好神仙,求長生不死之藥于日本,日本欲求彼國之五帝三王遺書,始皇乃悉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國因焚書坑儒,孔子之全經遂存于日本。”*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徐福志》第十二章《日本部分史志書籍有關徐福的記載》,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00頁。《神皇正統記》不僅肯定了徐福東渡“求長生不死之藥于日本”,而且提到,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孔子之全經遂存于日本”,這也與歐陽修《日本刀歌》相符。明朝中期1471年,朝鮮王室編纂刊印的《海東諸國紀·日本國紀》也記載:“孝靈天皇七十二年壬午(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紀伊州居焉,在位七十六年,壽百十五。”“崇神天皇……是時熊野權現神始現,徐福死而為神,國人至今祭之。”*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日本國紀·天皇代序》,朝鮮刊本,1471年。主持編纂《海東諸國紀》的,系朝鮮領議政(首相)的申叔舟(1417-1475)。申叔舟曾于1443年奉朝鮮國王之命,以日本通信使書狀官身份出使過日本,《海東諸國紀》中關于《日本國紀》的記載,顯然來自日本的官方資料。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事件進入日本和朝鮮李朝的正史,得到了當時兩國官方的認可,應與日本當時廣泛流行的徐福傳說及許多與徐福有關的遺址和紀念設施有關。
徐福東渡到達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的情況,韓國史料也多有記載。
明朝萬歷年間朝鮮著名理學家李睟光(1563-1623)在他的《芝峰類說》中提到:“世謂三山,乃在我國。以金剛為蓬萊,智異為方丈,漢挐為瀛洲。以杜(甫)詩‘方丈三韓外’證之。余謂三神山之說,出于徐福。而徐福入日本,死而為神。則三山應在東海之東矣。老杜不曰方丈在三韓。而曰‘方丈三韓外’。其言宜可信也。”*李睟光:《芝峯類說》卷二《地理部·山》,朝鮮刊本,1633年。文中“金剛”指金剛山,位于今朝鮮東南部,臨近韓國;“智異”指智異山,在今韓國南部;“漢拿”指漢拿山,在今韓國濟州島;“老杜”指中國唐代詩人杜甫。李睟光在這里提到,朝鮮李朝時期,或在這之前,朝鮮人認為“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就在朝鮮半島,還用杜甫的詩句來論證這一觀點。李睟光不同意這樣的提法,他認為徐福東渡尋找的三神山在日本,杜甫的詩“方丈三韓外”,恰恰說明了三神山在“三韓”之外,即朝鮮半島之外的日本。
李睟光在《芝峰類說》中還提到:“《后漢書》曰:徐福入海,止夷、澶洲。韓文所謂海外夷、亶之州是也。按夷、亶二州名,今倭國南海道,有紀伊州、淡州。淡與亶音相近,疑即夷、澶洲也。”*李睟光:《芝峯類說》卷二《諸國部·外國·日本》,朝鮮刊本,1633年。李睟光用語音相近來說明《后漢書》記載的夷、亶之州指的是日本的“紀伊州、淡州”,再用日本“紀伊州,今有徐福祠”,“熊野山守神者,徐福之神也”及“日本京都,見有徐福祠”,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說明,徐福東渡到朝鮮半島或日本,已為朝鮮許多名家及普通百姓所深信不疑。
朝鮮李朝時期著名哲學家、學術大師李瀷(1681-1763)也曾說過:“濟州,古耽羅國,距陸九百七十余里,周圍四百余里。山頂必凹陷,峰峰皆然。新晴登望申方,天際有山,浙商云:松江府之金山也。……徐福、韓終之入海,雖曰誣辭,其言曰:登之罘山望神山。之罘在東海邊,始皇之登覽者也。登此而望見者,疑若指此而云爾。松江金山在坤申方,則自彼而望此,必在東北矣。島中亦有瀛洲之名,可異。”*李瀷:《星湖先生僿說》卷之一《天地門·濟州》,朝鮮刊本,1760年。韓終亦為秦代方士,秦始皇也曾派他到海上“求仙人不死之藥”。李瀷認為,濟州島可能就是當年秦始皇登臨之罘山遠望的神山“瀛洲”,而濟州島也稱過“瀛洲”。李瀷還提到:“通典云:百濟海中有三島,出黃漆樹,六月取汁,漆器物若黃金。此乃今之黃漆,而惟濟州產此物,則三島者即濟州之稱。又或島中有三座山而云爾也。……既避秦入海,必不舍朝鮮而投倭也。其所謂三山仙藥,特讆言瞞人也。”*李瀷:《星湖先生僿說》卷二十《經史門·徐巿》,朝鮮刊本,1760年。李瀷肯定了徐福一行到過朝鮮半島南部和濟州島一帶,并在這里定居下來。當然,他提到徐福一行“必不舍朝鮮而投倭也”,并不是否認徐福一行去過日本,而是強調他們先到達朝鮮半島南部和濟州島一帶。此外,李瀷還認為,當時朝鮮半島南部的辰韓就是徐福一行建立的。
今韓國境內還曾發現過多處與徐福東渡有關的石刻,如濟州島西歸浦市東烘洞正房瀑布的峭壁上就曾有過“徐巿過之”石刻。“1910年,日本學者冢原熹先生在正房瀑布拍攝的‘徐巿過之’照片與撰寫的《濟州島秦徐福遺跡考》一起被收入《朝鮮志》,現存日本東京大學圖書館。20世紀50年代,遺址便湮沒了。現只保存下來摩崖石刻的拓片。”*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徐福志》第十五章《韓國遺址、遺存與紀念設施》,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60頁。雖然這些石刻的年代還需要進一步考證,但至少說明當地人相信徐福東渡應該到過朝鮮半島南部,包括今韓國濟州島一帶。歷史上曾稱“瀛洲”的濟州島,總面積1826平方公里,在古代容納“數萬家”居民生活是沒有問題的。濟州島自古以來就廣泛流傳著許多徐福尋仙求藥的傳說。濟州島的漢拿山,也稱瀛洲山,海拔1950米,為韓國最高峰,是傳說中徐福尋找的三神山之一。濟州島的西歸浦(今西歸浦市),相傳是徐福第一次東渡到達濟州島尋找長生不老藥,后從濟州島的正房瀑布海岸西行回國,這里因此而得名西歸浦。這一傳說應是由來已久,朝鮮李朝官員任征夏(1687-1730)在他的《濟州雜詩二十首》中就寫道:“徐巿求仙去,應從此島回。老人南極在,童女玉凾來。碧海幾回變,蟠桃猶未開。乙那亦塵土,遺廟至今哀。”*任征夏:《西齋集》卷之二《濟州雜詩二十首·其八》,《韓國文集叢刊·續》(第68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8年,第464頁。這說明在當時不僅有徐福從濟州島回國的傳聞,而且濟州島很早就有供奉徐福的廟宇等,今西歸浦市還建有徐福公園,西歸浦市每年都在徐福公園舉行徐福祭禮活動。
除濟州島外,今韓國的南海郡南海島商洲里錦山海濱的大巖石半山腰,有大型刻石,內容為“徐巿起拜日出”。“(20世紀)80年代中葉,在與此巖刻僅隔一山的一個石洞里,發現了一幅壁面,上畫動物、船只及人物,洞外還刻有腳印……傳說與徐福到此有關。”*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徐福志》第十五章《韓國遺址、遺存與紀念設施》,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20頁。清末朝鮮李朝官員姜獻奎也撰文提到:“以芒鞋竹杖,作南海之游。”“入閑山,……泛龜船凌陽侯,望徐巿題石處。”*姜獻奎:《農廬集》卷之九《鹿門居士傳》,《韓國文集叢刊·續》(第122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11年,第189頁。“閑山”指閑山島,在韓國巨濟島西,也是徐福一行東去日本的必經之地,今屬韓國慶尚南道統營市。“陽侯”是傳說中的水神、波濤之神,這里代指波濤。“泛龜船凌陽侯”即指乘船在海上暢游。這說明,韓國閑山島一代,也遺有與徐福東渡相關的刻石。這些刻石和壁畫,無論是徐福當年所留,還是后人所為,至少可以說明徐福一行,或他們的后人到過這里。
(二)明清時期赴日朝鮮官員的相關記載
明清時期,有不少朝鮮李朝的官員因各種原因到過日本,記載了日本有關徐福的一些紀念設施和傳說。
明朝萬歷年間,朝鮮官員姜沆(1567-1618,字太初,號睡隱)在日軍侵略朝鮮時被俘掠往日本。在日3年期間,他將日本的國情、國土特征及所見所聞記錄了下來,結集為《姜睡隱看羊錄》。其中《倭國八道六十六州圖》提到:“秦始皇時,徐福載童男女入海,至倭紀伊州熊野山,止焉。熊野山尚有徐福祠。其子孫今為秦氏,世稱徐福之后。今為倭皇則非也。洪武中,倭僧津絕海,入貢中原。太祖命賦詩,詩曰:‘熊野山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余肥。至今海上波濤穩,直待好風須早歸。’太祖賜和章曰:‘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昔時徐福浮舟去,直至于今猶未歸。’”*姜沆:《姜睡隱看羊錄》,《倭國八道六十六州圖》,朝鮮刊本,1656年。文中“太祖”,指明太祖朱元璋。這里提到的日本僧人“津絕海”,也稱絕海中津,于明初洪武元年(1368)來到中國,洪武九年(1376)春覲見明太祖朱元璋。這說明,日本熊野山前的“徐福祠”,至少在元代或之前就有了。朝鮮李朝晚期著名政治家、歷史學家安鼎福因此也深信徐福到了日本:“姜沆《看羊錄》云:徐福入倭伊紀州熊野山止焉,今有祠,子孫為秦氏。據此則(徐)福之入日本信矣。其稱秦氏,猶辰韓之稱秦韓,蓋以自秦而來也。”*安鼎福:《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書東史問答》,《韓國文集叢刊》(第229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年,第545頁。
和姜沆有著相同經歷的朝鮮官員魯認(1566-1622,字公識,號錦溪),在1597年日軍再次大規模入侵朝鮮時,被俘押送到日本。后來在明朝官員的協助下,于1599年3月逃到福建閩南,年底回到朝鮮。魯認有《錦溪集》傳世,記載了他在日本的一些經歷,其中卷之六《倭俗錄》提到了在日本的一些見聞,有關徐福的內容同前面姜沆記載的完全一樣,也提到了日本僧人與明太祖朱元璋詩歌唱和之事。*魯認:《錦溪集》卷之六《倭俗錄》,《韓國文集叢刊》(第71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年,第233頁。這說明,二人的信息來源是一致的,同時也進一步說明,日本熊野山的“徐福祠”,應是在元代或之前就有了,明萬歷年間仍有日本人自稱是徐福的后人。
前文提到的朝鮮李朝著名理學家李睟光在其文集中記載:“趙生完璧者,晉州士人也。弱冠,值丁酉倭變,被擄入日本京都。……在日本時,見京都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李睟光:《芝峰先生集》卷之二十三《雜著·趙完璧傳》,《韓國文集叢刊》(第66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年,第252頁。“丁酉倭變”,指萬歷二十五年(1597),日軍大規模地入侵朝鮮。可見,明代萬歷年間的日本京都也有“徐福祠”。
萬歷三十五年(1607),出使日本的朝鮮官員慶暹(1562-1620)也記載:“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藥。徐福至紀伊州,居一百八十九年而死。國人為之立祠,至今祭之云。”*慶暹:《慶七松海槎錄》《七月十七日》,朝鮮刊本,1607年。雖然徐福在日本活了189年的說法過于夸張,但他被日本人“為之立祠,至今祭之”,應為可靠記載。
明末天啟甲子年(1624),朝鮮赴日本回答使副使姜弘重(1577-?)在日本期間,曾向負責接待的日本官員詢問:“徐福祠在何處?”日本官員回答說:“在南海道紀伊州熊野山下,居人至今崇奉,不絕香火。其子孫亦在其地,皆稱秦氏云。熊野山一名金峰山云。”*姜弘重:《東槎錄》,朝鮮刊本,1624年。
朝鮮孝宗大王六年乙未(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出使日本的朝鮮官員南龍翼(1628-1692)在《扶桑日錄》中記載:“熊野在(大坂)南四十里,即紀伊州之地。而徐福到此山居焉,山下有墓,子孫皆姓秦氏。”*南龍翼:《扶桑日錄·九月初五日》,朝鮮刊本,1655年。這說明居住在熊野山一帶的日本人皆以秦為姓,自稱是徐福的后裔,祖祖輩輩都供奉徐福。我們雖然不足以考證他們與徐福是否有血緣關系,但這樣的風俗信仰代代相傳,也不可否定他們與徐福的關系。
除日本九州島、本州島等地外,徐福東渡路經的日本對馬島也有徐福的傳說,這在赴日的朝鮮官員筆下也有反映。
明代萬歷申丙年(1596)秋,朝鮮通信使一行出使日本,正使黃慎(1560-1619)在《日本往還日記》中寫道:“八月初八日,……夕抵對馬島之西浦。……浦中人居不甚多,泊船處稍平闊。正使昏乘轎登徐福寺而宿。同寺俯臨大洋,累石為磴,以板為屋,居僧僅數十人。”*黃慎:《日本往還日記·八月初八日》,朝鮮刊本,1596年。可見,當時的對馬島有“徐福寺”,黃慎說廟里“居僧僅數十人”,顯然太少了。在他看來,作為徐福東渡日本必經之路的對馬島,“徐福寺”的僧人理應更多些。
明代崇禎癸未年(1643)春,朝鮮通信使一行出使日本,五月初路經對馬島時,朝鮮官員趙絅(1586-1669)在《東槎錄》中記載對馬島地方風俗時提到:“采藥稱徐福,描鷹說宋宗。”*趙絅:《龍洲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三《東槎錄》,《韓國文集叢刊》(第90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2年,第424頁。亦可證明徐福在對馬島采仙藥的故事曾在當地廣為流傳。
清初,朝鮮官員、著名學者、世子師魚有鳳(1672-1744)在送友人出使日本時贈詩曰:“送君天外去,極目海茫茫。國是秦徐福,舟同漢博望。”*魚有鳳:《杞園集》卷之四 《送李美伯邦彥奉使日域》,《韓國文集叢刊》(第183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89年,第451頁。魚有鳳認為,秦代的徐福東渡不僅到了日本,而且日本國也是徐福建立起來的。朝鮮官員、著名學者李德懋(1741-1793),未去過日本,他依據其他朝鮮官員從日本帶回的史料及其他資料,撰寫了《蜻蛉國志》,即《日本國志》。其中《神佛》一節有這樣的記載:“紀伊州,有高野山,一名熊野山。傳言孝靈時,秦人徐巿,與其子福,乘舟,至紀伊州止焉。國人尊敬之。巿,尋死。福年一百八十而死,多靈異。國人立祠于高野山中,為權現守神。或稱福,即巿之改名。或稱巿之字,又稱福之孫。”*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四《蜻蛉國志·神佛》,《韓國文集叢刊》(第259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第166頁。李德懋記載的日本傳言,把“徐巿”“徐福”混為父子二人,或是不了解“徐巿”與“徐福”只是寫法不同而已。不過由此足以證實,直至清朝乾隆年間,日本仍將“徐福”作為神靈供奉,“立祠于高野山中”,也說明徐福東渡的影響,至少是有史料記載以來,上千年一直不曾斷絕。
中國清朝時期,還有許多出使日本的朝鮮官員有過關于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記載,茲不一一引述。
實際上,日本至今有許多關于徐福的傳說,“不但有登陸的地點,還有登陸之后教導土著人民耕種、捕鯨的事。在傳說他們一行登陸地的紀伊熊野浦(現和歌山縣新宮市),還有徐福和他親信的墓,旁邊更立有徐福祠,專門祭祀他們,完全象若有其事一般”*汪向榮:《古代中日關系史話》,北京:時事出版社,1986年,第53頁。。雖然這些紀念設施和傳說都難以直接證明徐福到了日本,但日本對徐福的信仰及相關風俗確乎長期傳承,歷一兩千年而經久不衰,甚至不少日本人至今仍承認自己的家族來自于徐福或徐福的部屬,如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移民的后裔,并多次到中國來尋根問祖。羽田孜曾說過:“我的祖上是姓秦的。我們的身上有徐福的遺傳因子,在我的老家還有‘秦陽館’,作為徐福的后代,我們感到驕傲。”他還說過:“凡是與中國沾邊的事,我都高興去做。有關徐福的活動,我都要爭取參加。”*環球網快訊:《日本前首相羽田孜逝世 認為自己是中國移民后裔》,環球網國際新聞2017年8月28日。這至少可以說明,徐福集團的一部分人到達了日本,并對日本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日本民眾紀念徐福的活動,也反映出他們渴望繼續保持中日友好傳統的強烈愿望。
三、徐福東渡與中日韓海上絲綢之路
徐福東渡,雖說最初的動機是為了到海上尋找仙山、仙藥,但徐福的第二次東渡,帶領“男女三千人,資之五谷種種百工而行”,實際上是假借“入海求仙人”到海外拓殖,開創新的疆域。綜合史料記載和考古發現,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徐福東渡,是中國文化——特別是齊魯文化向海外的一次大傳播,是中日韓第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在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列島還處于原始社會時期,秦人徐福帶領的龐大船隊,沿途傳播的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這無疑繁榮了中日韓海上絲綢之路,也為漢代更大規模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拓寬了航路。
(一)辰韓應是徐福集團創立的
中國秦朝時期,朝鮮半島南部——今韓國所轄區域——分屬三韓:馬韓、弁韓、辰韓。馬韓居住在今韓國西部,屬當地土著。辰韓,居住在今韓國東部,由“避秦役”的秦人組成,因而也稱“秦韓”*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2頁。。弁韓在馬韓、辰韓之間,由土著人、辰韓人混合而成。有關朝鮮半島三韓的史料記載,主要來自《后漢書·東夷列傳》和《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二者所述基本相同。這里僅引述成書較早的《三國志》。
當時的馬韓還處在原始生活狀態,如:“其俗少綱紀……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槨無棺,不知乘牛馬,牛馬盡于送死。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懸)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1頁。馬韓人居住在半地下房屋里,不會使用牛、馬,牛、馬只能宰殺食用,不知道金銀珠寶和絲綢的珍貴,也沒有中國人所尊奉的“長幼男女之別”等禮儀習俗。這說明,馬韓土著無論是生產力水平,還是社會關系,都與中國的原始社會相似。
而由“避秦役”的秦人組成的辰韓,其生產力水平和生活習俗則與秦漢時期的山東半島無異。辰韓“宜種五谷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3頁。
辰韓(秦韓)應是形成于中國的秦朝時期,辰韓“名國為邦”*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2頁。就是有力證據。漢朝的開國皇帝是漢高祖劉邦,為了避諱,漢代人是絕不能講“邦”的,這說明辰韓至晚在秦末就已經形成了。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2頁。,說明辰韓擴充為“十二國”,或十二個部落,是在辰韓創立不久就完成了,也應是由“避秦役”的秦人組成的。韓國的考古成果已經證實,三韓時期朝鮮半島南部“避秦役”的秦人主要是來自山東半島的原齊國人。北京大學教授、中韓古代關系史學家楊通方在《中韓古代關系史論》也寫道:“三韓從新石器時代直接進入鐵器時代,與中國山東省形制相同的、棋盤式的支石墓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遺物。”*楊通方:《中韓古代關系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6頁。秦國于公元前221年滅齊,到公元前207年秦就滅亡了,也就是說,秦朝在山東半島統治時間只有十多年,辰韓“十二國”的形成,也應是在這一時間段完成的。在這樣短的時間里,能迅速擴張,應是徐福第二次東渡的結果。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也說明徐福找到了可以落腳和發展的居留之地。雖說辰韓居民不一定都是徐福東渡時帶去的人員,但以徐福隨員為核心,再團結聚集其他“避秦役”的散兵流民,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王國是完全可能的。
徐福集團建立辰韓這一觀點,朝鮮李朝時期著名哲學家、文人李瀷曾有論述:“按東史辰韓者,秦之避亂者。……齊民流移之徒,豈有越萬里度夷貊得至東國之理,又豈有過遼沈四郡之墟而窮到我東南之一角耶,想其勢非浮海則不能達也。關中之于東海,既東西厓角,秦人而浮海非流民所辦,必將頼國之資送者也。當其時徐巿(福)浮海而東邦,果有自秦來泊者,辰韓之為徐巿(福)國可知。”*李瀷:《星湖先生僿說》卷二十《經史門·徐巿》,朝鮮刊本,1760年。“夷貊”,指北方的少數民族,這里指中國北方地區。“東國”,本指當時的朝鮮,這里指朝鮮半島南部地區。李瀷認為,由“秦之避亂者”建立的辰韓,是“齊民流移之徒”越海到這里建立起來的,“非浮海則不能達也”。具體說,辰韓是徐福一行東渡到這里建立的,而非秦人中浮海的“流民所辦”。當時秦人中的“流民”是沒有能力建立辰韓的,建立辰韓必須是“賴國之資送者也”,則唯有徐福一行能夠做到這一點。
清初,朝鮮王室重臣權相一(1679-1759)也提到:“我國(指朝鮮)名山,以金剛為第一,則蓬萊之稱,舍此山不可得也。徐巿為避秦計,以神山采藥之說,欺弄始皇,其所止泊處,不可詳知。……秦人之為辰韓似分明,秦時有浮宅之民,若青齊等地,不堪役煩。浮海而來,接于我國東南,勢或有之也。”*[日本]權相一:《清臺先生文集》卷之六《答李子新甲子》,《韓國文集叢刊·續》(第61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2008年,第327頁。“浮宅”,浮在水面的房屋,指船。“青齊”,指山東半島。山東半島,夏代屬青州,春秋戰國時屬齊國。權相一也認為,徐福一行應是乘船來到了朝鮮的東南部,當年的辰韓應是徐福一行建立的。
1905年,日本學者淺見倫太郎來到朝鮮半島,考察了徐福東渡至朝鮮半島南部的遺跡,在談到當年辰韓作為“秦國亡命人”建立的國家時也提到:“徐福帶領童男童女渡海,……數千童男童女流亡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徐福志》第十三章《韓國部分史籍有關徐福的記載》,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20頁。他也認為辰韓是由徐福帶領童男童女建立的。
在朝鮮李朝之前的高麗時期,身居高麗王室要職的李谷(1298-1351),在談到朝鮮半島東南部東萊府時提到,這里是“徐福尋仙處,新羅入貢余”*李谷:《稼亭先生文集》卷之十七《鄭仲孚示予去年蔚州所作東萊十首次其韻》,《韓國文集叢刊》(第3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第206頁。。“新羅”,其前身就是辰韓。唐高宗時,新羅在唐軍的支援下統一了朝鮮半島。李谷認為,朝鮮半島東南部的辰韓就是徐福當年尋仙落腳的地方,后來新羅人之所以頻繁地向唐王朝進貢,即因辰韓乃中國人徐福所建。從西漢至唐高宗時期,山東半島東部一直屬東萊郡管轄,包括傳說是徐福故鄉的徐鄉縣都在東萊郡管轄之下。朝鮮半島的東萊府顯然與山東半島的東萊郡有著某種淵源,至于是否與徐福東渡有關,尚待考究。
辰韓不僅熟練掌握冶鐵和鐵器制造等先進技術,而且能夠大量生產。周邊的國家,包括西邊的馬韓、弁韓,朝鮮半島北部的濊貉,甚至漢初漢朝管轄的樂浪郡、帶方郡,及與辰韓隔海相望的日本,對鐵的需求皆有賴于辰韓。辰韓人還能生產高檔絲綢“縑布”。“縑布”,東漢劉熙的《釋名》解釋說:“縑,兼也,其絲細致,數兼于絹,染兼五色,細致,不漏水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49頁。中國的漢代、魏晉時期,縑布一直是作為貴重物品甚至以之取代貨幣。晉建國之初,“泰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壊,市易又難”*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26頁。。辰韓“嫁娶禮俗,男女有別”,“行者相逢,皆住讓路”*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3頁。,也都是齊魯禮儀之邦的文化習俗。顯然,辰韓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不僅影響了朝鮮半島南部,對秦末漢初的朝鮮半島北部以及日本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紡織業非常發達,《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齊冠帶衣履天下”。當時各國貴族及上層人士頭上戴的,身上穿的,包括腳上的鞋子,所用的高檔絲綢都來自山東半島的齊國。齊國的絲綢也是當時出口周邊諸侯國,包括海外國家的主要貨源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冶煉業和銅、鐵器生產同樣非常發達。《管子·海王篇》說,“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55頁。。說明當時銅、鐵器具已在齊國得到廣泛使用。解放后出土的齊叔夷鐘有銘文曰:“余命汝司予萊,陶鐵徒四千。”*李英森、王秀珠、程剛:《齊國經濟史》,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410頁。因叔夷滅萊國有功,齊靈公命叔夷管理萊國并賞給叔夷四千冶鐵工人。齊靈公賞給叔夷“陶鐵徒四千”,可見當時齊國冶鐵規模很大。
徐福乃齊人,必然熟悉家鄉的鐵器制造、高檔絲綢織造等情況,東渡時除了帶領掌握鐵器制造、高檔絲綢制造的“百工”,也少不了要帶上相關的生產工具,甚至部分原材料等。
辰韓能組織起大規模的冶鐵生產,出產高檔絲綢,如果沒有相應的原材料和先進的生產工具、生產工藝是不可能的。僅靠“避秦役”的散兵流民,難以在短時間內形成大規模的生產活動,而徐福東渡帶領大批人員及“五谷種種百工”,不僅有擅長各種工藝的工匠,還有各種生產設施,憑借雄厚的人力物力,即可在較短的時間里組織起有效的冶鐵、絲綢生產。同時辰韓的生活習俗也并非本土原生,而是徐福治下的民眾,遵循沿襲了母國傳統的結果。
辰韓所在地域本來屬于馬韓,“避秦役”的秦人來到朝鮮半島南部,“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2頁。。這可說明兩點:其一,來到朝鮮半島南部“避秦役”的秦人,不會是零散的潰兵流民,而是比較集中的有組織有首領的大批人員,否則,馬韓不會割讓那樣一大片土地讓他們居住,使其成為獨立的國家。而見于史料記載的,秦代唯有徐福一行大規模東渡,這也可以旁證,由“避秦役”的秦人形成的辰韓,就是徐福集團建立的。而其他零散的“避秦役”的秦人,應主要居住在弁韓,這里原來就有當地土著人居住,故而形成土著人和秦人雜居的地區。其二,徐福一行在朝鮮半島東南部,今韓國東部一帶建立自己的國家或部落,其土地不是靠侵略得來的,而是和當地土著人友好相處的結果。雖然,徐福東渡也有較強大的兵力相隨,建立的辰韓一開始就有著先進的文化和生產力,但自始至終尊重馬韓當地土著人,并擁戴馬韓人做自己的領袖,“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53頁。。“辰王不得自立為王”,也有可能是馬韓當時讓秦人大規模居住在自己地盤的條件,但“世世相繼”,則說明即使辰韓的生產力遠遠超出了當地土著人馬韓,也沒有取而代之的行動。從漢代一直延續到三國時期,四五百年間,辰韓都是馬韓附屬國,這在朝鮮半島高麗時期成書的《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中就有記載。*金富軾:《三國史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頁。辰韓人“行者相逢,皆住讓路”,展現的也是一種尊重對方、和諧相處的絲路文化精神,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文化,才使得馬韓能夠接受辰韓,辰韓人能在異國他鄉長期存在,并與當地人融為一體。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辰韓應是徐福集團建立的。徐福東渡把秦王朝高度發達的造船、航海技術,冶鐵及制造鐵器、高檔絲綢等技藝,還有“宜種五谷及稻”“乘駕牛馬”等先進的生產方式,以及相互尊重、和諧文明的生活習俗帶到朝鮮半島南部,也大幅度地推動了朝鮮半島南部的發展進步,使得當時還處在原始社會狀態的馬韓綜合國力和生產力水平得到飛速提高。
(二)對日本彌生文化貢獻最大的應是徐福集團
日本歷史上有過一段刀耕火種的蒙昧階段,后來由原始的繩文文化迅速進入了更先進的彌生文化。彌生文化因最早在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町發現彌生式陶器而得名。考古發掘證明,日本人民在這一時期開始了農業生產,尤其是水稻種植,同時也開始使用青銅器和鐵制生產工具以及絲織品等,而且出現了文字。所有這些,都與此前的繩文文化沒有任何傳承關系。這一文化上的質變時期,即日本的彌生時代。這種文化上的質變,生產力的跳躍式發展,不可能憑空而生,日本學界尤其是考古界認為:彌生文化源于中國北方沿海文化。對此貢獻最大的,應是東渡到日本的徐福集團,因為只有像徐福帶去的先進生產力,才有可能促使日本發生這種質的突變。
日本的彌生時代,起止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300年,持續了約500年,相當于中國的秦漢時期。也就是說,日本的彌生文化開始于中國的秦朝時期。彌生文化最大的遺址,位于九州島北部的佐賀縣吉野里丘陵,這一帶也應是徐福集團東渡經由對馬島、壹岐島,越過朝鮮海峽后登陸日本九州島的登陸地。彌生文化有一顯著特點:在日本仍處于原始生活狀態的繩文文化時期便開始了農業生產,并種植了水稻,生產中使用青銅器和鐵制工具。中國社科院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曾撰文指出:“古代日本沒有經過真正的青銅器時代,而是由新石器時代直接過渡到鐵器時代,但彌生的鐵器時代還沒有完全排擠掉石器。”*安志敏:《日本吉野ケ里和中國江南文化》,《東南文化》1990年第5期。也就是說,日本的社會進步發生了跨越式的發展。研究古代日中文化交流的專家,日本學者羽田武榮博士指出:從日本出土的文物考察看,“這些東西起源于中國沿海東夷人”,“彌生文化并不是繩文文化的繼續和發展,而是外來文化。而傳播這些文化的人則是包括徐福東渡集團在內的中國人”*[日本]羽田武榮:《日本學者看徐福》,《海洋世界》1995年第7期。。羽田武榮博士在《與徐福相關的古印章》的報告中,還詳細介紹過20世紀30年代,在日本“富士山下挖得一枚獅形印章的情況,該印高31.3mm,印長22mm,重47.4克。印面為大篆‘秦’字樣,印質似為青銅合金。……該印造型為秦、漢時代流行的獅形印,可確定系中國大陸遺物”*劉毅:《徐福研究評述》,《日本研究》1992年第1期。。日本彌生時代沒有自己的文字,而是借用的中國漢字。日本吉野里遺址“環壕聚落及其防御措施的嚴密,農耕和手工業的分工,商業性貿易的出現,墳丘墓所象征的階級分化,都標志著城市的萌芽”*安志敏:《日本吉野ケ里和中國江南文化》,《東南文化》1990年第5期。。這都說明,日本彌生時代,即中國的秦漢時期,與中國大陸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并受到中國先進文化的深刻影響,而徐福東渡應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日本彌生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出現了水稻的種植,這也標志著日本農耕時代的正式開啟。日本原先沒有野生水稻,其水稻種植學者們大都主張是中國大陸傳過去的,至于怎么傳到日本去的,專家們的觀點并不一致。安志敏就曾提到:“幾乎所有的學者都主張日本的稻作農耕來自中國,但傳入的通道卻有華北、華中和華南三種說法。過去以華北說占優勢,即由陸路(河北、遼寧)或海路(山東)經朝鮮半島而傳入日本。由于華北缺乏早期稻作的實證,作為傳播的起點是不大可能的。最近一般傾向于華中說,即由長江下游經東海而傳入朝鮮和日本,……繩文晚期稻作農耕的出現以及彌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當是由于海上交通而輸入的。”*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考古》1990年第4期。安志敏之所以否定了華北說,是因為“華北缺乏早期稻作的實證”,但隨著新的考古成果的問世,華北說又占了上風,這也為徐福東渡將稻作農耕帶入日本提供了證據。
20世紀末,山東和蘇北地區多處發現了龍山文化時期的稻谷遺存和稻田遺址,如山東煙臺市轄區的棲霞楊家圈二期文化遺址,山東日照市轄區的堯王城遺址、兩城鎮遺址、五蓮丹土遺址,山東淄博市轄區的臨淄田旺遺址;與山東鄰近的蘇北連云港市轄區藤花落遺址、贛榆縣鹽倉城遺址、贛榆縣后大堂遺址,等等。*靳桂云、欒豐實:《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稻作農業研究的進展與問題》,《農業考古》2006年第1期。這些地區稻谷遺存和稻田遺址的發現,既說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山東半島及周邊地區就開始種植水稻,也使得水稻種植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的路線越來越明朗化。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在1997年就撰文指出:“由于有(棲霞楊家圈遺址發現稻谷遺存)這一發現,稻谷農業最初傳入日本的路線開始明朗化了。過去有所謂北路說、中路說和南路說,后兩種說法事實上不大可能,而前一說又缺乏證據。楊家圈的發現證明北路說是有道理的。如前所述,從大汶口文化直到岳石文化的長時期中,山東半島的史前文化是單方面向遼東半島傳播的,而遼東半島史前文化對朝鮮半島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因此我提出了一個從山東半島經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再到日本九州島,以接力棒的方式傳播過去的說法,簡稱‘北路接力棒說’,此說后來因為在大連大嘴遺址和朝鮮平壤附近的南京遺址都發現了稻谷遺存而得到了相當的證實。”*嚴文明:《膠東考古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頁。
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水稻種植是由山東半島傳入的這一論斷,得到了中、日、韓三國專家的廣泛認同,有的日本專家還把日本彌生時代出現的稻作農耕與徐福東渡聯系到了一起。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農業大學、韓國漢城農業大學的中韓兩國專家共同完成的論文《也論中國栽培稻的起源與東傳》一文中提到:1991年在河南省舞陽賈湖遺址發現了距今約8000年的人工栽培的稻谷,說明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一樣,也是栽培稻的發源地。根據這一考古發現,兩國專家共同認為:“山東沿海的稻作文化有可能直接向東傳播至朝鮮半島中部的漢江下游,然后再由此向南北兩個方向擴散開來,向北至朝鮮半島北部,向南直至日本列島。”*張居中、王象坤、崔宗鈞、許文會:《也論中國栽培稻的起源與東傳》,《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日本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會事務局長內藤大典在《彌生旗手——徐福》一文中講道:“以相傳為徐福登陸地的佐賀市諸富町北部七公里處發現的吉野里遺跡出土的文物為證,并比照中國的仰韶文化遺址、半坡遺址、淹城遺址,認為徐福東渡集團是日本稻作文化的開創者,是彌生文化旗手。”*劉毅:《徐福研究評述》,《日本研究》1992年第1期。
專家學者們之所以更傾向于北路說,正如嚴文明教授所說,中路說和南路說“事實上不大可能”。這里說的“不大可能”,主要還是因為當時的航海條件從江浙閩沿海一帶直通日本是不現實的。三國時期東吳以一國之力,派出大批兵力乘船尋找徐福登陸的“亶洲”,也只能到達“夷洲”,今我國臺灣島,卻到不了徐福登陸的“亶洲”,今日本九州島。三國時期尚且如此,更不用說秦漢時期了。
日本彌生文化的另一表現,就是這一時期“大陸上大批的移民到了日本列島。這批移民的數量相當龐大,由于這批移民的到達(主要在北九州和本州的西部)并與當地土著居民通婚,一段時間內甚至改變了當地人的體質狀況,……彌生時代日本列島的人身高突然間增高了近三個厘米”*蔡鳳書:《古代中國與史前時代的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溯源》,《考古》1987年第11期。。短時間內中國大陸大批移民能夠到達日本,同樣不是分散的一家一戶移民可以達到的,也只有像徐福東渡集團這樣成千上萬的人才能做到,更何況徐福帶來了大批的童男童女,這些童男童女長大成人后,與當地人結婚生子,后代子女自然也具有了異族融合的遺傳優勢。
日本彌生文化的最大遺址——九州島島吉野里遺址的發現,為秦漢時期的中國人東渡日本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盡管將徐福東渡與日本九州島吉野里遺址中的先進文化要素聯系到一起還需進一步研究考證,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除了史料記載的徐福東渡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要素能夠如此大規格全方位地促進日本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日本彌生文化與徐福東渡的聯系是密不可分的。
徐福東渡先到朝鮮半島南部,再由朝鮮半島南下至日本列島,已成為現當代許多中、日、韓學者的共識。但徐福集團把日本作為登陸地,還是把朝鮮半島南部作為登陸地,看法并不一致。有專家認為“朝鮮半島的南部有大塊平原”,指的就是徐福找到的“平原廣澤”*朱亞非:《古代山東與海外交往史》,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6頁。。但包括日本學者在內的許多專家認為,徐福東渡的目的地是日本九州島,朝鮮半島不過是路過而已。前面提到的明清時期的朝鮮李朝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我們認為,徐福兩次東渡,因受航海能力和對日本了解的限制,第一次東渡應是停留在了朝鮮半島東南部,辰韓的建立應與徐福集團有關。在開發朝鮮半島時,由于技術人員和生產資料的短缺,才有了徐福攜“五谷種種百工而行”的第二次東渡。朝鮮半島東南部臨近日本,隨著對朝鮮海峽和日本的了解,徐福集團又有大批人員從朝鮮半島移居日本九州島,也就有了九州島吉野里遺址出現的生產力飛速發展的景象。
徐福東渡,是一次打著“入海求仙人”旗號,準備了豐厚的海外生存必需品,有組織、有目的的海外拓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海上絲綢之路活動。它不僅比漢武帝時期在陸路開辟的西域絲綢之路早了80多年,更比同樣是大規模海上絲綢之路活動的明代鄭和下西洋早了1600多年。徐福東渡不僅在“海上絲綢之路”傳播了中華文明,為當時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在東渡沿線灑下了友誼的種子,為漢代更大規模的中韓日海上絲綢之路拓寬了航道。到達彼岸的童男童女們繁衍生息,更是演繹著一代代中韓、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話,韓國和日本今天之所以仍在祭祀和紀念徐福,這應是主要原因。徐福率領的龐大船隊東渡遠航,是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創舉,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上探索和海外開發活動,也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了1700多年。所以,我們可以無愧地說,徐福不僅是中國早期海上絲綢之路航船上的偉大舵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開拓者。
(山東省作家協會趙月斌、山東教育出版社王慧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