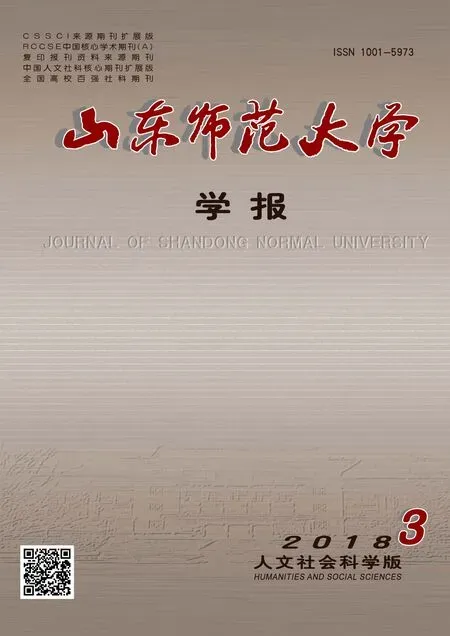語言統一的奮斗: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育實際效果評價*①
朱季康
( 揚州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揚州,225002 )
一、漢族區域小學校的情況
對于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學的效果評估,從整體上看是呈上升態勢的。1914年,李啟元曾評價當時的小學國文教學不但費力費時,而且效果不佳,他認為“取近來小學畢業之國文成績觀察之,幾至一年不如一年”*李啟元:《論小學國語教授宜特別注意》,《京師教育報》1914年第4期。。黎劭西認為,潮流雖然轟轟烈烈,但影響還未達于鄉村。在1916年的廣大鄉村中,仍有很多小學未知曉國文教學的意義并進行實踐。到1920年,這種情況還是很明顯。“在民國九年一月以前,只有江蘇幾個特別的小學校教語體文,以外的,把語體文都認為奇怪的東西,鄉村的小學,連聽都沒有聽到。”*黎劭西:《國語教育底三步》,《國語月刊》1922年第6期。
對于小學國語教育的推行,民國學者們也有一些理想。如1919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議案》中,有人推想:“二十年以后,國音普及全國;窮鄉僻壤里種田的男子,養蠶的女人,因為附近的小學校里用國音教授國語,以致他們也能講國語、讀國音;到那時候,就是他們看的淺俗書報,也可以用國語國音編撰,無須更用方言方音了。”*《國語統一籌備會議案三件》,《北京大學月刊》1919年第4期。這份推想不但描繪了小學國語教育對全體國民國語普及的貢獻,還提到了國語推廣普及后,各地方言的存續情況,字里行間滿是自信。“但國語國音,可以用人力強迫全國早日普及,而國語國音普及以后,方言方音必無即日滅亡之理,并且也不能用人力強迫他定期滅亡。”*《國語統一籌備會議案三件》,《北京大學月刊》1919年第4期。黎巾卉認為,自1918年起,不是官話區域的東南各省中,很多熱心國語的人士都在努力,安慶、蕪湖、南京、上海、寶山、南通、杭州、松江、寧波、鎮海、福州、廈門、廣州、瓊州等地皆是如此。“并且《小學用國語讀本》的銷行,差不多東南各省占有全國二分之一,所以我敢說,國語在東南各省的宣傳,比官話區域要上緊些,成績也多些,當真的,并非謬獎!”*黎巾卉:《國語在東南各省的發展》,《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1923年第23期。
有人對于國語教育的未來并不那么樂觀。1920年,有人評價:“這件事,單靠著教育部慢慢兒做去。不知何年何月方才普及,全靠各省高級的行政機關和公共團體,大家籌辦,才有些希望呀。”*我一:《提倡國語的難關怎樣過渡呢?》,《教育雜志》1920年第4期。范祥善就對國語教育推行的難度有清楚的認識。他說:“不過從前有句話:‘言之匪艱,行之惟艱’。現在學校里的教師,正是犯了這個毛病。你想教授國語一句話,說來很便,試問如何實行呢?據我所知道的:著名的各學校,正在那里研究教授順序,教授案……等種種細功夫;次一些,雖是也在搖旗擂鼓,鬧得驚天動地,待到角色出場,怕要被看客喝倒采呢?再次一些,就是形式上用了一本國語教科書,實際上依舊是挨腔挨板的朗讀,這真所謂‘換湯不換藥’的一句俗話了。然而這種學校,倒占一個大多數,至于頑固派的反對國語,我也不屑和他辯論了。”*范祥善:《怎樣教授國語》,《教育雜志》1920年第4期。即使是在強力堅持國語教育推廣的這些學者心里,這種感覺,也常縈繞他們的心頭。在現實中,他們既自慰于大家做了一些事情,但同時又深刻地感受到民初社會對于國語教育的排斥,以至于有的學校為了教授國語,竟被家庭反對,社會唾棄。實際上,他們自己也常常陷入使用國語的糾結。“自己做的這些文章,都還脫不了紳士的架子,總覺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不是我們用的,而是他們——高小以下的學生們和粗實文字的平民用的,充其量也不過是我們對他們于必要時用的,而不是我們自己用的。”*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34頁。有人還建議在推廣國語教育的同時,不能減少方言方音的演講、方言方音的書報。雖然這些建議有其理由,但也可見社會對于國語推廣的障礙。“我國自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議,決以北平語為標準語以來,各小學并不注意實行,仍以方言教育。”*《教育部厲行國語教育》,《時事月報》1930年第2期。直至1935年,民國政府一項統計表明,全國識字的人不超過20%。*途友:《拉丁化與方言統一》,《大同月刊》1935年第3期。而在國語普及上,各地極大多數的人還是用著各地的方言。有人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相傳有一個鄉下孩子,到北京去學買賣。整學了三年,才功行圓滿,回家省親。他一進家門,首先看見自己的父親。他急忙走向前,施了一禮,說一聲“爸爸您好!”誰知“您好”二字,尚未脫口,“拍!”的一下,他父親給了他個大嘴巴,他正在莫名其妙,就聽得他父親說:“你居然叫我‘爸爸’!好小子!跟你‘爹’都撇起京腔來了!”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爸爸”得罪了“爹”。他趕緊謝過,說:“你老人家不必生氣。我在北京待了三年之久,叫‘爸爸’,叫慣了。”他父親一聽,更是“怒不可遏”,高聲叫罵:“你在北京都是管誰叫‘爸爸’,叫慣了?”*老向:《論小學國語中的爸爸媽媽等》,《眾志月刊》1934年第2期。由這個故事,作者提出在親戚稱呼上,教科書沒有必要改變學生的習慣。一些人以為,國語普及并不是方言的結束,所謂“目的并不是在反對國語統一,而是在說明用一個方言來削平群雄定于一尊以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這種方法是行不通的”*陳丹企:《略論國語與方言》,《中國語文》(上海)1941年第3-4期。。這也是一種觀點。
到了小學國語教學的實質性推廣階段,尤其是教育部通令全國各小學校改國文為語體文后,全國各地小學校終于開始都要學習國語了。黎劭西說:“好了,照章辦事的鄉村小學校,現在也知道了,也要改國文為語體文了。所以,我從前說這道命令,實在是中國歷史一大改革。”*黎劭西:《國語教育底三步》,《國語周刊》1922年第6期。
這段時期,民國教育界除了積極推行國語教學外,也開始對教學效果開展了一些評價工作。如1929年1月7日,民國教育部下發指令380號給予了客觀評價:“前國語統一籌備會前后辦理國語講習所四次,也并傳授注音字母。十年以后,中小學校大都能利用注音字母作語音字音的標準,不可謂非此等傳習之功。”有人說,推行國語,“學校方面,不過閱讀幾本國語教科書,模仿幾句四不像的藍青官話,一般先生們學生們,已覺得心滿意足了”*云六:《教育評壇推行國語教育的我見》,《教育雜志》1922年第2期。。這是對國語教育推行不力學校的評價。各地也有一些相關的匯報。如上海崇明朱有成報告說崇明本地人將國民學校國音練習視為外國書,“他們對于外國有一種天然憎惡心,所以他們看了像外國書似的書,極端的不贊成”;而“國語的語音和聲調,大都根據北京話,語調不同,還沒有多大的關系,語音不同,是個極大的難題,……這是鄉人腦筋中最反對的”*朱有成:《鄉村地方推行國語的難處和救濟的方法》,《國語月刊》1922年第8期。。歐陽潤說湖南隆中在國語推行方面遭受到民間的巨大阻力。“而對于國語一科,不惟不甚發展,且或加以誹謗哪!我們當表白意思的時候,若去掉方言,他們必笑我們是‘敲竹腦殼’。”*歐陽潤:《湖南寶慶隆中團的國語狀況》,《國語月刊》1922年第8期。綜合來看,很多地區的小學校雖然改了國語教學,但文字障礙仍舊存在。在很多少數民聚居區,這樣的情況更加普遍。“其能應用現代學校教育方式傳授民族語言者,只有新疆之突厥系各族,其歷史亦不過十年,教材缺乏,字母使用及拼音標準尚多不能一致。”*芮逸夫:《中國邊疆民族之語言文字及其傳授方法》,《中國邊疆》1948年第11期。
一些觀察從宏觀上指出,小學國語教育還需要時間的積淀以及強有力的監督制度才能有實效。“國語教育,亦一重大問題,近來各縣小學,各師范,各中等學校,改授國語科者,類多有名無實;設非省有專員,隨時視察,周歷指導,分別獎懲,恐十年二十年,國語空氣,不得濃密。”*《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議案全文》,《國語月刊》1922年第9期。有人說民國雖然有種種小學國語教育推行的措施,但在實施上,卻并不如人意。“除卻城市小學以外,在一個縣份是很少有實施的,至于談到鄉村小學中的語言統一訓練,那更是不足道了。”*葉霖:《國語教學上的語言統一訓練問題的研討》,《安徽教育輔導旬刊》1936年第28期。
在很多較為閉塞的地區,即使學生在小學中學習了國語,回到家中后,他們所學習的國音也無使用之地,因為在家庭里,一家人談話間是不會用國語的,而是習慣地用方言。家長們往往以為國音難懂,而依舊逼迫孩子講習方言。“做父母的不肯改。要做子弟的先改。一家的人不全改。要一部份人先改。這就是難事。”*我一:《提倡國語的難關怎樣過渡呢?》,《教育雜志》1920年第4期。從學生自身來說,對于從小就說習慣了的方言,很不容易改口。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學生的國語學習效果很難得到鞏固。“今使一出校門。而入于耳者,仍盡是娓娓之鄉談。則每周數小時之教課。果能奏若干之效果也耶。”*羅重民:《國民之統一與國語之統一》,《學藝》1917年第2期。趙廷為就坦承道:“倘然兒童在校內和校外的實際生活中仍然應用土語而不應用國語,那末,兒童雖讀熟了一百部漢字注音的教科書,也是不中用的。”*趙廷為:《小學國語教學問題》,《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叢刊》1935年第2期。所以,也有時人評價,要完成中國的語言統一絕不是一個短期的工作。“這工作至少也得經過三個世紀以上的時期才能收效。而且,照這樣,這一件統一工作還是發展得很不自然。”*希行:《也來談談關于方言劇》,《中國語文》(上海)1941年第3、4期。而如果沒有其他條件,尤其是交通條件的配合,這樣的工作則更加艱難。首先要建設好全國的基礎交通設施,然后才能使各地語言得到充分的接觸。如果沒有這樣的交通基礎設施,沒有達到全國各個語言、方言間的民眾的自然接觸,仍舊是割裂、封閉的狀態,是不可能實現國語的通行的。
在當前的新媒體時代的發展下,檔案文化充分借助新媒體進行廣泛傳播。隨著當前現代先進的科學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人工智能化的不斷進步,新媒體成功地運用了現代互聯網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極大地受到了大眾的喜愛。而檔案文化也已經成功的借助了新媒體時代下的新興的傳播媒介建立了更加龐大的檔案文化資源管理數據庫,有效地提高了檔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并且由于新媒體自身帶有的即時性以及便捷性的特點,能夠使得大眾在第一時間獲得政府所發放的最新關于檔案文化信息的相關內容,與此同時企業也能夠及時的受到群眾的反饋意見,進而迅速采取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也有一些評價具有現實與指導意義。如1922年,北京國語總會就對全市的小學國音字母的教學效果進行了測試。其結果如下表*《國語界消息》,《國語月刊》1922年第11期。:

學校得獎人數加獎人數學校得獎人數加獎人數公立第十九小學180女高師附屬小學222公立第八小學40第二女子小學190公立第三十四小學120公立第十小學586第一女子小學120公立第三十五小學120高師附屬小學1092公立第四小學10415公立第二十三小學300公立第十三小學518公立第二十四高小170公立第十五小學300公立第二十六高小80公立第二十二小學514公立第三十一高小30公立第二十七小學300公立第四十高小30平民補習學校161普勵小學140師范一部分196第二十四國民學校90公立第十八小學482公立第一兩等學校30第一國民學校80公立第三小學30公立第十一小學682公立第五小學70公立第十二小學70公立第六小學60公立第十七小學806公立第二十五小學90公立第三十六小學70公立第三十八小學90第三女子小學20東郊第一小學171平民第三小學180平民第一小學71共計94956
從上表可見,盡管同是北京市的學校,其在小學國語教學方面的效果差異還是很大的,并不均衡。再如吳縣地區各高等小學中,每個星期用于國語會話教育的時間僅有一二小時,其余仍舊是“之乎者也”地鬧個不輕。這種情況普遍存在于全國的小學中,王家鰲稱:“據我的朋友說,方才知道不單是我們吳縣高等小學是這樣的,各處差不多都是這樣。”*王家鰲:《高等小學的國文應該快改國語》,《國語月刊》1922年第3期。范祥善就評判各地小學的國語教育很難達到教育部的基本要求,指出:“就是畢業最低限度內所定的初級小學識普通的文字二千個左右,高級小學識字累計三千五百個左右,也是一種虛構之談,并沒有經過甚么調查統計的工夫,嚴格說起來,那里可以信得過?”*范祥善:《小學國語教學法的將來》,《新教育》1925年第3期。何仲英說:“有人說得好:‘為什么一個人進學校,在上海要學蘇白;在北京要學京腔’”*何仲英:《提倡國語與研究方言》,《約翰聲》1923年第2期。。
師資問題是很多學者所關注到的因素,他們認為小學國語教學推行不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合格的國語教師的缺乏。趙廷為就直述:“與其努力于漢字注音的運動,還不如先努力來解決這更根本的師資問題。”*趙廷為:《小學國語教學問題》,《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叢刊》1935年第2期。而師資是否合格,對于國語注音的教學效果又有極大的影響。沒有合格的小學國語教師,不可能嫻熟地教授漢字注音的教科書,其教學效果難以保障。有些鄉村小學教師自己還不懂注音符號,如何去從事國語教學呢?“然而可惜的是:領導這個運動的人們沒有注意語言同化的自然規律,不知道從各地方言的交互影響,因勢利導,而只是機械的片面的推行法定的國語,即那已經失去全國中心都市地位的北平的方言。于是注音符號除了在小學教科書的生字旁邊和國音字典上注國音以外,便沒有別的用處了。……就小學的國語正音教育來說,因為缺乏說北平話的師資,也就大半不能實施。”*伯韓:《方言的使用和研究》,《文化雜志(桂林)》1942年第3期。
注音教學與實際國語教學效果也緊密相關。小學國語教育中常使用每字注音的方式,以簡化、熟練學生學習的過程,促進學生的學習。在課堂教學中,這種做法有其有利之處,但亦存在不利之處,因為在社會生活中所閱讀的材料,絕不會是每個字都標有注音的。由于在課堂教學時每個字都注音,導致學生產生了依賴。在小學國語教學中,因為教者難以達到統一的標準國音教授的水準,學生也得不到標準國音的受教。尤其是在與國音標準差異較大的南方方言區內,這種情況更加明顯。恰如黃德安所說:“現在各地短期小學對于注音教學,有的拘守課本上的注音,厲行國音平調,有的變更課本的注音,仍用方音鄉調。有的對于國音與方音,平調與鄉調,躊躇不定,無所適從。有的根本上不知道注音,或不注意注音,對于注音符號,視同贅疣,不加理會。”*黃德安:《短期義教如何注意國語的統一與普及》,《湖南義教》1936年第38期。
以上這些情況,為民國小學國語教學評估帶來了動力。很多學校還自發組織參與與國語教學有關的比賽。1921年,山車輞坂小學每周都組織小型的演講會、辯論會,“起先的時候,大家覺得很不高興,后來也慣常了”*王家鰲:《試行國語教學后的大略報告》,《教育雜志》1921年第8期。。1922年1月11日晚上7點,在上海的寧波同鄉會會館里,上海很多學校聯合組織了國語運動學藝大會。加入表演的,有坤范女中學、民生女學、國民公學、北區公學、萬竹女校、國語專修學校、奉賢女校、開智小學、紫金小學、養正小學、養性女學、飛虹小學等眾多學校。*《國語界消息略志》,《國語月刊》1922年第1期。演講是最能直接反映學生國語綜合素質的項目,所以演講比賽在很多學校都有開展。如1931年,集美男小學為了鼓勵學生練習口才及國語,進行了國語演講比賽,由高年級每班推出3名選手參加。比賽開始前30分鐘,由校長親自揭示演講題目《集小學生應否學習英語》。“各演員接到題目后,均聚精會神,預抒發表意見。屆時即相繼登臺發揮,態度聲音,俱頗自然清晰。”*《男小學校消息甲組國語演講比賽》,《集美周刊》1931年第274期。各地小學國語教育的比賽活動此起彼伏,精彩不斷,也啟發了全國性的相關活動。如1934年9月,教育部就向全國各地的教育廳發布了《全國小學國語文競賽會辦法》,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國語文競賽活動,其宗旨是“競賽國語文,促進國語普及”,其參與者“以全國公私立小學校學生為限”*《全國小學國語文競賽會辦法》,《河北教育公報》1934年第27-29期。。這些活動的組織與開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小學國語教學的發展。
1947年,有人曾對臺灣省國語教育運動的效果進行評價,指出有了長足的進步,而其中進步最快的就是小學生。“臺灣的國語運動,自光復以來,總算有了長足的進步。說得最好的是小學生,其次是中學生,再次恐怕就要算商人了。”*味橄:《臺灣的國語運動》,《臺灣文化》1947年第7期。臺灣省由于長期遭受日本語言殖民政策的影響,日語成為臺灣光復前當地民眾的主流語言。但在臺灣光復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強化國語的措施,使得臺灣省國語通行狀況有了明顯的改變,尤其是小學國語教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少數民族地區小學母語教育的評價
(一)區域性差異
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育的推行,使少數民族地區小學國語教育亦有一定的進步。根據20世紀30年代的統計,民國教育部在1935-1938年間,設立了2375所邊疆小學,具體分布為:甘肅省55所,青海省143所,寧夏省14所,西康省5所,云南省35所,貴州省12所,四川省15所,湖南省100所,新疆省1412所,綏遠省29所,察哈爾省13所,廣西省541所,西藏1所。其中,新疆建設的最多,占了一半以上,而西藏則僅有1所,可見邊疆小學在建設數量上存在著區域差異。在這些邊疆小學中,基本都設有少數民族語言課程與國語課程,承擔著小學國語教育的任務。到了1949年,梁素人評價:“十八年來為少數民族而設的國營邊疆學校僅有四二校,三〇五班,九、六一一(原文如此,引者注)學生,卻散布在面積遼闊的十五省區,二千萬人口里,真是鳳毛麟角,渺小可憐的數字。”*梁素人:《新中國的少數民族教育問題》,《中華教育界》1949年第9期。
在少數民族小學國語教育推廣評價上,區域性差異非常明顯。如1938年設立的國立拉薩小學,有藏文班、回文(即阿拉伯文)班、國(漢)藏文班,設有藏文、國語、算術、歷史、地理、公民、常識、音樂、圖畫、體育、習字和阿拉伯文等課程。該校初期僅有不足百人的學生規模,除了少數藏族學生外,大部分是維吾爾族、漢族及外商、尼泊爾官員的子弟。該校于1949年停辦,但全部高小畢業生僅有12人。從小學國語教育的推廣效果上看,這所學校幾乎沒有建樹。在新疆地區,則有相對更多的努力。在教育部令的要求下,凡是有辦學條件的縣城學校都在努力貫徹相關命令,疏勒、莎車、澤普、麥蓋提、巴楚、伽師、阿圖什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先后建立起了學校。1932年,新疆的各個縣僅有一兩所小學,短短4年后,僅莎車一地,學校數目即達199所,學生22000多人。這些學校基本都有漢語課程;如柯坪縣學校內設有國文(漢語)、修身、算術、維吾爾文等語言課程;塔爾迪吐然學校(后改為伊犁區立鞏乃斯學校)開設了哈薩克文、漢語等課程。1934年起,維吾爾、哈薩克等族民族文化促進會陸續建立并創辦了不少小學,在這些會立小學中,基本上都有漢語課程。僅1937年哈薩克文化會即創辦了學校275所,學生規模達到14322人,開設有語文課程,小學高年級則有漢語課程。至1940年,新疆公立與會立小學中的少數民族學生已經達到210019名,含維吾爾族學生162378名,哈薩克、柯爾克族學生34412名,回族學生4723名,蒙古族學生1868名,塔塔爾族學生1151名,烏孜別克族學生721名,俄羅斯族學生2458名,滿族學生182名,塔吉克族學生46名。許景灝在《新疆志略》中稱,1942年,新疆僅會立學校即達1883所,學生180035人。少數民族地區小學的開辦數量也對小學國語教育的推廣有直接影響。如1936年,經過努力,云南省已設立省立小學34所,雖然這些小學的國語教育還存在著課本選擇的困惑,但是其規模及效果已有客觀呈現。1938年,寧夏全省已有小學200余所。同年,青海全省也有回民小學15所,學生有2000人左右,初級小學76所,學生有4000人左右。這些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的小學數量與密度雖然不能與內地或漢族地區相比,但縱向比較,進步十分明顯。
(二)有利于少數民族小學國語教育開展的原因
首先是這些地區普遍實行了有利于小學國語教育推廣的教育政策。
早在清末,新疆就在推廣漢語教育。到了民國時期,在楊增新執政新疆時,他雖然認同強迫維吾爾族兒童直接接受漢語授課,給開發維吾爾族兒童早期的智慧帶來了一定的損失,但也堅持認為這種政策有利于民族的交流與理解。民國政府還在寧夏、貴州、西康、西藏等地設立了實驗中心學校,“以迎合其特殊環境與實際需要”,“其語言文字教學方法,均與內地小學不同”*《教育部邊疆教育現狀》,《邊疆服務》1943年第5期。。1946年,新疆伊犁就根據《和平條款》,實行了維文與漢文并行的行文政策。1949年7月,新疆省政府再次發文,通令各單位公文國文通用。*李儒忠、曹春梅:《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育前年大事年表(之一)》,《新疆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新疆與西藏地區之所以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除了兩地少數民族語言學習環境、習慣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雙語師資的培養。
1935年,新疆省立師范即開設了維吾爾族師范班,三年制。1939年又開始開設哈薩克族3年制師范班。新疆學院以語文系國語專修科(兩年制)招生,培養維吾爾、哈薩克族學生學習漢語,畢業生大都作為雙語師資而進入各級學校。
外國傳教士在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的傳道教育雖然具有文化侵略的性質,但在客觀上也推動了這些地區少數民族接受國語教育。他們所創辦的學校,尤其是小學階段的學校教育,對于少數民族學生接受漢語教育有很大的幫助。如在西南地區,無論是云南的瀾滄、車里,還是漢越鐵路沿線,都有英法傳教士所創辦的學校。如在卡瓦山一帶有學校17所,福音宣講所90處;在羅黑山一帶有學校14所,福音宣講所136處。
(三)不利于少數民族小學國語教育開展的原因
首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的教育基礎較內地薄弱。單薄的基礎教育事業無論在體量規模上,還是質量上,都難以擔當小學國語教育推廣的重任。如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等省份,是回族聚居區域,但回民教育仍較內地各省落后,小學校數量也很少。在一些地區,因為經費緊張,也經常挪用小學教育經費。
其次是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流行著漠視教育的風氣,尤其是不愿意接受漢族所主導的教育模式。曾在西北藏區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俞湘文就明顯地感受到當地藏民在為子女選擇教育內容時,對于接受漢族文字教育有受壓迫的感覺。其最大原因在于心理層面,因為一個民族有他們固有的文字,若是外界強迫他們去學另一民族的文字,會使他們思想上意識到壓迫而產生反感。他舉例說,1943年初,當地的康根小學成立時,受到了當地藏民的反對,民眾反對設立學校的原因有三:一是孩子是家庭中的一份生產力,孩子去當學生,如同抽去了這個家庭的一份勞動力;二是該地區文化落后,生活簡單,大部分民眾覺得接受教育沒有必要;三是藏族民眾以為學習另一民族的文字會喪失他們民族的自尊心。可見,除了對于漢語教育的排斥,這些民眾由于生活環境、家庭情況以及教育回報期待等原因,也對子女教育本身缺少興趣和動力。回族學者艾沙曾對新疆教育有一定了解,他總結回民不愿意接受漢族語言教育的原因有四點:一是回民們的宗教信仰濃厚,認為接受了漢族語言教育及漢族文化教育,就會不知不覺中失去對宗教的信心。這一觀點在阿訇中十分流行,也成為他們積極反對漢語語言教育的借口。所以,在社會上無形中形成一種風氣,以讀漢書為恥。二是回民們普遍對漢族文化存在著鄙視的姿態,以為漢族文化中沒有什么學問,所以不愿意去了解與學習。三是回民從清末開始,即對漢族懷有戒心,總以為漢族語言教育與文化教育帶有民族同化的陰謀。而越是漢族教育官員催逼回民子弟學習漢語,越造成回民的抵觸情緒,兩種極相反的心理交互作用,遂使回民不學漢語的問題更為復雜化。四是他們認為學習了漢族語言的回民大多會與漢族官員相聯系,“學者愈多,民族基礎,愈趨動搖”*艾沙作、矯如述:《新疆回民教育之回顧與瞻望》,《邊鐸》1934年第2期。。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出現了強征少數民族學生來學習,而非他們自愿求學的情況。這些地區小學的學生多數是接近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漢族子弟,而不是少數民族子弟。而其中來入學的少數民族子弟,大都是以強制手段征來的。一些地區甚至以官位與俸祿相引誘,乃至采取強迫攤派的手段,但自愿入學者依舊是鳳毛麟角。
即使是一些所謂的“教育”,其實質卻是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有很大區別。如在新疆地區,很多家庭在其孩子實行割禮以后,就送到宗教場所進行學習。但在這些場所進行的教育,完全是為培養孩子的宗教信仰而服務的。在這些宗教場所進行的學習內容,主要是將一些阿拉伯語的宗教經典進行背誦,方法十分機械。很多孩子經過幾年學習,即使能夠背誦得很熟練,對于阿拉伯語的字母拼音、意義等也仍很不明白。而在西藏地區,實際上缺乏宗教內容以外的藏文書籍。如果要將藏文教育作為普及教育的途徑,其成本是浩大的,因為需要將宗教之外講述新知識的書籍翻譯為藏文,這不但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而且因為這種翻譯工作的人才不易尋求,很難完成。此外,因為當時藏族的平民幾乎都是文盲,即使翻譯成功這些藏文書籍,對于藏民來說,仍是無濟于事。還是要從基本的識字階段開始,所以要用邊民自己的文字來推廣教育,并不是短時間可能實現的事情。而藏文也大多只有宗教界人士才能掌握,平民中掌握藏文的也不多。
即使一些少數民族小學生接受了學校教育,學習了漢語,但在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環境的限制下,也很難在生活中使用漢語。尤其是一些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正常、有較大影響力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域中,漢語的使用空間十分狹小。王一影就評價道:“除土司土目階級外,民族民間是很少能講說漢語的。然而各地的邊民學校,大部份是用國語或土語教授漢字,在整個國家教育方針上說,固然不錯,不過在教學的方法上說,來入學的夷族青年子弟既不易聽懂,而不科學的方塊漢字,更使夷族學生感覺得記憶是非常的困難,所以夷族青年子弟,視讀書為畏途。……就是夷族青年子弟,在學校中努力記得幾個漢字,學會幾句漢話,回到家中,無處應用,一頃刻也都忘了。”*王一影:《泛論邊疆夷族青年的教育與訓練》,《邊政公論》1941年第3-4期。長此以往,這些學生覺得學習漢語沒有用處,也對學習產生了抗拒的情感。往往少數民族學生覺得學習是可怕的事情。漢語沒有成為當地少數民族必不可少的交際工具,自然失去了對少數民族子弟的吸引力。1944年,新疆警務處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稱新疆人口占前三位的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共有人口400萬左右,其中絕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語言。而使用漢語的主要是漢族、回族、滿族等,其總人口不過33萬。從民族分布情況來看,漢語的使用范圍也是有限的,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區。
在小學國語教育實施的同時,對于國語標準的爭論依然在持續,這些爭論也影響到了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育的進行。“由方言的分化到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這里伴隨著古老民族的不斷融合與混合,同時政治與經濟的集中,使語言形成一種向心的運動,同離心的運動(方言不斷分化)作斗爭,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才會形成與穩定下來。”*周雙利:《馬克思、恩格斯論民族與民族語的形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方言區的一些小學教師對方言懷有感情,在教學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使用方言的情況十分普遍。“在提倡統一國語的聲浪之下,每一個學生不得不對于每一個漢字,兼學一個土音和一個國音。”*趙廷為:《小學國語教學問題》,《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叢刊》1935年第2期。有人說:“文字在方言變成普通話的過程中不是不曾起過作用,但主要的不是那種國音字典和注了國音的小學教本,而是用北方口頭話寫的小說、劇本和雜志文等。”*伯韓:《方言的使用和研究》,《文化雜志》1942年第3期。而更加復雜的是,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育的推行,還引起了民眾語言心理上的變化。“受不同方言習慣的影響,推行國語亦引起民眾方言觀念上的文化沖突,這一集體群像充分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化轉型過程中復雜的社會面相。”*賈猛、崔明海:《認同與困惑:近代白話文推行的社會反應力》,《學術界》2011年第6期。
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育的推行,本質上是中國語言界對于推廣標準語言奮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育的實際效果評價上,無論是對漢族小學校,還是對少數民族小學校,其結果都不盡如人意,其中原因很多。但民國時期小學國語教育的實施,為中國語言統一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亦有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