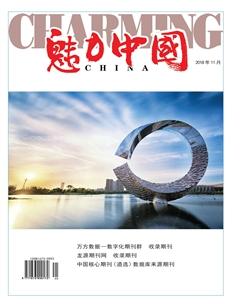道德文化價值的目標與實現途徑
劉合行
摘要:道德文化價值的核心目標是真善美的統一,具體表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幸福與道德、滿足精神需要與提升文化品位的統一。道德文化價值的實現需要通過一定的途徑來進行。通過提升道德文化價值目標,確立道德文化價值原則,建立科學的道德文化價值評價體系等,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價值體系。
關鍵詞:道德;文化;價值;目標
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的道德屬性首先表現在道德是文化的核心價值。從某種程度上講,文化諸多方面形態功能和作用的發揮,都滲透著道德價值的功能與作用。道德文化價值是道德價值在文化領域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反映著道德與文化諸多其它要素之間的作用關系。道德與文化的關系,決定了道德文化價值與文化價值的關系,道德文化價值是文化價值一個方面的重要體現。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而不同文化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其文化價值體系的差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上,如何更好地實現道德文化價值功能,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道德文化價值的目標
“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進行塑造,而人則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1]從馬克思這一論述的意義上來說,人的文化活動就是人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實現過程,道德文化價值作為一個社會的共同目標和追求,其核心目標就是真善美的統一。雖然由于所處層次與側重點的不同,真善美三者存在著矛盾性:真與美之間存在著“可信”與“可愛”的矛盾,善與美之間存在著情理之爭、理欲之爭的矛盾,真與善之間存在著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矛盾。但善和美必須以真為前提,真善美統一于人的自由。真善美的統一是人們的理想追求。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是人區別于其它動物的根本特征。對真善美的追也是社會發展客觀必然性的根本體現,真善美的統一將使人的存在、人的生活達到一種最高境界,實現全面與自由的發展。真善美的統一具體表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幸福與道德的統一、滿足精神需要與提升文化品位的統一三個方面。
(一)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
先進文化必然是人類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真理性認識的客觀反映。新時期建設先進文化就要準確時代發展趨勢,將實事求是這一時代精神注入到文化體系當中,提煉出能夠代表和反映時代潮流的先進文化觀念和精神氣質,并使這些先進文化觀念和精神氣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得到發揚光大,從而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
科學是人類獨特的文化形式,在改變人類生活,為人類帶來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以心智成熟和精神完善為重要標志的科學精神。人文精神是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中心的思想。而人是存在不同時代的,所以,人文精神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特點和歷史痕跡。馬克思主義的人文精神為建設新的人文精神指明了方向。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具有不同的特點:科學精神追求真實,推崇理性至上;人文精神追求美好,推崇感性和多樣化。它們是人類認識世界不可或缺的兩種基本方法和維度,二者都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克服這些局限性的要務在于對方的介入。所以,只有將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統一起來才能構成完整的人類思維和文化。如果只重視人文精神而忽視科學求真的精神,人類就會陷入虛無縹緲的非理性狀態,甚至走向瘋狂。同樣,科學所追求的目標在其自身范圍內也是難以達到,現實中存在的一些事情如道德等是不能用科學來衡量的。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互補的關系,二者的統一是當代文化的主導趨勢。縱觀人類文化的發展歷程,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統一也是占據主流地位。尤其是當代,大量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出現,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交匯融合的巨大潮流已經迎面而來;人性化已經成為當下高科技發展的一大趨勢,關注人的需要和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成為高科技發展新的關注點。科學活動和人文活動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內容,都是在人類的推動下發展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有著內在根據。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相互融入體現在科學向人學的滲透和人文精神向科學的融入。科學向人學的滲透主要是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理性被用來研究和解釋人文現象。人文精神向科學的融入主要是在科學研究中將科學的興衰與人類的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日益重視科學活動對人的影響。
(二)實現幸福與道德的統一
道德和幸福是倫理學主要研究的兩個問題。善是道德文化價值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追求“至善”必須處理好道德與幸福的關系。
道德不等于幸福。幸福是一種生活狀態或者說是一種生活過程,是人內心世界對生活滿意的一種感受。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幸福往往等同于德性或者美德,道德被認為是人的終極目標。以道德作為人的終極目標著眼于維護社會秩序和整體利益的實現,忽視甚至否認個人利益,這必然限制個體的全面發展和個性自由。一方面,德性或者美德并不等于幸福。作為一個個體的人除了德性之外,還有自身賴于生存和發展的身體、智能等,只有德性或者美德不能使人真正感到對生活的滿意。另一方面,遵守社會規范規則更不能與幸福等同化。因為遵守社會規范規則只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
亞里士多德指出:“較之于其他對象,幸福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終極目的;我們總是因為幸福本身,而不是因其他任何理由而選擇幸福。它不同于榮譽、智力、美德:對于后者,我們有時為了其本身,有時則為了幸福而選擇它們”。 [2]隨著社會的發展,內涵日益豐富的幸福被確立為人的終極目標。作為人的終極目標的幸福在于生活的更好。人對生活的感受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概念,滿意的程度始終發生著變化,量變引起質變,滿意與不滿意相互轉化。滿意作為幸福的表現形式,不僅映射出對生活狀況的認知而且包含對相關生活狀況的評價。由于個體的價值觀念和生活目標不同,同樣的生活手段和生活狀況會使不同的個體產生不同的滿意之感,幸福與否及程度大小有一定差別。
“盡管幸福使擁有幸福的人感到愉悅,但它本身并不是絕對的、全面的善;相反,它總是以合乎道德的行為為其前提條件。” [3]道德雖然不同于幸福,但是道德對幸福有著特殊的意義。道德的使命就是協調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確立一定的價值取向。因此,道德成為了人們追求幸福的社會條件,具有工具意義。幸福的實現以合乎道德為前提。道德是人類生活幸福的源泉,幸福就在人們習德、知德、行德的道德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