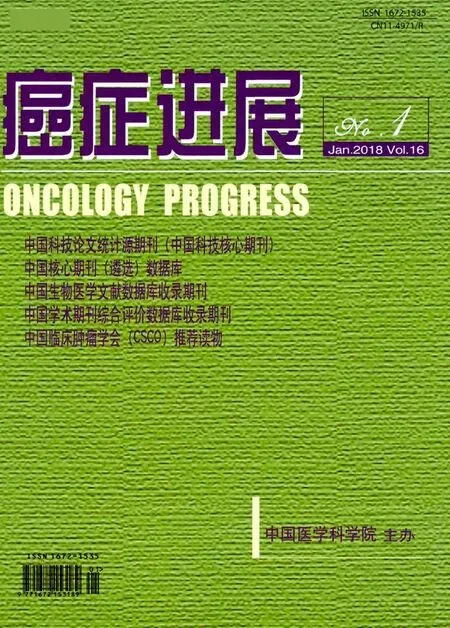吉非替尼致肝毒性后非小細胞肺癌1例并文獻復習
蔣梅,郭然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腫瘤中心一區,廣州5104050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58歲,于2015年1月因“活動后氣促”到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檢查胸部X線正位片提示:左側中量胸腔積液,詳見圖1。入院行胸腔穿刺置管引流術,共引流出血性胸腔積液約2400 ml,癥狀好轉后出院。胸膜活檢病理提示:中分化腺癌浸潤,考慮源于肺。確診為非小細胞肺癌。免疫組化標記:細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甲狀腺轉錄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間皮瘤相關抗原 MC(-)。胸部增強CT診斷:左側肺上葉前段周圍型肺癌且向左側胸膜轉移,左側胸腔積液,左側肺部散在多發小結節影。既往無肝炎病史和輸血史。血清肝炎病毒感染標志物均為陰性。

圖1 2015年 1月6日胸部 X線正位片
2015年4 月,患者再次因“活動后氣促”就診,檢查胸部X線片提示“左側大量胸腔積液”入院。行胸腔穿刺置管引流術,引出血性胸腔積液約2000 ml。行胸膜活檢組織基因檢測提示:EGFR基因突變,21號外顯子L858R錯義突變。患者于2015年4月7日開始口服吉非替尼,每次250 mg,qd。于5月6日檢測血清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由服藥前69.3 μg/L降至10.21 μg/L;同時檢查胸部CT,與4月CT比較,左側肺上葉前段主動脈弓旁見一結節狀軟組織影,呈淺分葉,較前稍減小,現腫物大小約為24 mm×16 mm×19 mm(原約為28 mm×21 mm×24 mm),左側胸腔積液明顯減少。血清谷草轉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為215 U/L,谷丙轉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為396 U/L,膽紅素系列正常,提示3級肝毒性(依據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通用毒性標準NCⅠ‐CTC 3.0版),囑停服吉非替尼,加服還原型谷胱甘肽片,每次400 mg,tid。
停服吉非替尼20 d后,患者血清AST和ALT恢復正常。患者于2015年5月26日再次口服吉非替尼,每次250 mg,qd。服藥1個半月,于7月7日復查血清AST為38 U/L,ALT為42 U/L,肝功能輕度損害;血清CEA水平繼續下降,至4.86 μg/L。7月8日復查胸部CT,與5月6日CT比較,左側肺上葉腫物減小,大小約為19 mm×17 mm×17 mm(原約為24 mm×16 mm×19 mm);左側胸膜厚度減小,左側斜裂胸膜處厚約為5 mm(原約為10 mm),左側肺胸膜和左側肺部散在多發小結節影減少。口服吉非替尼3個月后(中途因3級肝毒性停藥20 d),療效評價為部分緩解(依據實體瘤療效評價標準RECⅠST)。
繼續口服吉非替尼3個月,9月1日復查血清AST為83 U/L,ALT為126 U/L,肝功能2級損害;同時復查胸部CT,與7月8日CT比較,左側肺上葉腫物大小約為18 mm×15 mm×17 mm(原約為19 mm×17 mm×17 mm),左側胸膜多發局灶性增厚,與之前比較變化不明顯,詳見圖2。囑患者減少吉非替尼的劑量,隔日250 mg;2周后(9月14日)復查血清AST為87 U/L,ALT為117 U/L,仍為肝功能2級損害,未見改善,再次停服吉非替尼。

圖2 吉非替尼治療前后胸部CT比較
停藥1個月余,于11月4日復查血清AST為58 U/L,ALT為64 U/L,較停藥前有所恢復;但CEA為77.40 μg/L,明顯升高。11月4日復查胸部CT,與9月1日CT比較,左側肺上葉結節較前增大,呈淺分葉,見多發長毛刺,腫物大小約為21 mm×17 mm×23 mm(原約為18 mm×15 mm×17 mm),左側胸腔積液明顯增多。考慮口服吉非替尼近半年,療效為部分緩解,但因肝毒性已減量、停藥多次,病情進展,遂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行吉西他濱+順鉑方案化療4個療程,化療期間肝功能逐漸恢復。2月24日復查血清AST和ALT均在正常范圍;CEA降至5.03 μg/L;同時復查胸部CT,與2015年12月18日CT比較,左側肺上葉病灶變化不明顯,大小約為25 mm×15 mm×21 mm,左側胸腔積液減少。
3月3日,在局麻下行左側肺上葉腫物穿刺活檢+射頻消融術,檢查結果顯示,肺組織內見上皮異型增生,呈腺樣和乳頭狀結構,考慮“左肺”高分化腺癌。基因檢測結果仍為EGFR突變,21號外顯子L858R錯義突變。
消融術后1個月,復查血清CEA為5.99 μg/L。患者于4月8日開始口服埃克替尼,每次125 mg,tid,連續口服3個月余,每月復查肝功能均正常。7月19日復查血清CEA降至3.36 μg/L。7月21日復查胸部CT提示,左側肺上葉軟組織影呈消融術后改變,大小約為32 mm×30 mm×29 mm,左側胸腔積液少量。
囑患者繼續按照原劑量口服埃克替尼治療,每月復查肝功能均正常。9月18日復查胸部CT,與7月21日CT比較,左側肺上葉結節狀軟組織影縮小,大小約為30 mm×23 mm×28 mm(原約為32 mm×30 mm×29 mm),左側胸腔積液稍增多,詳見圖3。至此,患者已連續口服埃克替尼5個月,未見肝功能異常,腫瘤療效總體評價為穩定(依據實體瘤療效評價標準RECⅠST);按照ECOG評分標準,患者的體力狀況為1分,隨診中。

圖3 射頻消融術后,埃克替尼治療前后胸部CT比較
2 討論
對于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變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采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Ⅰ)靶向治療,可以明顯延長患者的生存期,目前報道的累計生存期已達3.5年[1]。
TKⅠ與傳統的細胞毒化療藥物顯著不同,被認為毒性極小,方便服用;然而,伴隨其在晚期NSCLC患者一線、二線以及維持治療中的廣泛應用,EGFR‐TKⅠ的新毒性也逐漸引起人們重視。多項Ⅲ/Ⅳ期臨床研究發現,一代EGFR‐TKⅠ(厄洛替尼和吉非替尼)的肝毒性發生較為常見,尤其是吉非替尼,在3級及以上的肝毒性發生率為1.0%~27.6%,明顯高于化療[2]。厄洛替尼所致的3級以上的肝損害發生率≤8.0%,低于吉非替尼,但仍明顯高于化療[3‐4]。多項病例報告顯示,晚期肺癌患者口服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療,可以導致重癥肝衰竭甚至死亡[5‐7]。這可能是源于化學結構和代謝途徑的差異,不同TKⅠ的肝毒性發生率存在差別。有研究顯示,吉非替尼組患者的肝毒性發生率明顯高于厄洛替尼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8]。有報道顯示,晚期NSCLC患者口服埃克替尼治療后,肝功能異常的發生率為7.4%,停藥并予以保肝治療后肝功能恢復正常,可以繼續口服埃克替尼治療[9]。
對于EGFR基因突變的NSCLC患者,一代TKⅠ獲益顯著,而二、三代TKⅠ如阿法替尼和AZD‐9291等價格昂貴,國內獲取途徑有限;因此,肝毒性停藥后治療策略的選擇十分重要。有報道稱,吉非替尼誘導肝毒性后成功轉換到厄洛替尼治療,可能是因為厄洛替尼對代謝酶CYP2D6和CYP3A5的敏感性弱于吉非替尼[10]。目前,EGFR‐TKⅠ停藥后再暴露僅見于病例報告,沒有大樣本的研究數據支持。
本病例的患者口服吉非替尼治療半年余,療效達部分緩解,控制胸積液效果明顯,但患者服藥1個月余出現3級血清轉氨酶升高,停藥2周余迅速恢復,提示:吉非替尼導致藥物性肝損害。考慮腫瘤治療的效果顯著,予再次用藥,同時加用還原性谷胱甘肽護肝治療,患者的耐受性尚可。3個月后患者逐漸出現輕、中度肝損害,降低吉非替尼的劑量2周后,未見緩解,予以停藥。
藥物性肝損害發生的機制復雜,主要與藥物的體內代謝方式及宿主的遺傳因素有關。多西他賽、吉西他濱、培美曲塞聯合鉑類的雙藥聯合化療方案被認為是治療晚期NSCLC的標準治療方案,但這3種治療方案的肝毒性比較,缺乏數據分析,僅從藥物動力學方面分析,多西他賽導致的肝毒性可能與抑制肝臟細胞色素P450酶活性有關[11],說明書注意事項中明確指出:血清轉氨酶[ALT和(或)AST]超過正常值上限1.5倍,同時伴有堿性磷酸酶超過正常值上限2.5倍,存在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高度危險……這些患者不應使用,并且在基線和每個化療周期前要檢測肝功能;吉西他濱在肝臟、腎臟、血液和其他組織中被胞苷脫氨酶快速代謝,給藥后一周內,吉西他濱給藥劑量的92%~98%被檢出,其中99%主要以dFdU形式經尿排泄,1%經糞便排泄;培美曲塞不經肝臟代謝,體外肝微粒體蛋白的研究結果顯示,培美曲塞未導致CYP3A酶、CYP2D6酶、CYP2C9酶和CYP1A2酶代謝的藥物清除率降低。推測對于曾經出現過藥物性肝損害的患者,培美曲塞、吉西他濱聯合鉑類的化療方案可能更安全。由于經濟原因,本病例選用了吉西他濱+順鉑方案化療,治療4個療程,肝功能逐漸恢復正常,腫瘤控制良好。肺腫物射頻消融后,患者按照埃克替尼的標準劑量口服5個月余,未見肝毒性,腫瘤療效評價為穩定。2015年4月至2016年9月,治療時間為17個月,患者的總體耐受性良好;按照ECOG評分標準,患者的體力狀況保持在0~1分。這提示吉非替尼導致肝毒性后,可以根據損傷程度采用停藥、減量和換用其他類型EGFR‐TKⅠ藥物,如厄羅替尼和埃克替尼等,吉西他濱+順鉑方案化療和局部消融治療也可以作為替代方案以贏得肝功能的恢復時間。本病例患者無病毒性肝炎和其他肝病病史,由吉非替尼導致的肝損害均可以恢復,提示選用吉非替尼治療時應該定期檢測肝功能,尤其是有基礎肝病的患者,應該及時發現,盡早預防,避免發展為重癥肝衰竭。
[1]Sholl LM,Aisner DL,Varella‐Garcia M,et al.Multi‐institu‐tional oncogenic driver mutation analysis in lung adenocar‐cinoma:the lung cancer uutation consortium experience[J].J Thorac Oncol,2015,10(5):768‐777.
[2]Mitsudomi T,Morita S,Yatabe Y,et al.Gefitinib versus cis‐platin plus docetaxel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harbouring mutations of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WJTOG3405):an open label,randomised phase 3 trial[J].Lancet Oncol,2010,11(2):121‐128.
[3]Zhou C,Wu YL,Chen G,et al.Erlotinib versus chemother‐apy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GFR mutation‐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OPTⅠMAL,CTONG‐0802):a multicentre,open‐label,randomised,phase 3 study[J].Lancet Oncol,2011,12(8):735‐742.
[4]Rosell R,Carcereny E,Gervais R,et al.Erlotinib versus standard chemotherapy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Europea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GFR mutation‐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EURTAC):a multicentre,open‐label,ran‐domised phase 3 trial[J].Lancet Oncol,2012,13(3):239‐246.
[5]Kim YH,Mio T,Mishima M.Gefitinib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J].Ⅰntern Med,2009,48(18):1677‐1679.
[6]Ramanarayanan J,Scarpace SL.Acute drug induced hepati‐tis due to erlotinib[J].JOP,2007,8(1):39‐43.
[7]Schacher‐Kaufmann S,Pless M.Acute fatal liver toxicity under erlotinib[J].Case Rep Oncol,2010,3(2):182‐188.
[8]Urata Y,Katakami N,Morita S,et al.Randomized phaseⅢstudy comparing gefitinib with erlotinib in patients with previously treated advanced lung adenocarcinoma:WJOG 5108L[J].J Clin Oncol,2016,34(27):3248‐3257.
[9]劉俊,王韡旻,潘峰,等.埃克替尼治療215例復治晚期非小細胞肺癌[J].腫瘤學雜志,2017,23(1):25‐29.
[10]Kitade H,Yamada T,Ⅰgarashi S,et al.Efficacy of low‐dose erlotinib against gefitinib‐induced hepatotoxicity in a patient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harboring EGFR muta‐tions[J].Gan To Kagaku Ryoho,2013,40(1):79‐81.
[11]周艷剛,劉朝敏,姜鶴群,等.多西紫杉醇致持續肝損害1例[J].四川醫學,2013,34(5):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