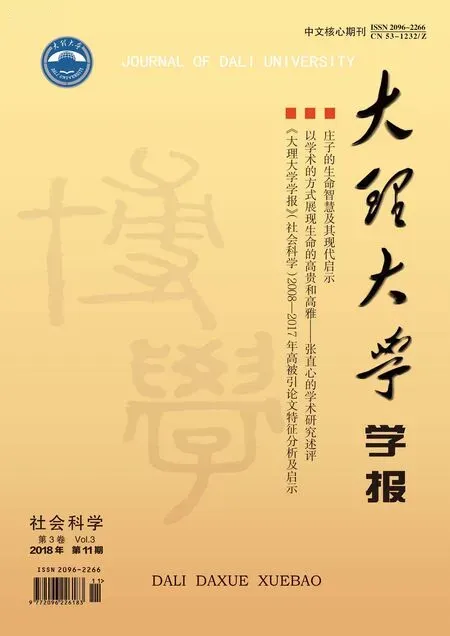道教書法藝術的特點與影響
張 梅
(湖北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武漢 430065)
“道教是以文字信仰為基干的宗教,所有宗教中,只有它與書法藝術有著本質上的類同性。”〔1〕340基于傳統天人之間通過神圣文字進行溝通的觀念①漢字創立之初便帶有宗教神秘意蘊,這從中國文字起源的傳說當中就可見一斑。伏羲畫卦之說揭示出象形文字同自然形象之間具有神秘關聯,倉頡造字之說揭示出構字的動機是為了同神靈有更有效的溝通,而且傳說中描述倉頡四目,顯示出了他有超乎尋常的洞察力,在造字之后有天雨栗鬼夜哭的異象,這更像說明他完成了一件宗教事業而不是世俗工具。,道教認為道經文字和符號不只是表意、象形、傳達信息的線條和空間組合體,還是含有神秘宗教意義的表現形式,具有象征性的意味在里面,這種象征的意味便是道教所要宣揚的理念。這一神秘化和神圣化的文字觀,乃道教書法產生與存在的理論來源與根據。
道教寫經與道教書符是道教書法的主要藝術形式。在與中國“特產”——書法的互動過程中,道教書法不僅擁有宗教實用功效,還獨具審美價值,成為中國傳統書法藝術中一種獨特而又重要的藝術形式。
一、道教書法藝術的主要形式
(一)道教寫經
借助于筆墨抄寫經書是道教經典口頭相傳之外的重要傳播方式。書寫道教經典不僅有保存、傳播重要書籍等實用意義,還是道教中人的一種必要修持,為“登真之徑路,出世之因緣”“生死之法橋”〔2〕24:749(文獻〔2〕為道教經籍的總籍《道藏》,“24:749”表示第24冊749頁,后同)。因此,道教鼓勵抄經,并對于寫經有著特殊的關照。
道教寫經嚴禁草書示人。“道學不得為草書”,“道學不得教人為草書”〔2〕25:153,道教要求所抄之經嚴肅、工整、易識,字體多為隸書、楷書,如陶弘景、王羲之、郗愔寫經均為隸書。道教認為,草書結構簡省、筆畫連綿,以這樣的書體上章拜表,不利于識別,且易造成脫落。《太微仙君功過格》云:“薦亡符簡文字等,一字差錯為一過,脫漏一字為一過。”〔2〕3:452道教寫經旨在借文字書法闡明教理教義,積累功德,由此草書不為道教所提倡。
道教寫經須遵循儀式軌則。經書的書寫是道教整體儀軌制度中的一環,或者說其本身就是一種儀式。道經書寫通過儀軌的渲染更能體現其權威性與神圣性。《傳授經戒儀注訣》中說:
徐覓能書,清嚴道士,敬信之人,別往靜謐,觸物精新,自就師請經卷,卷皆拜受,竟又拜送。恭肅兢兢,所受部屬,悉應寫之,皆用縑素抄之,則紙充乃應,師手書一通,以授弟子,弟子手書一通,以奉師宗。功既難就,或拙秉毫,許得雇借,精校分明,慎勿漏誤,誤則奪年籌,遭災禍,其罰深重,五校十校,講習相符,玄神祐人,延壽成圣,恩濟一切,非特己身。〔2〕32:171
作為道教師資授受的必備環節,寫經、傳授經戒必須是能書且戒律精嚴的道士,在清靜凈室內“恭肅兢兢”書寫才合符儀軌。書寫經籍完畢后要經過精心典校,否則徒增罪衍,而合乎法度的鈔寫,非但書寫者本人延壽成圣,還可澤及眾生。這種儀式性的要求普遍存在于道教寫經過程中。如《正一修真略儀》中就描述有更為嚴格的寫經儀軌。首先,書寫器具的購買過程“不得與人乖爭,言利宜之”,避免紛爭;其次,書寫者需要清凈心性,做到“情必虛懷潤物,清靜護慎,精意修理”〔2〕32:181,勿得穢雜雞犬異類,及婦人目視;預備寫經之前做到齋戒月余,之后于清靜凈室,東向開窗,焚香于左右,衣冠整潔;布置完畢之后,觀想師尊,調氣染筆,然后書寫,切忌牛皮膠,以免影響靈驗程度;抄經過后的紙張,用鹿角和乳頭香粘貼。至此,方才完成整個書寫過程。不合乎以上規范的寫經不具備宗教功用,因此抄寫經箓務必毫無茍且才合乎儀軌。
道教寫完經之后的裝幀以簡樸為主。《太霄瑯書瓊文帝章訣·書經決》強調:
首日軸帶,袟囊蘊巾帊廚箱,令堅完凈而已,不得過華。世間教化,化世舍華,華未能舍,權制用華,使世間人損俗華麗。華麗供法,漸識素方,得素后華,自然不壞。不求自得,不為自成,自然而然,莫能使之。不然緣素果此,勿滯俗華。臺堂行裝,各有豐儉,富貧相稱,不得強為。富者強陋,貧者強華,華奢陋儉,皆乖道制。〔2〕1:865
道教認為經籍隨力供養,不必過于奢華,關鍵在于尊奉精誠,精誠者必然成圣,與道合一。道教對于虔誠專注的要求貫穿于寫經前后的整個過程,可見道教對于寫經的重視程度。
(二)道教符箓
道教書法的另一種典型藝術形態為符箓。“符”是道教稱為天神的文字,筆畫曲折,似篆而非篆;“箓”是指天地鬼神及其官屬佐吏之名。“符箓”往往合稱,是道教的秘密文字,具有祛邪避災、消厄解困等神奇功效,乃道教重要的信仰表現形式之一。北周道安在《二教論》中概括道教內容時說:“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箓禁厭。”足見道符在初期道教中之地位。
符箓最早出現當推成于東漢的《太平經》卷一百四至一百七所載“復文”①“復文”系字與字組合而成,其中少數與漢字大致相同,多數是幾個漢字及其偏旁的重疊。如六個“天”字堆在一起,兩個“道”字和兩個“手”字疊在一起等等,形狀怪異,被稱為“太平復文”,共九五章。,“復文”是當時的符書,王育成認為:“當時制作道符的人是把組符的字作為表示符意的符號或者縮寫來使用的。這似乎和古文中的合文之意相去不遠。”〔3〕“復文”只是漢字變為道符的方式之一,后來被發展成為更龐大的系統。
符箓在演變的過程中,還有一種方式是借用筆劃的變形來完成。這種筆劃的變形也并非全無規則,而主要是依據道經中所提到的“龍鳳之章”“光明云篆”演化為彎曲如龍鳳或者云氣的形態。陶弘景《真誥》云:“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群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云篆、明光之章也。”〔2〕20:493《云笈七簽》卷七《符字》條記載符與書的關系云:“符者通取云物星辰之勢,書者別析音句銓量之旨,圖者畫取靈變之狀,然符中有書,參似圖像;書中有圖,形聲并用,固有八體六文,更相發顯。”〔2〕22:41道符與書法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字體上,道符模擬神龍云氣,因為神龍云氣場景往往伴隨神仙出現,而本身具有了神圣的意義。道符的筆劃用這些特別曲折的線條或者延伸為龍形波動,或者延伸為云狀盤卷,顯示其神秘與神圣性,由此也與日常書寫方式相比而具有自身的特殊形態,這也是道教書法特點最主要的體現。
畫符也要遵循一定的規則,否則便不靈驗。畫符最講究的是“確”與“巧”,“一字差錯為一過”,便要受到懲罰,“符文差錯脫漏為十過”〔2〕3:452,符亦不得靈驗了,所以必須“正心用之”。由此,書符者須得深諳道符之人且善書者。出于此種要求,書符不僅道教中人擅長,方外之士中善書之人也多有書符之事。米芾《畫史》云:“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卷,咒小字,五斗米道也。”〔4〕王獻之出生天師道世家,善書,書符有所本,當不誤。宋著名書家養欣亦“素好黃老,常自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5〕
二、道教書法藝術的創作特點
道教書法藝術屬于宗教藝術范疇,是體現與宣傳道教教理教義最為直觀的表現形式之一。出于宗教情感使然,道教書法表現出獨特的精神特征以及審美思維。修道的法門通過這些富有暗示隱喻性的藝術符號形式引導而獲得。
(一)大道無形:道教書法藝術本體
道教以“道”為一切事物的本源,是宇宙萬物的根本所在,“萬物含道精”,“道”在物之中。道教思想理論中涉及生命、天文、哲學、數術、文藝、政治、環境等,無不是圍繞著“道”為起點進行展開,并以此為標準的,認為人之任何行為和目的都要回歸到“道”的層面,進入一種與“道”合一的本原狀態,這樣才會將自己有限的生命和行為目的融化在虛無的“道”之中,無有窮盡。
“自然之道,顯示為道之文”〔1〕78,道教崇奉文字與經典,認為語言文字、符號本身是“道”的一種顯現與載體,乃“道”之精氣見諸于筆墨,人如果要窺探宇宙萬物之奧妙,必須經由道經文字。道教的一切修煉法門,幾乎都圍繞這個核心理念而展開。在宗教情感的熏陶之下,道教書法藝術的主旨在于合乎“道”。“道”是道教書法藝術的本體和審美體驗對象,同時也是道教書法的審美理想與目標。
陶弘景在《真誥》中對道教書法的主要特征描述為:“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空”和“無”是中國傳統書法表現的重要語言之一,陶弘景在此強調“空”“無”在書法中的體現,深層次的內涵實際上是指向了宇宙萬物的終極本體——“道”。“無”是道家道教之“道”的內涵之一,也是對“道”具有朦朧美感特征的描繪,正所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1:476大道空洞,其顯像便是文,道教書法以有形之點畫,有無相成的空間布局,表達了對“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6〕之“道”的神秘美感體驗。
道教書法藝術的核心追求——對于“道”的體驗也影響了方外文人書法創作理念。這是因為,藝術創作中的審美心理與宗教思維存在著某些方面的相似性,道教超功利的宗教化思維方式與非功利主義的藝術精神相通,因而容易深入書家之心,對書法理論和書法創作產生重要影響。
王羲之在《記白云先生書訣》中借用天臺紫真之口闡明其對于書法創作達到最高境界的認同標準,其謂:“天臺紫真謂予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7〕38“至美”的書法要求達到“至善”,“至善”之書必與“混元”相符。簡言之,作為物質形態的書法,審美須與宇宙萬物的本源相通。“混元”之理是宇宙萬物的生成運行之理,也即是道教之中所謂的“道”,“道”、技、藝統一方才為妙境。虞世南在《筆髓論》中亦說:“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學者心悟于至道,則書契于無為,茍涉浮華,終懵于斯理也。”〔7〕113這正是對宇宙之“道”的極高領悟。
(二)意到筆隨:道教書法創作技巧
道教修煉講究清心寡欲,物我兩忘,道教書法的創作前提與創作心態亦如此。
端靜凝攝是道教書法藝術創作和審美觀照過程所必備的心理前提,它不僅關系到創作主體修身養性的問題,同時也是書法藝術創作能否達到與“道”為一完美境界的關鍵步驟。
唐代道經《三洞神符記》中《書符記》對書符做出明確的規范,須“收視反聽,攝念存誠,心若太虛,內外貞白。元始即我,我即元始,意到運筆,一氣成符。若符中點畫微有不同,不必拘泥,貴乎信筆而成,心中得意妙處也。”〔2〕2:142道教書法創作必須保持內心清虛的狀態,不余雜物。《道法會元》卷四曰:“凡書符篆,先凝神定慮,物我兩忘,倏然間便見天真,即舉筆書符,使分清濁,見點點畫畫皆金光燦燦,舉念一間,神即往矣,何必待咒而行。”又曰:“凡書符皆須閉氣,一筆掃成。”“書符之法,不過發先天妙用,運一氣以成符,祖師所謂眼書云篆,心悟雷玄,初無存想,亦無作用,靈者自靈,不必問其所以靈;應者自應,不必問其所以應。人但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2〕28:674由此可見,道教書法創作的過程是對“道”或大自然精神品格理念的表現過程,簡言之是對“道”與“人”為一的精神境界的協調統一過程。這個協調統一過程的前提便是要保持“心齋”“坐忘”“面如死灰,心如槁木”的“忘我”“守一”狀態。此種“虛空”狀態下創作主體的精神不受外界干擾,處于一種自由無礙、物我兩忘的境界,在這種“乘物以游心”,“思與神會”,超然物外的境界中,藝術創作主體獲得了極其廣闊的藝術發揮空間,創作靈感迸發,奇特而瑰麗的想象由此而形成,這實際上就是對美的觀照。
“凝神定慮”“物我兩忘”不僅是道教重要的修煉觀,也普遍成為中國傳統書法藝術創作時的審美心理背景。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后》《書論》皆有言道:“夫欲書者,先于研磨,凝神靜思。”〔7〕26“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結思成矣。”〔7〕29王僧虔《筆意贊》云:“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以斯言之,豈是多得。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遺情,書筆相忘,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7〕62盛唐時張懷瓘《書斷》、孫過庭《書譜》、李嗣真《續書品》等書論中談論書法創作時出現與道教思想相關的守靜、內觀、沖虛等精神修養方式,這些都是對書畫創作時主體空虛清靜之“心意”重視的表現,從而提升了書、畫藝術創作中的審美境界。
(三)天書玄妙:道教書法審美追求
道教書法中符箓審美風格最為奇特,是道教書法美學風格的典型代表。書符不是主體對客觀對象“照相式”的反映,而是為了加強神秘感,對漢字作了大膽的變形,突破了字體筆劃的束縛,通過夸張的手法使字無正型,其趣宛奧,難可尋詳,表現出鮮明的夢幻特征。道符中包括有星象、云氣、畫像等元素,筆墨濃淡,線條流轉,富于想象變化,有繪畫般的審美意趣,但一般來說它的基本內容還是文字構建,通過文字點畫、構件的變形或者變位來形成新的組合。道符字體通常巨大,廣長一丈,給人以震懾感,由此道符整體風貌呈現出幽遠、神秘、崇高的宗教審美特征。
道教符箓屈折之筆畫組成的神秘難曉符號對一般人來說猶如天書,無法辨認,連宋代大書法家蘇軾也望字興嘆,他對道教方士之書評價“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明代陶宗儀也認為道教的書法“其書類飛白而不真,筆勢遒勁,莫能傳學。”道教符箓因為字不可識,才能比較集中地注意并欣賞其大膽而富有想象力的形式美。現代書法理論家熊秉明先生在其經典著作《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中評論道教書法時提到:“如果我們為道教書法找出一個主要特征來,那該是‘神異’或者‘神怪’,至少有一種神仙飄舉之氣。”〔8〕熊秉明先生說的主要是“道教書法”的風格,也即是諸如符箓之類的道教“專業”書法。
三、道教書法藝術的影響與成就
真經、道符多為道教所創立,由此道教中善書者眾多。書寫者在創作過程中將修道體驗到的宗教情緒、心境以及隱藏于自身的深厚文化修養通過筆墨線條進行自由表現,形成格調神韻各異的作品,豐富了傳統書法藝術的形式與內涵。
葛洪書法很有可觀,他所書“天臺之觀”飛白跡被北宋大書法家米芾稱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上清派創始人“三君”(楊羲、許謐、許翙)均是善書之人,楊羲書法最為工,能大能細,不今不古。許謐正書古拙,章草堪稱一絕。許翙師從楊羲,字體勁利,非人能及。茅山宗開創者、南朝書法鑒賞家陶弘景嘆“三君”手跡“非智藝所及”。北天師道寇謙之曾寫《嵩山靈廟碑》(公元456年),堪稱“六朝第一碑”,康有為贊之為“奇古”。陶弘景不僅是書法鑒賞家,也是書法高手,據《云笈七簽》卷一〇七,陶弘景從子翊撰《華陽陶隱居先生本起錄》云:“(陶弘景)善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家,骨體勁媚。”〔2〕22:732他以“媚”為書法審美標準,力主“手隨意運,筆與手會”的和諧美境界,書風獨具一格。陶弘景與梁武帝之間有多封討論古今書法的書函,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
另有道教經籍本身書風絕妙,成為后世書法名家傳承與臨摹的經典,如《黃庭經》《陰符經》《靈飛經》等,其中《黃庭經》地位尤殊。《黃庭經》為道教上清派經典,真跡早已不存,現存為后世臨摹本,相傳如王羲之、顏真卿、智永、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趙孟頫等均臨摹過《黃庭經》,以探究此書之妙境。清梁巘對相傳為書圣王羲之臨摹的《黃庭經》給予了很高的認可:“圓厚古茂,多似鐘繇,而又偏側取勢,以見風姿,而且極緊。”“結構之穩適,撇捺之斂放,至《黃庭》已登絕境,任后之窮書能事者,皆未能過。然極渾圓蒼勁,又及瀟灑生動。”清人包世臣《藝舟雙楫》稱《黃庭經》“筆力驚艷,能使點畫蕩漾空際,回互成趣”,又稱“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藩籬完固,有率然之勢。”通過這些文獻記載,從側面可見此道經書法造詣之高。
隨著道教的傳播以及文人雅士在道教書法領域的介入,道教“自然之道”“生命之道”“神仙之道”從不同層面啟發了藝術家們創作個性的覺醒,使得藝術審美和藝術創作從宗法倫理所劃定的狹隘范圍里解放出來,藝術創作開始追求審美境界的無限性,這一現象在漢魏六朝時期表現最為突出。
漢魏六朝時期的書法世家多天師道信仰世家,“道士集團與文士集團多所重疊”,如郗、王天師道信仰世家,書法大家頻出,郗儉及其兩子,書圣王羲之、王獻之、王凝之、王僧虔等皆是當時書法藝術創作領域中的領軍人物。王羲之最為世人所知曉和稱道的書跡有三,一為《蘭亭序》,一為《樂毅論》,其三便是《黃庭經》,另有寫《道德經》向山陰道士換鵝的韻事被傳為美談。李白《王右軍》一詩中稱贊王羲之寫經換鵝事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高平郗氏中的郗愔“性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隸書,與右軍相垺,自起寫道經,將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郗愔所書道經至六朝末還多有存者。另外王僧虔《論書》中云:“謝靜、謝敷并善寫經,亦人能境,居鐘毫之美,邁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在這些文化雅士書法創作的過程中,道教寫經書法突破了實用的觀念,從記文抄寫的工具變成了抒發自我的感情媒介。
道教畫符對后世的書法創作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道符與書法之關系主要體現在字體之上。道教寫經為求工整、嚴肅,多以楷書示人。道符突破文字的束縛,以豐富想象力進行書寫,或為變幻莫測之流云,或為天空之星象,這種千變萬化的體式與富有想象力的創作過程為后來的草書的演變帶來了重要的靈感。唐朝張旭信仰道教,性格疏放,乃“酒中八仙”,擅長草書,世人稱其為“草圣”。他的狂草一改“小草”的造型格局,“揮筆如流星”“落紙如煙云”“頹然天放,略點畫處,意態自足,號稱神逸。”張旭草書時而上下兩字筆畫相連看似一字,時而字里行間空白疏密相間,對比強烈,形成連綿回繞、氣勢奔放的藝術效果,千變萬化的體勢與道士所畫之符十分相似。張旭的“狂草”成為了草書史上繼張芝“大草”、王羲之“小草”之后的第三次變革。
“道教所關心的是,人的死亡問題,生命的安頓問題。為了安頓生命,貴生惡死,想出了尊奉真經、掌握真文,抄寫誦讀之,并上章釋表用符以祛病除魅。這些都不是為提倡書法而發,但其效果,則對書藝之發展甚有幫助。”〔1〕345道教書法風格既帶有宗教性又富于審美性,是宗教與藝術相融合所產生的文化碩果。這種宗教內容與藝術形式完美結合的特殊書法表現形式,在客觀上影響了傳統書法的藝術思維與觀念,豐富了傳統書法的藝術形式,推動了中國傳統書法藝術的發展,是研究道教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書法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