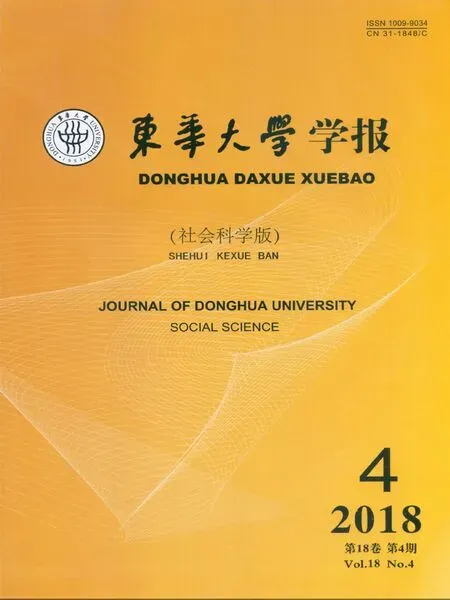試論夏曾佑、范文瀾宗教觀及其異同
江琪然,陸益軍
(東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20世紀初,由于西力東侵,中國傳統的社會觀念、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在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的雙重困境下,國家、政治、文化與宗教等問題備受知識分子關切。嚴復、康有為、蔡元培和梁啟超等人都曾積極參與宗教問題的探討。作為歷史學家,夏曾佑與范文瀾亦不例外,也對宗教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觀。目前學界對他們宗教觀的研究較為缺乏。本文擬對夏曾佑與范文瀾的宗教觀進行比較,以探究那一代知識分子在特定的歷史際遇下對宗教的思考及對其未來走向的艱難求索。
一、 夏曾佑、范文瀾之宗教觀概述
在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的雙重困境下,夏曾佑、范文瀾對宗教問題的深思,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留下了絢麗的一頁。由于社會背景和人生閱歷的差異,他們在宗教問題上的認識有著較大的不同,深刻反映出特定時代下知識分子對待宗教問題的復雜心態。
夏曾佑(1863—1924)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學者和思想家。他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與嚴復一同創辦《國聞報》宣傳維新思想,對晚清思想、文學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梁啟超在《亡友夏穂卿先生》一文中稱他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是其“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1]。他撰著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即《中國古代史》),嚴復稱之為“曠世之作”。此書多次再版,對錢穆、顧頡剛等都有很大的啟發。同時夏曾佑還精通佛學,致力于佛學濟世;他十分關注宗教的發展歷史,將宗教與政治結合,以“政教”為核心來探究國家和民族興亡的演變。
夏曾佑認為人類歷史與宗教關系密切,在撰寫《中國古代史》之前,他就對中國古代歷史演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中國政教,先秦是一大關鍵。“先秦以后,方有史冊可憑;先秦以前,所傳五帝三王之道與事,但有教門之書,絕無國家之史。”[2]在《中國古代史》中,他認為,歷史上幾乎沒有一件事不與宗教相關,尤其是古史,人類最初的歷史即為宗教的歷史。人類的起源有各種不同的見解,一般可分為兩派,一派為宗教家,另一派為生物學家。宗教家在討論人類起源問題時,都以本教最古老的教文為憑證,“詳天地剖判之形,元祖降生之事。”[3]中國也不例外。以前的學者多以宗教解釋古史,如今的學者則以宗教考察古史。
夏曾佑認為“宗教”和“政治”相互為用。他在1904年發表的《書本報所紀法國禁約教會事后》一文中說:“國之政術,常依附于其教”“政之所以能久存者,必與其國之宗教相附麗。”[4]在他看來,宗教和國家、宗教與政治都是相互依存的,宗教對于國家興亡和政治穩定影響十分深遠。他悉心研究世界其他民族的歷史,尤其是歐洲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在為嚴復翻譯的《社會通詮》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宗教和政治必須相互依附,這樣二者才能久存于世。古時歷來改朝換代都會有新宗教與新政權為伴,后者想要撼動前代政權也是先從撼動宗教著手,從來未出現舊宗教還未分裂新政權就產生的現象。宗法是政事的始基。夏曾佑認為人類社會都經歷過宗法階段。歐洲進入宗法社會是最遲的,從中脫胎也是最早的,這是因為他們的宗教和政治較為疏遠。中國很早就進入了宗法社會,“而其出也歷五六千年,望之且未有崖,則以宗教之與政治附麗密也”。[5]通過對中國和世界各國歷史的比較,他深刻闡述了宗教及其發展對世界各國歷史文明進程的極其重要的影響。
夏曾佑重視“政教”,進而提出了“革政”“改教”,這是辛亥革命前中國飽受列強侵略、民族危機空前之時,先進知識分子要求政治和文化變革的現實反映。他認為,“孔子之術”目的在于鞏固君權,走的是宗法這條路徑,所以向來都是以宗法定君權。“宗法者,凡百政事之始基也。”[6]既然政治和宗教密不可分,“革政”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討論“改教”了。
總而言之,在夏曾佑看來,“教”與“政”是密不可分的,正因如此,他在撰寫《中國古代史》時,始終以“政教”為核心貫穿全書,探究國家與民族興亡演變之因果。
范文瀾(1893—1969)是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早年精研國學,在北京大學求學時,師從古文經學學者陳漢章、劉師培,深受訓詁學家黃侃的影響,奠定了深厚的國學根基。1925年,范文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心雕龍講疏》。此后,又相繼出版了《水經注寫景文鈔》(1929年)、《正史考略》(1931年)、《群經概論》(1937年)等著作。大學畢業后,范文瀾因在混亂現實中苦尋出路無果,成了一位“佛迷”,一頭栽進了佛經中,潛心研究佛學以尋求慰藉。隨著時代潮流的涌動和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的傳播,范文瀾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開始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轉型。
范文瀾深知迷信思想對人們心靈的侵蝕毒害,對于歷史上佛教及其他宗教進行了深刻揭露和嚴厲批判。他曾在《唐代佛教》一書引言中,揭露佛教在唐朝的所作所為,指出:“佛教擺出一副離塵出世(超階級)的假面孔,實行階級欺騙以達到階級壓迫、剝削的真目的,它騙人的根本方法是高唱苦、滅(空)二諦。”[7]他列舉了佛教的三大禍害:第一,寺廟林立,宣揚迷信;第二,多立宗派,廣收徒眾;第三,麻痹農民,阻礙起義。他認為佛教阻礙了社會發展,尤其有“辭而辟之”的必要。
范文瀾對宗教的批判不僅限于佛教,更將鋒芒指向道教。他批判創立于東漢后期的道教“集中國傳統的鬼神迷信貪污淫穢一切黑暗卑劣思想的大成,再加佛教虛幻妄誕的騙人新法,造成中國獨有的宗教”[8],并斥之為“最下流污賤的宗教”[9]。
范文瀾對佛教及其他宗教進行的分析和批判,顯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批判佛教的同時并沒有完全否定佛教。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中,他詳細論述了佛教對中國文學和藝術的影響,指出:“佛教是中國文化重要的構成部分。”[10]
二、 共通之處:宗教的產生、作用及其與國家、政治的關系
夏曾佑、范文瀾所處的時代與學術背景不同,人生閱歷、思維方式也存在較大差異,這使他們對宗教的見解相去甚遠。盡管如此,他們的宗教觀仍存在一定的共通之處,那就是關于宗教的產生、作用及其與國家、政治的密切關系。
夏曾佑認為宗教的產生是因為遠古人們無法解釋“日月升沉、寒暑更迭”等自然現象,因而對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產生了敬畏心理,以為這個世界除了人以外,還有其他靈體存在,鬼神之說由此而生。這種由鬼神之說而來的宗教思想,不僅在中國社會迭代相傳,外國社會也同樣如此。在《中國古代史》“孔子以前之宗教”一節中,他就談到了這一點。既然鬼神魂魄為常人無法理解,那么就會有“豪杰”出世,宣稱能“明鬼神之情狀,辨魂魄之行受,闡上帝之意旨”[11],將其闡釋視為天神的安排而向民眾傳授,于是就產生了“教”。創教者被稱為“圣”,紀教之書稱為“經”,文之于事謂之“典禮”。天下民眾,言行若是合乎教旨,就可稱為“善”“賢智”;若是違背了教旨,那就是犯了惡行,愚昧不肖。“教”為善民創造一種樂境以樂之,對于惡民則設立一種苦境以苦之。是非標準既定,政體既立,統治民眾就有了保障。“豪杰”創教之后,教義便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民眾言行要合乎教義以獲安寧,否則將招來苦難。如此,宗教就成為一種精神信仰寄托存于民眾心靈中。
同時,宗教又與統治者維護政治穩定有密切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史》的“黃帝之政教”一節中,夏曾佑指出歷來種族之間發生沖突,一族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后,為了社會穩定,必定會創立一種宗教,目的是以宗教揭示人“所生不同,本非同類,原無平等之義”[12],如此一來宗教就成為統治者用來套牢民眾的工具。
范文瀾也認為宗教的產生和發展與統治者維護政權關系密切。他在《唐代佛教》引言中指出: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那時候正值農民起義爆發前夕;東漢、三國一直到隋朝,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異常激烈,統治階級迫切需要維護政權穩定,于是佛教就在這種機遇下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提倡,并在中國發展起來。他舉唐玄宗為例,說:“他知道宗教都是有用的工具,無論是土產的還是外來的宗教,他都一概歡迎,尤其是傳播已久的佛教,他認為‘玄妙可師’”[13],這樣隋朝大力提倡的佛教,在唐朝時得到統治階級更大范圍的推廣。
在范文瀾看來,一方面自從階級社會誕生以來,因統治階級剝削的需要,包括佛教在內的所有宗教都被制造加工出來,另一方面宗教又憑借著自身的欺騙作用,在社會土壤中扎根。只要剝削制度依舊存在,宗教是不會消滅的。即使剝削制度消滅了,宗教也不會自動消滅,因為宗教在被剝削階級中已經深深扎根了。即使剝削階級消滅了,平民翻身了,在一段時期內仍會有習慣勢力存在。習慣勢力存在,宗教就可以依附而茍延殘喘,甚至對國家、政治繼續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 難以彌縫的差異:宗教的涵義與價值判斷
夏曾佑和范文瀾的宗教觀,雖然在以上方面存在共通之處,但是彼此之間的差異還是相當明顯的,甚至難以彌縫,主要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 關于宗教的涵義
1. 宗教的范疇
夏曾佑總是圍繞兩個方面來思考宗教問題:一是“教”和“種”之關系,二是“宗教熏染”與“外族逼處”的關系。在他看來,“案人類至大之端有二,一曰種,一曰教,而二者常相需”。[14]“教”與“種”之間是相輔相成的,“教”定而后“種”定,反之亦然。而“宗教熏染”與“外族逼處”則是國家成立與發展的重要原因。夏曾佑認為,漢代以前,中國種族和宗教較為單一,自漢朝開疆辟土后,中國漸漸發展成為大國,種族也隨之交融復雜起來,伴隨著種族趨于復雜的還有中國的宗教。在夏曾佑的論著中,“教”和“宗教”的范疇極其廣泛,不僅指佛教、基督教這類外來宗教,也包括儒、道等諸子學說以及鬼神術數、原始信仰,其中夾雜著與種族相關的政教、學術和風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從中可以看出,夏曾佑認為中國宗教與西方宗教明顯不同,中國宗教有其獨特的內涵、形式、價值和功能。
范文瀾認為宗教是一種封建迷信,是唯心主義的思想。他將宗教視為剝削階級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宗教的主要功用則是宣揚統治階級思想,迷惑勞動人民。而他在其著作中所論及的宗教僅包括佛教、基督教等一些外來宗教及巫教、缽教、道教這類自創的本土宗教。
2. 儒學和陰陽五行是否為宗教
前面提到夏曾佑的思想中,儒學也被歸為宗教。在《中國古代史》的“孔子以前之宗教”一節中,夏曾佑認為孔子是“中國政教之原”,中國的歷史即為孔子一人之歷史,而中國兩千年政教,實為孔子一人之宗教,由此可見孔子對中國政教的影響極其深遠。他在“戰國之變古”一節中論及宗教改革,認為“此為社會進化之起源,即孔、老、墨三大宗是也”。[15]在夏曾佑看來,儒教、道教、墨家、佛教四大宗教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后隨著政權更替和社會形勢的變化發展,儒教逐漸發展成國教,道教無真傳,墨家消亡,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后,因兼道家和墨家之長而各去其短,盛行于中國。但是對中國政教影響最大者,他認為還屬孔子創立的儒教。夏曾佑對孔子以前的宗教進行了深入的考察,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鬼神五行之說的存在,各種巫史卜祝據此推測世事,沿襲下來成為宗教學問之根本。中國的宗教歷史悠久,陰陽五行也屬于宗教,且遠在孔教之前就已經存在。
范文瀾卻認為儒學與陰陽五行并非宗教,他在《中國通史》第二冊第二編第三章“經學、哲學、科學、宗教”一節中作了詳盡的論述。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雖然有眾多外來宗教的傳入和佛教的盛行,但是其中沒有哪一個宗教取得過獨尊的地位,它們都沒有在中國扎根,這是因為有中國史官文化的存在,而儒學正是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體。范文瀾認為,“宗教得以興盛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對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絕對信仰”,但是儒學對鬼神始終保持懷疑,不談鬼神與死后之事,敬而遠之,所以在儒家學說的思想體系中,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導地位,這也是儒學不會成為宗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史官文化的哲學來源,一是夏、商五行論,二是周朝陰陽論,二者本質上都屬于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是哲學而非宗教。戰國時鄒衍將陰陽和五行兩種思想合為陰陽五行學說,用“德”(五行的性)作本體,“運”(陰陽變化)為作用,以“德”“運”為出發點來推測自然與社會的命數,原本屬唯物論的陰陽論、五行論被鄒衍改造成唯心論的陰陽五行學說,但其本質仍屬哲學而非宗教。
(二) 對待佛教的態度
夏曾佑精研佛學,是清末著名的佛學居士。陳業東教授在《夏曾佑研究》中說:“甲午至戊戌年間,維新派知識分子把佛學與社會政治改革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他們往往寓政于佛、借佛談政。”[16]夏曾佑之所以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研究佛學,不僅是對佛經教義作闡釋,也非真正想要追求超脫塵俗,而是因為在他看來“宗教之理”未明是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今我中國,其腐敗至于此極,無論行新法、行舊法,無不可見其腐敗之情,識者皆知為人心使然。若人心不變,則萬事皆不可為,然世間萬物,有何物能改革人心者乎?則宗教而外,更無別物矣。”[17]他欲以佛法濟世,借宗教之手規劃政治藍圖,宗教成為變法改制最有力的思想理論武器。夏曾佑將佛教當作革命保國的一種有力武器,談佛是為了救國,對于佛教持肯定態度。
范文瀾對佛教等宗教思想始終持批判的態度,他說若能因評佛教而對其他各宗教有所批判,可謂是為反對唯心主義做了一些工作。在他看來,佛教在中國盛行,長期肆虐,造成了嚴重的禍害。佛教總是自詡離塵出世,擺著一副超階級的假面孔,實則是進行階級欺騙以達到階級壓迫、剝削的真正目的。他在《中國通史》第三冊第三編第七章“唐五代的文化概況”中,專設“佛教各宗派”和“禪宗——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兩節,又在《唐代佛教》引言中,以大量的史實對佛教禍國殃民的罪惡實質作了徹底的披露。盡管范文瀾也肯定佛教在藝術領域內曾作出的成績,但是他認為佛教利用藝術做販毒廣告,藝術性越高,流毒越廣。雖然有必要對佛教藝術進行保護,但是更有必要指出佛教的毒害性。由此可見,范文瀾對佛教始終持嚴厲批判態度,認為佛教屬宗教迷信思想,應當對其禍害進行批判揭露,用科學文明戰勝迷信愚昧。
作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夏曾佑深入探察中國歷史,同時與其他民族歷史進行比較和對照,從中挖掘出中國宗教中的變革因素,企圖以宗教為變法改制之武器,移風易俗,扭轉中國社會頹廢的風氣,救國保民。他堅持以佛法濟世,這是受當時維新變法社會背景影響,是先進知識分子在動蕩的社會中謀求政治思想變革的現實反映,盡管這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范文瀾看來,宗教盛行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巨大阻力,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宗教進行嚴厲批判,體現出了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綜觀夏曾佑和范文瀾二人對宗教的思考,他們對宗教問題的復雜心態,不論是肯定還是否定,充分展現了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知識分子對社會、人生的深切關注和理性思索。他們的宗教觀,對我們當下如何看待宗教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值得認真探討與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