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布”被誤讀為“郢爰”之考辨
文_韓書茂
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安徽省書法家協(xié)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淮南市委黨校中文副教授
“郢布”是戰(zhàn)國中晚期楚國鑄行的一種方形金幣,整版澆鑄,冷卻前鈐蓋方形白文印“郢布”二字,用大型剪刀按所需裁剪成小塊,稱量使用。楚國春秋時為“五霸”之一,戰(zhàn)國時曾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紀南城)。公元前278年,敗于秦,郢失守,遂遷都于陳(今河南淮陽)。在陳時,鑄行金幣“陳布”。公元前241年再遷都壽春(今安徽淮南壽縣)。現(xiàn)在所見“郢布”“陳布”方形金幣多出土于壽縣和河南境內(nèi)。
20世紀以來,錢幣界在“郢布”的釋讀上多有爭議,以釋讀“郢爰”“郢爯”者居多。但對其意義的解讀都莫衷一是,無法自圓其說。“郢布”說為筆者新讀。今從形、義兩個方面,對“郢布”“郢爰”“郢爯”三者考辨如次。
一、“郢布”(圖1)

圖1

圖2

圖3

圖4
甲骨文中無“布”字,戰(zhàn)國諸簡中有“布”的多種寫法。

圖5
“布”字(圖2、圖3、圖4),為會意字,上部為“手”,下部為“空首布”輪廓形的線化(圖5) 。意為以手持布進行交易。《詩經(jīng)·國風·衛(wèi)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mào)絲。”意即用布去購買絲,布是用來交易的貨幣。古人更進一步將“布”與“泉”的貨幣功能區(qū)分為:行之為“布”,藏之為“泉”。因此,“郢布”的正確釋讀應為:楚國都城“郢”鑄行的金幣。
二、“郢爰”

圖6

圖7

圖8

圖9
爰,甲骨文如圖6,金文如圖7,戰(zhàn)國竹簡如圖8、圖9,會意字,雙手持一長桿,夠取想要得到的物件,意為于、及。《盤庚》:“乃正厥位,綏爰有眾。”爰字后來加上提手旁,作“援”,仍保留了借助他物,以實現(xiàn)所要獲取的物品和目的的含義,如援助、支援。由此可見,“爰”字從字形和意義兩方面都與錢幣無關,將“郢布”釋讀為“郢爰”無法成立。

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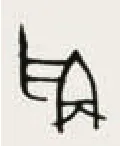
圖11
三、“郢爯”
爯,甲骨文如圖10,金文如圖11,會意字,上部為“手”,下部為“角”,角為古代量器。《管子·七法》:“尺寸也,繩墨也,……角量也。”以手持角,意為稱量。“爯”通“稱”(稱為“稱”的繁體字),《禮·月令》:“蠶事既登,……稱絲效功。”稱,又作衣物的量詞。《禮·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可見,爯從字形和字義上看,亦與錢幣無關。值得提出的是,《古文字類編》(高明、涂白奎編著)“爯”字條下,收錄了一個戰(zhàn)國簡中的(圖12),這個字與“郢布”中的“布”寫法相同,應列在“布”字條下。《編》將其列在“爯”字條下,顯然是采用了“郢爯”說,而“郢爯”說是錯誤的。“爯”的下部的“角”,后來楷化并省略為“冉”,但絕不可能楷化和省略為“巾”。

圖12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布、爰、爯三個字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與“手”有關。又都有一個不同點,就是所持之物分別為空首布、長桿、角。三個字之間,只有布與錢幣有關,而爰、爯與錢幣無關。
國之重器“后母戊鼎”,百年來一直被誤讀為“司母戊鼎”,其錯誤不在字形,而在字義的解讀。“后”是王后,“司”是職官,身份懸殊,豈能混淆。盛世中國,今天我們進行學術研究的條件較之前人要優(yōu)越得多,我們完全可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把過去的錯誤更正過來。將“郢布”的釋讀正本清源,是錢幣學研究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必然選擇。
注:文中引用的古文字均出自《古文字類編》(高明、涂白奎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