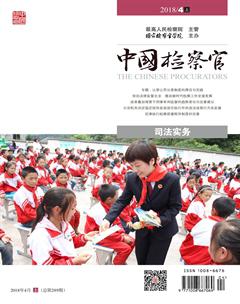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演進之治理路徑
吳中堯
摘 要: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經歷從“嚴”到“寬”的過程,其演進根植于“仁政”、“中庸”等傳統文化土壤并吸收接納國際刑事司法主流思潮和社會治理理念,價值導向逐漸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禁化及社會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治理之路應當重視微觀層面的治理工具,以實現“政府與社會共治”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新格局。
關鍵詞: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演進 治理路徑
現階段,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導向是“寬嚴相濟,以寬為先”。這個政策既源于傳統的“仁政”、“中庸”思想,又順應國際上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和恢復性司法的主要潮流,也契合了我國治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實際情況,因此,具有堅實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基礎。但是,隨著近些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人數逐年增多、犯罪低齡化問題日益突出,法學界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分歧,有的繼續主張“寬主嚴輔”、“當寬則寬、當嚴則嚴”,有的主張“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惡意補足年齡(malice supplies the age)原則”。本文認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低齡化問題雖然是刑事司法政策的問題,但是根子卻在社會治理上。習近平強調,要“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這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演進指明了方向。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發展歷程
從1979年8月17日中央轉發《關于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報告》提出“教育、挽救、改造”方針開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演進大致經歷確立完善和精細發展兩個階段。
199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和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教育、挽救、改造”方針的基礎上提出“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此為指導開始探索建立少年司法制度,初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偵查、檢察、審判和社區矯正制度。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作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化、非刑罰化、刑罰個別化和緩刑適用等規定,并在2006年《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補充規定未成年人犯罪在財產刑、減刑、假釋適用上的放寬條件和標準。同年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首次提出未成年人特殊和優先保護原則。200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依法從寬處理并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辦案方式。至此,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寬嚴相濟,以寬為先”的刑事司法政策基本確立并在總體框架上逐步完善。
2008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兩擴大、兩減少”[2]的方略,法學界隨之探討未成年人從寬處理、前科消滅、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禁化等前沿問題,并促成《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未成年人犯罪不構成累犯、未成年人有條件前科消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程序等的規定。由此,未成年人犯罪“寬嚴相濟,以寬為先”刑事司法政策的開始向縱深化、精細化發展。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寬嚴相濟,以寬為先”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首先是傳統的“仁政”、“中庸”思想。我國是一個十分注重文化傳承的文明古國,任何脫離傳統的變革都將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演進也是如此。其次是國際刑事司法主流思潮,包括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和恢復性司法,等等。最后是全球治理浪潮及治理理論。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路徑選擇
從發展歷程來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在“寬嚴相濟”的總體框架下,大致經歷了“偏嚴”→“寬嚴相符”→“以寬為主”的過程;從理論依據來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寬嚴相濟,以寬為先”的刑事司法政策根植于“仁政”特別是“中庸”等傳統文化土壤中,博采國際刑事司法主流思潮的精華,吸納全球治理的理念,價值導向逐漸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禁化及社會化。由此,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演進——治理路徑。
(一)“寬”、“嚴”之爭的局限
在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演進過程中,始終存在“寬”、“嚴”之爭,早期是“教育、挽救、改造”與“嚴厲打擊”,后期是“兩擴大、兩減少”與“惡意補足年齡”。其中,惡意補足年齡原則在理論和實務屆頗有影響力。
惡意補足年齡原則最早由英國法學家威廉·布雷克司頓在《英國法釋義》中提出,之后逐漸成為英美國家判定處于一定年齡段的低齡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一套規則。布雷克司頓認為,完全按照年齡劃分刑事責任歸屬仍過于機械,畢竟現實生活中總有部分未成年人較其同齡人早熟,對這些人的處分照搬刑事責任年齡顯然不合時宜。因此,雖然處于一定年齡段的未成年人被推定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但若控方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該未成年人在行為實施時具有主觀惡意,能夠辨別是非、善惡卻執意觸法,則可以推翻其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推定并使其對實施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惡意補足年齡原則以“有充足證據表明未成年人主觀惡意已能夠使其區分對錯而又執意觸法”這一主觀判斷為標準,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同時強調對于刑事責任年齡起點以下的未成年人予以追責,本質上是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觀點。
實際上,無論是持“惡意補足年齡”“嚴”的觀點,還是持“輕刑化”、“從寬處理”“寬”的觀點,[3]都認為未成年犯罪人有罪、有主觀惡意,都忽視了社會責任和未成年人法益特殊性,它們的區別在于刑罰是“嚴”或“寬”、未成年人主觀惡意是大或小,它們都有著共同的局限性,即沒有從社會責任入手、尋找社會共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方略。
(二)當前社會治理措施的缺陷
從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點和法益特殊性來看,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監禁、社區矯正、前科消滅等措施都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之所以出現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增多、低齡化的問題,主要原因在于兩方面:
其一,社會治理措施的更新速度跟不上社會發展、結構變化的速度,以遲滯的治理方式應對急速變化的社會,自然會減效、失效。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不能僵化地存在,政策需要依據社會情況的變化靈活應對。司法機關擅長的領域是懲戒、刑罰、監禁,社會擅長的領域是教育、矯正和回歸。司法機關以法律賦予的有限權力去從事并不擅長的領域,是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4]還是需要發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以符合未成年人成長規律的方式來治理未成年人犯罪。
其二,治理在資源投入方面不足、資源配置方面不合理,尤其是具體技術和方法缺少科學性和精確性,以粗范的技術手段應對復雜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當然會捉襟見肘。我國《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原則性的規定“針對未成年人的年齡、心理特點和身心發育需要等特殊情況,采取有益于其身心健康發展的監督管理措施;采用易為未成年人接受的方式,開展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輔導”,并沒有規范地確定具體的矯正方案和程序。各地推行的社區服務令、社會幫教、社會調查、心理輔導等制度還處于探索階段,在科學性、精確性和規范性方面差異較大,反映的效果也不一樣。另外,資金投入和人員配置也在探索和調整中,擅長未成年心理和幫教的專業人士比較缺乏。因此,社會治理領域的未成年人工作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三)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微觀工具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項復雜的社會性工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發展不能局限于“寬”、“嚴”相濟的宏觀層面,也不能滿足于推行“社區矯正”、“恢復性司法”的中觀層面,還應該重視微觀治理工具的應用,這些微觀工具有:
第一,社區服務令,指的是對實施了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可不予以關押,而是將其置于社區之中,在特定委員會的監管下,要求未成年人必須完成一定的勞動或社區工作的一種處罰方式。
第二,社會幫教,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和學校、城市居民委員會、農村居民委員會、對因不滿16周歲而不予刑事處罰、免于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或者被判處非監禁刑罰、被判處刑罰宣告緩刑、被假釋的未成年人,應當采取有效的幫教措施,協助司法機關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第三,社會調查,也稱品格調查、量刑調查報告等,即對犯罪人的性格、特點、家庭環境、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犯罪行為特征、事后表現等進行全方位的社會調查,最終對其人身危險性和責任程度進行評估,以此作為法院實施個別化處遇的參考。包括調查主體、調查啟動時間、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應否進入定罪階段等。
第四,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檔案庫(網),各轄區通過檔案庫靈活管理不同社區進行矯正的未成年人,改善目前的松散管理模式并實現“異地監管”。
第五,矯正方案調整,未成年人在某一矯正環節中如果表現良好,可以在該環節期滿前開展新的矯正環節或者根據未成年人回歸社會的現實需求,在完成前期矯正后,為其補充開展實際能力的訓練。反之,如果未成年人屢教不改、抗拒矯正,應該調整矯正方案,延長環節時間或者更換操作方法。
細節決定品質、細節決定成敗,微觀治理工具的應用和發展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走向。
總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在于使其回歸社會、恢復社會秩序,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應該在治理領域拓展,以實現“政府與社會共治”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新格局。
注釋:
[1]習近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2]具體是指:對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老年犯中一些罪行輕微的人員,依法減少判刑、擴大非罪處理;非判刑不可的,依法減少監禁刑、擴大適用非監禁刑和緩刑。
[3]在“寬”的觀點中,非刑罰化、非監禁化與輕刑化在觀念上是有區別的。
[4]司法實務中,檢察機關公訴人一般不愿意從事未成年檢察工作,原因很簡單,即讓習慣搜集證據定罪的人去搜集證據脫罪,在觀念和工作方式上沖突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