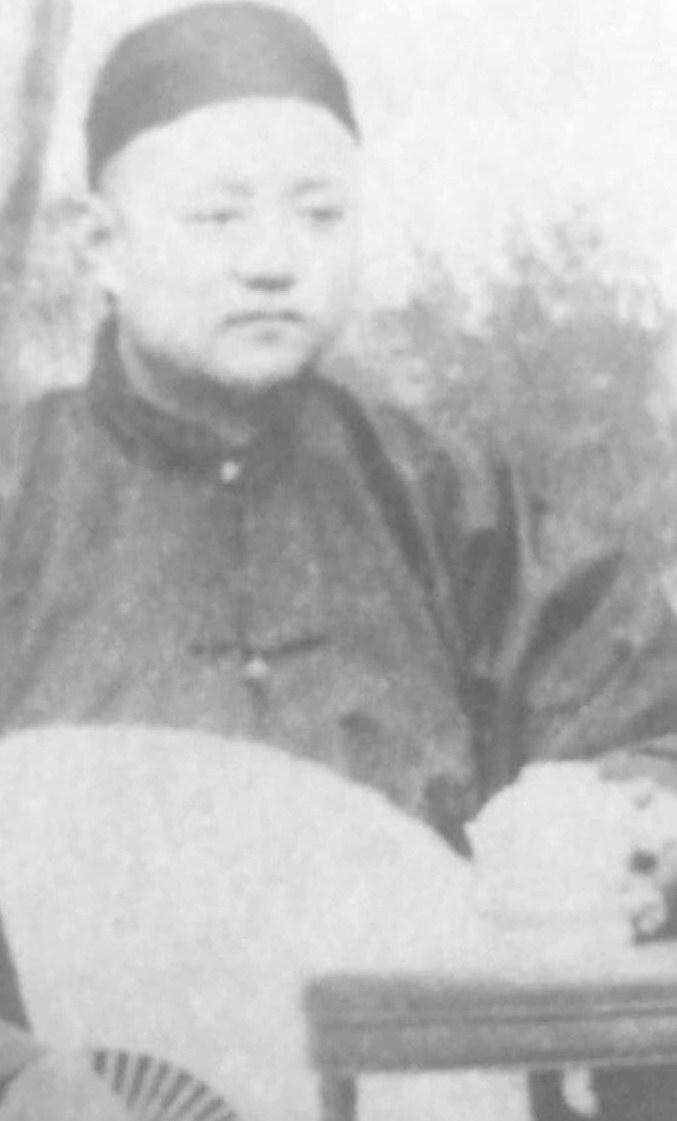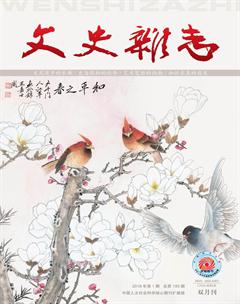榆次常家的“知恥”女子學(xué)堂
黃志娟
榆次車輞常氏,從清康熙年間以商起家,經(jīng)乾隆到宣統(tǒng),以茶為主開(kāi)展對(duì)俄貿(mào)易,歷經(jīng)200余年,成為“外貿(mào)世家”。其家族不僅重商業(yè),而且重文化,發(fā)展教育,創(chuàng)辦學(xué)堂,在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常氏各門共辦私塾17所,開(kāi)創(chuàng)了全省一個(gè)家族辦學(xué)最多的紀(jì)錄。1904年秋,常氏興辦的——“知恥”女子學(xué)堂,開(kāi)創(chuàng)了三晉辦女子學(xué)堂的先河。
“知恥”女子學(xué)堂的創(chuàng)辦背景
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觀念中認(rèn)為“女子無(wú)才便是德”,在“三從四德”婦德觀的束縛下,女子教育歷來(lái)為人忽視。即便是少數(shù)官宦家族的女子也僅僅以《孝經(jīng)》《烈女傳》《女訓(xùn)》《女誡》為主,女子像男子一樣去學(xué)堂接受教育幾乎不可能,國(guó)內(nèi)無(wú)正式女學(xué)。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隨著香港割讓,五口開(kāi)埠通商,大批外國(guó)傳教士入華,他們?cè)趥鹘痰耐瑫r(shí),著手創(chuàng)建各類教會(huì)學(xué)校,于是教會(huì)女學(xué)隨即出現(xiàn)。光緒初年發(fā)生的一場(chǎng)旱災(zāi)即“丁戊奇荒”,在這次災(zāi)荒的救濟(jì)中,西方教會(huì)通過(guò)賑災(zāi)的形式進(jìn)入山西。1878年,內(nèi)地會(huì)的女教士戴德生夫人、霍恩、克里克梅于太原賑災(zāi)時(shí)救助了一些女孤兒,為安置她們開(kāi)辦了一所學(xué)校。這是基督教傳教士在山西開(kāi)辦最早的教會(huì)學(xué)校,之后教會(huì)各派紛紛在山西建立新式學(xué)校。1900年,基督教浸禮會(huì)在山西陽(yáng)曲縣(今太原)杏花嶺開(kāi)辦男書(shū)房和女書(shū)房。1902年,基督教會(huì)率先在太谷縣南關(guān)開(kāi)辦貝露女子學(xué)校,信教女子走出閨閣,進(jìn)人課堂讀書(shū)受業(yè)。由此,為后來(lái)山西私人興辦女學(xué)奠定了基礎(chǔ)和提供了經(jīng)驗(yàn)。
西方先進(jìn)的教育文化讓中國(guó)開(kāi)明紳士體會(huì)到了女學(xué)的重要性,讓女子受教育是改革傳統(tǒng)教育的關(guān)鍵因素。1897年,梁?jiǎn)⒊凇稌r(shí)務(wù)報(bào)》上發(fā)表《論女學(xué)》,強(qiáng)調(diào)興辦女學(xué)的重要性,指出:“治天下之本二:日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yǎng)始;蒙養(yǎng)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xué)始。故婦學(xué)實(shí)天下存亡強(qiáng)弱之大原也。”他認(rèn)為,女學(xué)的興衰是衡量國(guó)家是否強(qiáng)盛的重要標(biāo)志。戊戌變法時(shí)期,維新人士積極提倡興女學(xué),梁?jiǎn)⒊瑢憽秳?chuàng)設(shè)女學(xué)堂啟》《論女學(xué)》,嚴(yán)復(fù)寫《論滬上創(chuàng)新女學(xué)堂事》,女子教育的問(wèn)題逐漸得到朝廷的重視。清政府推行以“新教育”為重要措施的新政,其中就包括允許興辦女學(xué)。派遣留學(xué)生到海外,是清末新式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常氏家族子弟也積極加入留學(xué)生的行列,赴外地求學(xué),接受了先進(jìn)的文化熏陶。《榆次市志》記載,從1905至1932年的28年間,榆次籍貫的留學(xué)生共26名,其中車輞常氏4名,占15%。在“廢科舉,興學(xué)堂”的過(guò)程中,受教會(huì)女學(xué)及維新思想的影響,山西地方鄉(xiāng)紳開(kāi)始提倡女學(xué),創(chuàng)辦女子學(xué)校,鼓勵(lì)女子進(jìn)入學(xué)校接受新式教育。
常家歷代掌門人對(duì)家庭教育都非常重視,常氏家族內(nèi)設(shè)立私塾最多時(shí)達(dá)到17個(gè)之多,遠(yuǎn)遠(yuǎn)多于晉商其他各家。此外,常家還專門建立家族大書(shū)院,各堂開(kāi)設(shè)有小書(shū)院,六七十個(gè)堂院幾乎家家都專設(shè)書(shū)房或書(shū)院,供主人看書(shū)學(xué)習(xí)和對(duì)晚輩進(jìn)行早期教育。《榆次市志》記載:“從1907至1949的43年間,榆次籍貫的大學(xué)畢業(yè)生共105名,其中車輞常氏23名,占全縣的22%。”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特別是清末,一向?qū)W以致用的常家在對(duì)俄貿(mào)易的過(guò)程中,對(duì)“國(guó)弱民受欺”有切膚之痛,進(jìn)而接受了一定的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維新思想。《晉商史料全覽》記載:“尤其是常麟書(shū)在京師南學(xué)學(xué)習(xí)7年,對(duì)西學(xué)進(jìn)行了深入細(xì)致的研究,還經(jīng)常郵寄書(shū)籍資料回鄉(xiāng),在族中造成廣泛影響。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十三世常立教赴京參加科考,與康有為、梁?jiǎn)⒊嘧R(shí),參加了“公車上書(shū)”,成為山西省參與戊戌變法的3名舉人之一。”這些都為常氏改革傳統(tǒng)教育、創(chuàng)辦新式學(xué)堂奠定基礎(chǔ)。
1901年,朝廷頒布《興學(xué)詔書(shū)》,令全國(guó)各州縣書(shū)院改辦小學(xué)堂,小學(xué)教育得以普及。1902年,清政府頒布“壬寅學(xué)制”。1903年又頒布“癸卯學(xué)制”,規(guī)定“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學(xué)。”女子教育首次被提出。1903年,常氏家族中的十四世、清末進(jìn)士常麟書(shū)合并族中私塾,集中族中學(xué)齡兒童,創(chuàng)辦“常氏篤初小學(xué)堂”,是為山西省最早的私立新式小學(xué)堂,比我國(guó)正式廢除科舉制度、興辦學(xué)堂早兩年,比清政府頒布《初等小學(xué)堂章程》早6年。男女不能同校,當(dāng)時(shí)的篤初小學(xué)堂只接收男子,而教會(huì)在附近各縣開(kāi)辦女子學(xué)堂的成功,卻在常麟書(shū)、常贊春等常家學(xué)子中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影響。
“知恥”女子學(xué)堂的建立及復(fù)校
十四世常望春率先發(fā)起婦女教育。《常氏家乘》記載:“先生嘗課婦識(shí)字,讀隨園女弟子詩(shī),間能為小詩(shī)及斷句,于是為蕓香館夜課圖,以征題詠,稱韻事焉。”《儒商常家》記載:“他不僅教給家中的婦女識(shí)字,還要求她們讀乾隆時(shí)代江南隨園老人袁枚(1716-1798)的女學(xué)子的詩(shī)。”這事實(shí)上為常氏家族后來(lái)創(chuàng)辦“知恥”女子學(xué)堂開(kāi)了先河。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常家眾子弟的努力下知恥女子學(xué)堂創(chuàng)辦,《常氏家乘》記載:“光緒三十年秋,由(十四世)沛春、澤春、建春等發(fā)起,女學(xué)堂定名知恥。”在“篤初學(xué)堂”創(chuàng)辦的第三年,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由第十四世的常沛春(字雨農(nóng),時(shí)年28歲)、常澤春(字柳村,時(shí)年23歲)和常建春(字星生,年25歲)等人發(fā)起,利用第十三世北常常立德(人稱“大先生”)宅院的西院創(chuàng)辦“常氏女子知恥學(xué)堂”,以常浴春(字少沂,時(shí)年24歲)司庶務(wù),由族人擔(dān)任教員,因“女生男授”,為“解慮隔閡”而聘常立仁妻范氏(常贊春、常旭春之生母,時(shí)年65歲)任舍監(jiān),常立敬妾孫氏(時(shí)年42歲)、常立信妻曹氏(時(shí)年35歲)及張氏、常氏等等分任幼稚舍監(jiān)。常氏女子“知恥”學(xué)堂從1905年創(chuàng)辦至1913年因經(jīng)費(fèi)問(wèn)題停辦,是為第一期,歷時(shí)8年。停辦后,據(jù)《常氏家乘》記:“民國(guó)九年,立翰公任村女校事,族中女生附焉。”它是距今可考山西最早的國(guó)人自辦女子學(xué)堂,開(kāi)創(chuàng)了山西女子進(jìn)入學(xué)校學(xué)習(xí)的先河。
民國(guó)《榆次縣志》記載:“(車輞村知恥學(xué)堂)民國(guó)二年停辦。十四年,常贊春等規(guī)復(fù)。十八年,乃合并村中諸女生而授課焉。”民國(guó)十四年(1925年)秋,在常贊春的建議下,常家利用家族舊商號(hào)的一些賬尾殘資作為基金,《儒商常家》記載:“在山西著名藝人喬國(guó)瑞(藝名“獅子黑”)等人的資助下,在北祠堂東偏院(原賬房院)恢復(fù)“常氏私立篤初小學(xué)校”,同時(shí)將“知恥女校”合并,男女同校。校董為常贊春、常彥春、常建春、常麟雋、常鳳梧和常風(fēng)等人,校長(zhǎng)為常寶春。為維持學(xué)校生存,族人共商將僅有的余資投放到可靠的商家人股,以利息支撐辦學(xué)費(fèi)用”。后期的篤初學(xué)校,從1925年堅(jiān)持到1937年,直至抗戰(zhàn)爆發(fā)。
“知恥”女學(xué)堂的辦學(xué)情況
從辦學(xué)宗旨上來(lái)看,起初,“知恥”女子學(xué)堂的辦學(xué)宗旨只是想讓族中女子多注重品格修養(yǎng),如十四世常望春發(fā)起的婦女教育,隨著附近教會(huì)女校的建立,女權(quán)思想的深入,關(guān)于“知恥”二字的寓意,不僅僅直接理解為使族中女子通過(guò)讀書(shū)識(shí)字以知失禮之恥和失節(jié)之恥,而是要一反“女子無(wú)才便是德”的傳統(tǒng)觀念,使女性經(jīng)過(guò)學(xué)習(xí)多方面的新知識(shí),提高自立的本領(lǐng),注重了品德修養(yǎng),樹(shù)立做人的尊嚴(yán),在人格和能力上都可以自立。應(yīng)該說(shuō)“知恥”的真正目的是使族中女子既知無(wú)德之恥,更知無(wú)才之恥,從而成為新時(shí)代的獨(dú)立女性和新式家庭的賢妻良母。從學(xué)生入學(xué)條件來(lái)看,學(xué)堂開(kāi)始只招收本族女子入學(xué),后規(guī)模擴(kuò)大,外族女子亦可入學(xué)。《儒商常家》記載:“篤初此次復(fù)學(xué),車輞常家在村的男女學(xué)齡兒童全部入學(xué)。外姓和外村的個(gè)別學(xué)齡兒童因家長(zhǎng)有特殊關(guān)系得以在篤初讀書(shū)。”
從教學(xué)內(nèi)容來(lái)看:據(jù)《常氏家乘》記貴和堂“大夫第”老院載:“其功課則以文字、算術(shù)、修身為主,不拘定部章也。”民國(guó)《榆次縣志》記載:“功課則初習(xí)家事及作文、習(xí)字、算術(shù),漸乃擇增科學(xué)。”課程設(shè)置從剛開(kāi)始只學(xué)習(xí)文字、家事到后來(lái)增加科學(xué),就能發(fā)現(xiàn)常家創(chuàng)辦女學(xué)堂理念在發(fā)生新變化,以及常氏辦女學(xué)的教育水平不斷提升,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tǒng)婦德意識(shí)下“三從四德”“女子無(wú)才便是德”的舊觀念。
從師資力量來(lái)看,學(xué)堂的教師起初大部分由常家博學(xué)多才的長(zhǎng)輩來(lái)教授,比如常立仁妻范氏(常贊春、常旭春之生母,時(shí)年65歲),是《常氏家乘》中留有文字記載最多的女性:“乙巳歲,創(chuàng)設(shè)女學(xué),公請(qǐng)淑人監(jiān)視講授,諸女生莫不樂(lè)淑人(即范氏)之寬,懾淑人之重。數(shù)年來(lái),幼稚無(wú)嬉戲廢業(yè),諸婦無(wú)儷規(guī)受罰”。常贊春除授經(jīng)史諸舊學(xué)外,更親自為學(xué)生講勾、股、弦等格致知識(shí)。常立信之妻曹氏擔(dān)任監(jiān)堂,非常負(fù)責(zé),“所監(jiān)堂多幼女,以言笑不茍,皆嚴(yán)憚,終日無(wú)歡嘩”。還有一位日本女子師范畢業(yè)生福士宮子,她是十五世北常常鳳德妻子,《儒商常家》記載:“宮子性情賢惠,曾在知恥女校教書(shū)。”復(fù)校后的“篤初”在經(jīng)費(fèi)相當(dāng)困難的情況下,堅(jiān)持以高薪聘請(qǐng)?zhí)谝粠煼逗蛧?guó)民師范的高材生來(lái)校任校長(zhǎng)和教師。
從辦學(xué)效果來(lái)看,學(xué)堂開(kāi)省內(nèi)女子進(jìn)入新式學(xué)堂讀書(shū)之先河,辦學(xué)第二年就“女生漸眾,分堂講授”,有甲、乙、丙、丁四堂。《儒商常家》記載:“據(jù)后人回憶,知恥女校初期學(xué)生能記起名字的有從第十四世到十六世的13人:第十四世常沅春、常麟祉;第十五世常鳳笄、常鳳瑩、常佩蘭;第十六世常乃愛(ài)、常乃香、常乃慈、常乃愿、常士列、常士秀、常士淑、常士娎。”常家十五世北常后裔常鳳笄1903年出生,是十四世常瀚春之女。幼時(shí)即人常氏知恥女子學(xué)堂學(xué)習(xí),自小便聰明好學(xué)。后考入太原第一女子師范學(xué)校,有感于當(dāng)時(shí)女子上學(xué)之難,立志將來(lái)從事教育,以解放女性為己任。1924年畢業(yè)后即留校任教,此時(shí)正值家族商事衰敗,生活困頓,她用微薄的薪水奉養(yǎng)全家,使父母老有所依,弟妹均受到良好的教育。1926年,常鳳笄以優(yōu)異的成績(jī)考入齊魯大學(xué)教育系,畢業(yè)后又考入燕京大學(xué)碩士研究院,學(xué)業(yè)完成后先后在幾所教會(huì)學(xué)校任教。她是常家第一位受到高等教育的女子,又是常家第一位獲得碩士學(xué)位的才女。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北平淪陷后,常鳳笄回到山西,執(zhí)教于汾陽(yáng)銘義中學(xué)。抗戰(zhàn)勝利后重返北平,在著名的貝滿女子中學(xué)(新中國(guó)成立后更名為北京女十二中,今北京第一六六中學(xué))任教,直至離休。按民國(guó)《榆次縣志》記載:“民國(guó)九年(1920年)至二十三年(1934年)的15年間,榆次全縣從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xué)校畢業(yè)的學(xué)生共18名,其中車輞常家的有10名。”這10名常家女子中有9名都是畢業(yè)于初期的“知恥”女子學(xué)堂,包括常鳳笄、常鳳瑩、常乃愛(ài)、常乃香、常乃慈、常乃愿、常士列、常士秀、常士淑。在“知恥”復(fù)校后讀書(shū)的常鳳岱女士回憶她一生的文化底子來(lái)自常家女校。
從社會(huì)影響來(lái)看,常氏女子“知恥”學(xué)堂的創(chuàng)辦,在當(dāng)時(shí)形成了不小的轟動(dòng)。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中這樣記載:“有人言:此村之北八里許車輞村,前月設(shè)立女學(xué)堂一所,女學(xué)生不一,有女、有婦,凡十余人,年皆十七八歲,教習(xí)為某孝廉、某生員,皆未三十歲,所教皆效洋人之法,衣服亦效洋人裝飾,人多羨慕其所為,而不以為非。”常氏創(chuàng)辦女校成為典范,其他商人也爭(zhēng)相效仿,劉大鵬在其《退想齋日記》中記載:“榆次車輞村去冬設(shè)立一所女子學(xué)堂,本月太谷東里村亦設(shè)立女學(xué)堂。聞皆二十余歲之婦,其小者皆十六七之女,充教習(xí)者為男子。此風(fēng)一開(kāi),則男女有別之道并不講矣。”在車輞常家創(chuàng)辦“知恥”女子學(xué)堂后,潞安知府斌衍在潞安設(shè)立女子小學(xué)堂,祁縣渠本翹在祁縣創(chuàng)辦女子學(xué)堂,平陽(yáng)府也設(shè)置了平陽(yáng)女子學(xué)堂。常氏“知恥”女子學(xué)堂的興辦,首開(kāi)女子學(xué)堂讀書(shū)之先河,具有率先示范的作用,帶動(dòng)了晉中地區(qū)乃至山西女子教育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