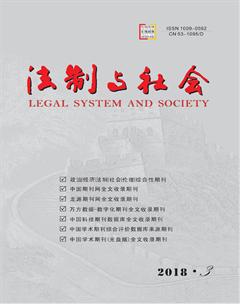淺析遺囑自由與限制
關鍵詞 遺囑自由 特留份制度 必留份制度
作者簡介:王雪,大連財經學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學。
中圖分類號:D923.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3.018
一、 遺囑自由
遺囑繼承是繼承的一種重要方式,而遺囑自由原則是遺產繼承制度的原則之一,它是被繼承人生前內心自由意志的體現,是當事人意思自治觀念的體現。根據探索發現,意思自治學說是于16世紀被正式提出,又過了兩個世紀開始被歐洲資本主義社會所使用,而到20世紀年以后,意思自治這個學說實際上已經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當事人的自治是意思自治的核心內容,其主要是對權利人自由的保護,這是一個法治國家所必須要考慮的和追求的,如美國《獨立宣言》其就是為美國普通民眾追求自由而創設,而其在我國的法律中也有所體現。如《民法總則》第五條:“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原則,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合同法》第四條: “當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 而在《繼承法》中則表現為遺囑自由。
遺囑自由即權利人可以依法律規定而設立遺囑,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由法定繼承人或非法定繼承人繼承,以及具體應繼承的份額。就如前幾年被媒體披露的一個遺產糾紛案件,一位四川瀘州的黃某將自己的六萬遺產經公證遺贈給了情人張某,致其妻兒為此訴諸法庭。這不得不讓我們進行反思,雖然黃某的意思表示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符合法律規則,但其遺囑的內容卻違反了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公序良俗原則。我國《民法總則》第八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如果這時黃某的妻子身患重病,孩子還未成年,得不到他的遺產他們的生活將會面臨什么樣的情形;如果在社會上要是形成這種風氣,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又會面臨什么樣的境地。這不僅不利于家庭和睦、社會進步、國家發展,更不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觀、價值觀。因此我們必須要對遺囑自由原則進行必要的限制。
二、特留份制度
任何事情都會有相對性,有權利就勢必會伴隨著義務的產生,正如盧梭所說“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中。”這正是其最好的詮釋。遺囑自由也是如此,因此大多數國家都對其采用相關制度進行了必要的限制,如特留份制度,其主要指遺囑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以遺囑方式來取消法定繼承人應繼承的份額。
特留份制度的淵源最早可溯至古代羅馬法的“義務份”制度,在《十二銅表法》時代,古羅馬的遺產繼承制度(即遺囑自由)已經被人所熟知并使用,而遺產自由并不是個人的觀點,而是家長為了維系家庭和睦;避免財產分散,而采用遺囑的方式來確定繼承人繼承。但,“到了共和國末葉,文字遺囑出現后,遺囑人可以用書面形式立遺囑,遺囑由公開轉為秘密,立遺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當時,生產力有了提高,財富增多,價值世風日下,家長或因受人愚弄或一時偏愛而濫用自由權的現象日趨嚴重,有的奴隸主甚至立遺囑將其財產留給情婦或不相干的人,而不給自己的子女”,因而,法律為了保護近親屬的利益,于是設立了義務份制度,此時如果遺囑人設立了一份損害義務份的遺囑,沒有給其近親屬留下必要的財產,則近親屬便可以提起訴訟,以請求撤銷遺囑人所設立的遺囑,返還其應得到的財產份額。
全球大部分國家的法律都創設了特留份制度。在大陸法系中,德國的繼承法對特留份做出了相關規定,其規定遺囑人可以遺囑的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但必須為自己的近親屬留出一定份額的財產,該份額如果少于法定應繼承的財產,則其近親屬還可以要求補齊。瑞典的相關法律也對此做了規定,如被繼承人有近親屬(即父母、配偶、子女等人),那么其只能處分特留份份額以外的財產,不能處分繼承人應繼承的份額。例如經典的特魯福特遺產案件,特魯福特是一瑞士公民,他死后留下遺囑,將其在英國的全部財產交給其教子,這時他的獨生子就對其進行起訴,要求繼承這筆遺產,最終根據瑞士實體法,其獨生子勝訴。這些法律法規不僅明確了特留份的權利主體,還具體規定了特留份權利人應繼承的財產份額,其充分的保護了特留份繼承人的權益。
在英美法系,雖然在單行條例和判例中沒有出現明確的“特留份”這一概念,但相關的制度還是存在的,以此來限制遺囑自由原則。如英國1938年頒布的《繼承法》,其借鑒了新西蘭有關經濟供養制度,用以限制遺囑自由。該法規定了被繼承人不得以遺囑的方式來逃避對其近親屬的扶養義務,如果其近親屬認為其沒有為自己的生活做出合理的安排,則可以請求法院分割一定份額的遺產用來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美國《統一遺囑檢驗法》也做出了相關規定,其主要包含了宅院特留份、憲法宅院特留份、豁免財產、家庭特留份、寡婦產和鰥夫產、選擇份等內容,從中可以看出《統一遺囑經驗法》也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規定了各種形式的特留份。可見,私權領域是不可能無限膨脹的,遺囑自由原則也是有邊界的。我國在遺囑自由方面也做了相應的規定,但相比較而言我國在此方面的立法仍有不足之處。
三、我國在遺囑自由限制的立法現狀及建議
(一)立法現狀
我國在《繼承法》第16條確定了遺囑自由原則,同樣也對其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我國跟其他國家相比在遺囑自由限制這方面的立法做的還遠遠不夠。如《繼承法》第19條規定:“遺囑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保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意見》第45條規定:“應當為胎兒保留的遺產份額沒保留的,應從繼承人所繼承的遺產中扣回,為胎兒保留的遺產份額,如胎兒出生后死亡的,由被繼承人的繼承人繼承。”新頒布的《民法總則》第16條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娩出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自始不存在”從上述的法條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我國的必留份制度對于遺囑自由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對遺囑自由的限制的規定過于狹窄,其主要針對的是沒有勞動能力沒有生活來源的人和胎兒,而這種人畢竟是少數,其未保護法定繼承人的合法權益。并且該規定也沒有明確說明必留份的繼承人具體應繼承的份額,按照什么比例繼承,從而法官就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這樣可能會導致法官權力的濫用,而且還可能會引發家庭內部矛盾,導致糾紛的發生,不利于社會和睦。由此看出,我國在遺囑自由限制方面依然是很薄弱的,因此我國應該對其應該加強整頓。
(二)立法建議
1.擴大必留份繼承人的范圍
針對現有的法條來看,我國只對缺乏勞動能力并且沒有生活來源(以下簡稱“雙缺人”)的繼承人和胎兒保有必留份制度,而忽視了其他法定繼承人的合法權益。當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尚且有勞動能力,被繼承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將財產以遺囑方式贈與他人,如果幾年之后其繼承人喪失了勞動能力沒有了生活來源,生活陷入困頓,那么其法定繼承人的生活又由誰來保障,這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可以擴大必留份權利人的范圍,可以把遺囑人的近親屬如父母、妻子、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遺囑人收養的子女)列入到必留份權利人的范圍,從而避免了近親屬不能繼承遺產的發生,也極大可能的避免出現老無所養,幼無所依的情況,同時也能為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減輕一些負擔。
2.確定繼承人的遺產繼承份額
我國針對必留份的遺產份額標準不明確,我國繼承法對于“雙缺人”和胎兒的遺產繼承只使用“必要的遺產份額”、“應當保留繼承份額”等字眼,并沒有規定具體的份額,到底按照什么標準來計算,我國立法并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那么司法實踐中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對案件進行判決,這就很可能導致必留份人的合法權益遭到損害。因此,我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確定具體的繼承份額。如日本的“全體特留主義”,即在總產中拿出一定比例的份額給繼承人。如德國的“各別特留主義”,其根據繼承人的法定繼承份額來確定特留份的具體份額。我國也可以根據具體的國情采用相關的規定來確定法定繼承人最終應繼承的份額。本人認為可依據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盡的撫養義務的多少來確定繼承份額,如果其中一位繼承人與被繼承人共同生活,照顧其起居,其盡的扶養義務多那就可以繼承的多,如果繼承人平日不去探望照顧被繼承人,其扶養的少則少繼承。這樣不僅有利于做出公平分割,更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和促進社會的穩定融洽,同時也有利于繼承人更好的分配自己的財產,避免因為繼承份額不明而產生不必要的糾紛。
3.確立必留份剝奪制度
必留份權是以擁有繼承權為前提,如果繼承人喪失了繼承權,那么繼承人也就不再擁有必留份權。而目前我國對于繼承權被剝奪的主要依據是《繼承法》的第七條規定“繼承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為爭奪遺產而殺害其他繼承人的;遺棄被繼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情節嚴重的。”有關于《意見》 的第33條:“有扶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的繼承人,不盡扶養義務,分配遺產時,應當不分或者少分” 和《意見》第34條:“有扶養能力和扶養條件的繼承人雖然和被繼承人共同生活,但對需要扶養的被繼承人不盡撫養義務,分配財產時,可以不分或少分。” 關于這兩條意見,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如果繼承人出現以上所列舉的行為,并且造成了一定的后果,筆者認為也可以加入剝奪制度中,從而達到權利義務相一致,以此來維護社會秩序,同時也保障了遺囑人的權利,如果觸犯刑法相關法條,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實現法律公正。
四、結論
實行遺囑自由是對個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尊重與保護,對于遺囑繼承的立法,首先應當堅持“遺囑自由的原則”,充分尊重被繼承人的意愿,但這并不意味著對遺囑效力的限制的放松,不能讓遺囑成為個人意志的任性,自由應該是有限度的,應在公序良俗的框架內進行,不能只顧一方,而舍棄另一方,只有法理和情理同時兼顧,使得各方相互沖突的合法利益達成一種公平的競合狀態,從而實現公平正義,如此,司法實踐中諸如前文所提到的“瀘州張某受遺贈案”之類的案件便可以從容應對。
參考文獻:
[1][美]E·博登海默著. 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2]周楠.羅馬法原論(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盧梭.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周銀、宋瑞、李昕、徐一權.論遺囑自由的法律限度.法制與社會.2015(11).
[5]陳碧賢.特留份制度-遺囑自由與諸權益之平衡與協調.法治與經濟.2006(1).
[6]史浩明.我國應建立特留份制度.政法論叢.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