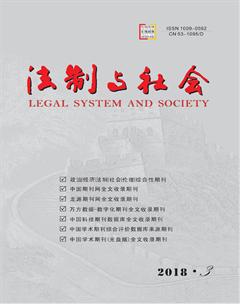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的立法現狀分析
李德龍 袁建瓊
關鍵詞 國家立法 城市立法 立法模式 責任制度
基金項目:本文是2016年重慶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重慶市主城區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立法完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CYB16086。
作者簡介:李德龍,西南政法大學2015級法律史博士在讀,研究方向:立法史、中國法制史;袁建瓊,重慶醫科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院,講師,西南政法大學2015級法律史博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法制史、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3.078
我國自上世紀末提出建立生活垃圾分類制度以來,在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已經制定了若干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對現有各個層面相關法律法規的梳理憤分析,筆者認為總體上可概括為:國家層面粗疏簡陋,地方層面龐雜零亂。自2013年以來,專門針對城市垃圾分類進行立法的城市正逐年增加,各個城市開始嘗試以專門立法的方式推進該領域工作。本章中,筆者將從國家層面、省級層面、城市層面對生活垃圾分類立法進行梳理,并總結此領域立法的最新動態。
一、國家層面立法:未成體系
國家層面立法涉及生活垃圾分類的條文,零散見于關于垃圾處理的若干法律文件中,大體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規范體系。按照頒布時間的先后順序整理如下:
第一,《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國務院1992年6月28日頒布。該條例系統地對城市固體廢棄物的處理進行了規范,其中第28條第2款規定:“對城市生活廢棄物應當逐步做到分類收集、運輸和處理。”是我國較早提出對生活廢棄物進行分類處理的法律文件。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棄物防治法》,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1995年10月30日制定,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2004年12月29日修訂。該法是我國關于防治固體廢棄物污染領域的基本法律,其中第三章第三節專門針對防治生活垃圾污染環境進行了規范,是我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同時,第42條規定:“對城市生活垃圾應當及時清運,逐步做到分類收集和運輸,并積極開展合理利用和實施無害化處置。”對垃圾的分類回收進行了初步原則性規定。
第三,《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原國家建設部2007年制定。該辦法是對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專門的相對具體的規定。第15條規定:“城市生活垃圾應當逐步實行分類投放、收集和運輸。具體辦法,由直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建設(環境衛生)主管部門根據國家標準和本地區實際制定。”第16條第2款規定:“城市生活垃圾實行分類收集的地區、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規定的分類要求,將生活垃圾裝入相應的垃圾袋內,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場所。”該規章對生活垃圾的分類投放、收集作了粗疏規定,為地方政府的立法提供了空間支持。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2008年8月29日通過。該法目的在于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和改善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并且提出減量化、無害化、再利用的廢棄物處理原則。應當說,促進生活垃圾分類回收是該法應有之義。第41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統籌規劃建設城鄉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和資源化利用設施,建立和完善分類收集和資源化利用體系,提高生活垃圾資源化率。”
此外,《環境保護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國務院《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也對分類問題有零星規定。可見,我國國家層面有關垃圾分類的法律規范仍僅為原則性表述,不成系統,也未形成具體制度。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為地方立法留下了充分空間。
二、省級層面立法:逐步探索
截至2016年10月,省、自治區層面的立法中,除《環境保護條例》、《市容環境衛生條例》等綜合類環境立法外,還有21個省(自治區)出臺了針對垃圾管理問題的46部立法文件, 其中絕大多數是省級地方政府規章層級。這些立法主要分為三類:一是針對特殊類型城市垃圾的管理進行專門規定,主要是規范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餐飲企業的廚余垃圾收運程序,而這些垃圾一般不被視為城市生活垃圾;二是針對一般城市生活垃圾的具體收運處理規定,主要是垃圾收費辦法、垃圾袋裝收運辦法等;三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專門性規定,比如廣東等省份有專門的水域垃圾處理管理辦法。可見,現有的省級地方立法對創設具體的垃圾分類回收法規規章著墨不多,只是在一般性立法文件或是特殊行業的專門性垃圾收運規定中有所體現,對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的影響不大,其探索十分有限。
三、城市層面立法:逐步出現,龐雜零亂
原國家建設部出臺了《關于公布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的通知》(建城部[2000]12號)并確定了八個試點城市之后,試點城市各自先后出臺過若干規范性文件。2011年2月,廣州市政府率先出臺了《廣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暫行規定》并于當年開始實施。以地方政府規章形式對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進行創設性立法,在國內屬于首例。此后,《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2013年4月)、《上海市促進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辦法》(2014年2月)、《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和減量管理辦法》(2015年6月)、《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規定》(2015年6月)、《蘇州市生活垃圾分類促進辦法》(2016年1月)先后公布,這是目前已出臺的五部專門針對生活垃圾分類進行的地方立法成果。仔細對比這五部立法文件,可以發現:
(一)立法的總體模式方面
首先,五部立法文件都是地方政府規章層級,目前尚未出現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進行生活垃圾分類專門立法的個例。其次,五部規章對立法目的、基本原則的敘述基本一致,主要是以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為生活垃圾分類目標,以政府主導、部門分工、屬地管轄、公眾參與為主要原則;略有不同的是,廣州和深圳的立法增加有“市場運作”的表述。再次,五部規章的篇幅詳略方面有明顯差異,廣州《規定》、南京《辦法》從篇幅和內容上看比較詳細,蘇州《辦法》比較簡略,上海《辦法》、深圳《辦法》則居中。最后,上海《辦法》的著眼點是融合“減量”與“分類”為一體,不僅從規章名稱,而且從內容上看,直接規定“減量”辦法的條文能占到近半數;深圳《辦法》雖然也在名稱上加以“減量”字樣,但其內容直接涉及“減量”的并不多;其他三座城市的規章則除了總則中目的條款外,較少涉及“減量”內容。
(二)對垃圾分類流程的規范差異較大
若以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置、資源再利用為一個完整過程,則廣州、南京、深圳的規定最為詳盡;蘇州《辦法》則較為簡單,分類處理流程更像是提綱性內容,缺乏具體操作標準和程序;上海《辦法》則僅規定了分類投放,對收集、運輸、處置沒有規定,其行為適用已經制定的《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運處置管理辦法》。
(三)對生活垃圾分類標準的規定不同
廣州、南京的立法都采用“四分法”,即將生活垃圾分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廚垃圾和其他垃圾。有所區別的是,南京《辦法》沒有在對四類垃圾進行列舉,而廣州和上海的《規定》則對四類垃圾有詳細列舉。同時,廣州《規定》中的“餐廚垃圾”范圍較廣,包括家庭和餐飲行業產生的廚余、廢棄食用油脂等易腐性垃圾;這類廢棄物本身既適用《廣州市餐飲垃圾和廢棄食用油脂管理辦法(試行)》中的處理流程,同時也納入了統一的生活垃圾分類流程。上海的《辦法》分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和干垃圾四類,其中“濕垃圾”不包括餐廚垃圾,后者的處理單獨適用《上海市餐廚垃圾處理管理辦法》。蘇州《辦法》也采用四分法,其中“易腐垃圾”范圍較廣,包括家庭、市場、工業廢料中的易腐垃圾和有機垃圾,以及農村可堆肥垃圾,但同樣不包括餐廚垃圾,后者的處理適用單獨的《蘇州市餐廚垃圾管理辦法》。深圳則采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三分法,同時鼓勵有條件的區域加設“廚余垃圾”分類。由此,各地分類方式中差異最大的就是對易腐、有機類、餐廚類垃圾的歸類和處理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地區是否建立有單獨的餐廚垃圾清運處理制度。
(四)普遍建立了“分類投放管理責任人”制度
這一制度未出現在2011年廣州《暫行辦法》中,也沒有明確出現在發改委、住建部的《制度方案(征求意見稿)》,卻在五部已經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中同時出現,說明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制度點。五部規章中對分類管理人的規定和列舉詳略不一,但基本思路相對一致,即:居住區域,實行物業管理的,以物業服務管理單位為責任人(未實行的,以全體業主為責任人);機關、企事業單位等辦公場所,該單位整體為責任人;公共建筑、公共區域,所有權人或者管理單位為責任人;經營性場所,經營單位為責任人。這一制度的主要意義在于,明確了不同類型區域垃圾分類投放的責任人,可以使分類投放階段的義務主體更具體明確,通過相關具體的激勵措施和獎懲規則,促使初始階段的分類得以完成。
(五)不同程度地規定了相關激勵措施
刺激性激勵機制已經被認為是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當中被廣泛運用的手段,幾乎貫穿于整個管理過程。 如分類獎勵、積分兌換、押金退還等。其中,深圳市和蘇州市的立法均以專章形式設置了有關條款,相對集中而詳細。
總體而言,從目前已出現的五部地方政府規章來看,生活垃圾分類管理領域的立法還處于初級試驗階段。各地立法雖然出現共性的內容,但在總體上呈現龐雜零亂的態勢。制度設計、立法文本內部自洽性、立法配套、與同位階法文本配合度等都有待完善。
注釋:
此處筆者統計省(自治區)層面立法情況時,沒有把四個直轄市計算入內,主要原因是直轄市的市政管理立法更具針對性,更接近城市層面而非省(自治區)層面,因此此處作了特殊處理,不將其計算入省(自治區)層面。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立法層級意義上將它們降低。
羅曼.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與處理的法律問題研究——以成都市為例//光華法學(第九輯).法律出版社.2015.17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