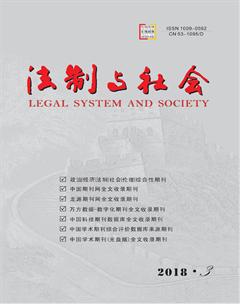論票據設質背書的法律效力
關鍵詞 票據質權 質押背書 法律效力
作者簡介:李映萱,華東政法大學。
中圖分類號:D92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3.101
票據設質背書,也稱票據質押背書,是指持票人以票據權利為債務擔保而設定質權的一種票據行為,即通過在票據上記載“質押”字樣并簽章做成背書、為被背書人設立票據質權。我國關于票據設質背書的法律規定存在沖突、淵源流變異常復雜、現行立法相互抵觸,引發了司法實踐和學術理論的分歧。筆者立足現行立法概括出設質背書效力的兩種主義——生效主義和對抗主義,集中分析二者是否存在實質沖突,試圖通過構建新的解釋論框架探討現行法下二者協調適用的可能性,并對《票據法》第35條第2款進行評價和建議。
一、現行立法及兩種主義
我國關于設質背書法律效力的規定見于《票據法》、《物權法》、《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然而三部法律對設質背書法律效力的具體規定卻各不相同,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模式:
(一)《物權法》:未對設質背書作出明文規定
《物權法》第224條規定:“以匯票、支票、本票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
(二)《票據法》及其司法解釋:作成質押背書票據質權才生效,未作成質押背書的不成立票據質權
《票據法》第32條第2款規定:“匯票可以設定質押;質押時應當以背書記載‘背書字樣。被背書人依法實現其質權時,可以行使匯票權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票據法司法解釋》)第55條規定:“以匯票設立質押時,出質人在匯票上只記載了‘質押字樣未在票據上簽章的。或出質人未在匯票上記載‘質押字樣而另行簽訂質權合同的,不構成票據質押”。
(三)《擔保法》司法解釋:票據一經交付則認為質權已經設立,作成設質背書后產生對抗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下稱《擔保法司法解釋》)第98條規定:“以匯票、支票、本票出質,出質人與質權人沒有背書記載質押字樣,以票據出質對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分析現行法體系可知,目前我國現行法中關于設質背書法律效力的規定體現出兩種基本主張。一種是“生效主義”,以《票據法》及其司法解釋為代表,即認為作成質押背書才設立票據質權,未作成質押背書的不成立票據質權。一種是“對抗主義”,以《擔保法司法解釋》為代表,認為票據質權自票據交付時設立,設質背書是票據質權的對抗要件,未經設質背書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盡管《物權法》未對設質背書作出明文規定,但“質權自交付時設立”可作反面解釋,其理論邏輯與“對抗主義”一脈相承,故亦可歸為“對抗主義”。
那么生效主義與對抗主義是否當然存在矛盾沖突呢? 部分學者根據文義解釋得出,若采生效主義,票據質權設立的要件為“交付+完全背書”,采對抗主義立,要件為“書面合同+交付”,顯然產生了不同的法效果,因此二者當然沖突。筆者認為不然,這種對生效主義和對抗主義的解釋是狹隘的,兩種主義其實并不存在根本性沖突,可以通過解釋論的視角重新構建生效主義、對抗主義的法律解釋框架,在現行法體系下協調適用。
二、生效主義與對抗主義的解釋與重構
傳統觀點認為,生效主義的含義是票據質權經設質背書設立、未經設質背書票據質權不成立;對抗主義的含義是票據質權自票據交付時設立、經設質背書產生對抗效力、未經設質背書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筆者認為,前述“票據質權”、“票據質押”盡管文義相同,卻可作不同的體系解釋。生效主義中的“票據質權”應解釋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對抗主義中的“票據質權”應解釋為“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二者具有不同的構成要件和內涵,票據質權的標的、設立和實現方式各不相同,因此“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和“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確有區分意義,且互不沖突、可以協調適用。
(一)生效主義的再解釋——基于“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
根據《票據法》相關規定,作為一種票據行為,設質背書必須具備無因性、要式性、文義性等特點,這些特點具有票據法上的特別意義。生效主義與票據法相對應,故生效主義中的票據質押亦應符合票據法的基本精神。結合票據法相關規定,筆者認為可對生效主義作出如下框架性解釋:
首先,生效主義中“票據質權”的標的是票據權利。
其次,生效主義中“票據質權”的設立條件是“交付+完全背書”。事實上背書本身即含有交付之意,完全背書則是票據行為要式性的體現。
最后,生效主義中“票據質權”的實現方式是質權人行使“匯票權利”。因為作成設質背書是“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的設立要件,故票據質押一旦生效,質權人就已通過背書記載在票據上,如果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質權人有權直接實現其質權,即通過行使付款請求權或追索權、就取得的票據金額優先受償。
(二)對抗主義的再解釋
根據前文所引《物權法》和《擔保法司法解釋》相關規定,票據質權自票據交付時設立,未經設質背書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筆者認為,僅交付而未經設質背書時設立的是“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不得對抗付款人和善意第三人,只有作成設質背書才能設立“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產生對抗效力。下面就對抗主義作出詳細解釋。
1. 僅交付:設立“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
(1)“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的標的是債權。由于未作成設質背書,此種質權不具有票據法上的特別效力,只能依據《物權法》第224條設立以票據為權利憑證、以普通債權為標的的質權。
部分學者對此持反對態度。有觀點認為,票據本身作為動產并不具有價值、根本不存在一種所謂的“普通債權”、據此設立“票據質權”沒有意義。筆者并不認同此種觀點。在探討“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時,應當把票據視為背后金錢債權的權利憑證,而非一項普通動產。誠然票據本身作為動產并無價值,但設立質權時著眼的是票據所代表的金錢債權,這也恰恰體現了權利質權與動產質權的區別所在。因此以“普通債權”為標的設立“票據質權”并無問題。
(2)“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的實現方式。未經背書的質權人雖然不具有票據權利,但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質權、實現擔保物權的目的。具體途徑有二——請求出質人行使票據權利、請求法院確認票據質權。其法律依據是《票據法》第31條“以背書轉讓的匯票,背書應當連續。持票人以背書的連續,證明其票據權利;非經背書轉讓,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匯票的,依法舉證,證明其票據權利”。
也有學者對此持有否定觀點。有觀點認為,這兩種途徑都需要借助出質人或法院配合才能實現、故此種票據質權有擔保物權之名無擔保物權之實。筆者認為此種觀點對于擔保物權的要求過于嚴格。從物權法內部體系來看,匯票、支票、本票、債券、存款單、倉單具有相似的權利憑證屬性,將普通債權剔除出的擔保物權的客體范圍過于絕對。
2. 作成設質背書:設立“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
一旦作成設質背書,則票據質權具有《票據法》上的特別效力,被背書人享有匯票權利,得以向付款人請求付款或者向前手追索以實現其質權,與上文生效主義中的“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性質和法效果相同。
有學者認為認為,區分“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和“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違反了票據行為的文義性、要式性的基本特點。其實并不盡然,僅僅承認了物權法意義上的票據質權、質權人并未獲得票據權利,實際上并沒有違反票據的文義性、要式性要求。
3. 關于對抗的效力
對抗效力具體包括對抗付款人的效力、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就付款人而言,僅交付票據而未經設質背書時,質權人不得對抗付款人,即付款人有權以背書不連續為由拒絕質權人的付款請求;若作成設質背書則該票據質權得以對抗付款人。就善意第三人而言,由于背書連續的要求,此種情況下事實上并不存在善意不知情的第三人。
綜前文所述,當區分“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和“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時,生效主義和對抗主義其實并不存在本質沖突。交付票據是設立“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的要件,設質背書是設立“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的要件,可以把二者看作遞進關系,即“票據質權”的設立視為兩步走。在該解釋框架下設質背書的效力并不存在實質性法律沖突。
三、新解釋框架下設質背書的法律效力
在上述解釋框架下,經設質背書才能設立“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未經背書不能設立“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討論設質背書的法律效力還有一個方面,即從反面著眼,分析不完全背書的法律效力。
不完全設質背書是指票據上只記載了“質押”字樣而未簽章,或者未在票據上記載“質押”字樣的背書行為。學界關于不完全設質背書的法律效力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因為不完全設質背書不能嚴格滿足設質背書的格式和程序性要求、不符合票據行為的要式性,不應當承認該行為所設立了“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在已交付的前提下僅能承認設立了“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
四、《票據法》第32條第2款的評價及建議
《票據法》第32條第2款規定:“匯票可以設定質押;質押時應當以背書記載‘背書字樣。被背書人依法實現其質權時,可以行使匯票權利。”本條采用設質背書對抗主義,依文義解釋本法條字面含義為:設質背書是構成票據質押的要件,未經背書、不完全設質背書不能構成票據質押。這種文義解釋對票據質押的要求過于嚴格,本條款中對“票據質權”的認識也過于狹隘,將使司法實踐中大量票據質押歸于無效,不利于票據權利發揮擔保功能。
承繼前文所述觀點,筆者認為應當將本條款中的“質押”限縮解釋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押”、“質權”限縮解釋為“票據法上的票據質權”。同時將未經背書、不完全背書設立的質權認定為“物權法上的票據質權”,給予較低程度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