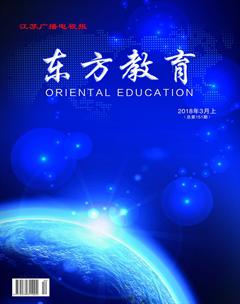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析
Rehab Mahmoud Ahmed
摘要:在她的作品中,張愛玲創作了許多女性角色。這些女性角色具有不同的個性和不同的結局,本文主要分析張愛玲小說中的四位女性人物。20世紀40年代的女性小說家張愛玲,通過她對女性心理、情感、生活和理解的理解,通過她獨特的視角和精神意識,為她的小說構建了一個生動的世界女性形象,這對中國兒童女權主義小說具有獨特的意義。
關鍵字:張愛玲小說;女性;人物形象
1.前言
張愛玲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女性人物形象。這些女性人物形象各有特色,結局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分析張愛玲小說中的四種女性人物形象,并對其性格和心理形成原因進行剖析。張愛玲是我國20世紀40年代女性主義小說作家代表,她以獨特的視角和心理體悟為基礎,通過對女性心理、情感、生活等的深刻把握,為其小說構筑了一個生動形象的女性世界,賦子了中國式女性主義小說獨特意義。
2.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張愛玲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現在中國現代文壇的天才女作家,她以她自己獨特的方式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場景。張愛玲對生活在那個特定時代中的人們,特別是都市現代女性們亂世中的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進行了深入透徹的剖析,塑造了一系列經典的女性形象。可以說,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張愛玲這樣,抱著對在經濟與精神上缺乏獨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關注,去專注于女性悲涼的命運的寫生。本文下面分三個部分探討一下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的不同類型,以期從中發現共性的部分及其對中國當代女性的啟示。
2.1良家婦女型的傳統女性
這類婦女形象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形象。簡單而言,良家婦女式的傳統女性即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環境里遵循著當時社會的倫理道德而循規蹈矩,履行著為人妻母的家庭婦女形象。她們是當前制度的合法遵循者,又深受封建道德意識的束縛,并且有著較強的家庭觀念。可以說,這類女性可以說在任何社會都占大多數。但是,張愛玲則走得更遠,她既把關注的視角既落在了家庭貧困的下層婦女身上,又掃描了貴族家庭婦女的生存狀況,描繪出了她們默默無聞的一生。或高貴或低賤,身份上的不同并沒有給她們帶來命運上的變化。她們也沒有做出什么出格的反叛的行為,但她們的勤勞,操持家務和掌控家庭的始終如一的恒心,無不是因為背后有一個或無能或猥瑣的小丈夫。如《創世紀》中的紫薇,伴著一個只會玩鳥斗雞的無任何思想、才能的遺少,把自己美好的一生消耗在了操持和掌握整個大家庭上。她精明能干,曾是風華絕代的美人,然而在退暮之年憶及繁華與荒涼的變遷和自己碌碌的一生,只能發出深深的慨嘆。正是這些庸俗而無能的丈夫毀滅了女性本應活潑靈動的生命,在這些平凡而常的良家婦女沉寂一生的命運上,我們看到了張愛玲對男性的猥瑣庸俗的部夷目光,明到了她對女性命運的深長的一聲嘆思[1]。
2.2畸形/變態的女性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女性人物形象都非常真實真切,即使丑陋古怪、壓抑瘋狂,她都進行了本真刻畫,以此來昭示宗法制父權之下女性的真實生存境況喚起人們對夾縫中女性被壓抑、扭曲甚至異化的不幸際遇的同情。《心經》是張愛玲在《第一爐香》《第二爐香》之后,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在文中,她將女性所造受的壓抑揭露得淋漓盡致。小寒有著濃濃的戀父情結在十二、三歲時,就愛上自己的父親許峰儀,最終演變成異性的畸形愛戀,并與母親為“奪夫”而上演曠日持久的大戰。總觀張愛玲小說中的變態女性形象其形成原因大多是對性欲或物欲過度追求面導致人性扭曲。在這類女性形象中中,最典型的莫過于《金鎖記》中的曹七巧這一形象,她從一個富有青春朝氣的“曹家大姑娘”,轉變成一個畸形和變態的人,這是她在反抗中無止境追逐欲望的結果。在“長為父”的封建倫常社會背景景下.曹七巧被兄長賣給了姜家、成為生下來就患有軟骨病的姜家二爺傳宗接代的工具。但是,曹七巧的丈夫卻從沒有使曹七巧體驗到做女人的快樂,這導致曹七巧的個人情欲被極大地壓抑,“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原欲就像一道主流受到阻礙的溪流,它只好溢向一向干涸的旁道”(弗洛伊德)。由于情欲長期遭受壓抑,曹七巧出現了性錯亂心理和性變態行為。由于曹七巧出身卑微,在姜家感受到的只是屈辱和漠視,“一家子都往我頭上踩”。那剛毅的性格和強悍的生命力,逐逐漸在這種環境下被扭曲成畸形。于是,在理葬了愛情之后,曹七巧踏上了瘋狂“復仇”的不歸之路,用她戴著黃金的枷鎖劈向了自已的骨肉,積蓄在胸中那變的火焰昋了別人,也吞噬了自己。《怨女》埋的銀娣和七巧有些相像,“麻油西施”銀娣自己選擇嫁給了軟骨病的富家子姚二爺,原本銀娣與藥店伙計可以結為百年之好,只是因為她受夠了沒有線的苦處,不想再繼續這種貧窮和被歧視的生活。與曹上巧巧相比,銀娣的變態程度要相對輕一光,但這種源自女性本身的變態,卻更引人深思和感慨[2]。
2.3夢想/幻滅中的女性
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女性,其獨立的精神人格和身份是很難在現實社會中實現的。張愛玲在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處于夢想/幻滅的女性形象,如《花湖》中的鄭川嫦、《封鎖》中的吳翠遠、《(金記》中的長安、《琉璃瓦》中的姚靜靜、《多少根》中的家藥以及《創世紀》中的匡瀠珠等。《花調》中的鄭川嫦出身在窮遺老的家庭,她非常渴望等爹有了錢,能送她上學,目的卻是當一個好“結婚員”。上學只是為了增加結婚選擇的等碼,榮華富貨才是唯一的夢想盡管這樣的愛情可悲可以,然而,在當時社會的確相當自然和現實。只不過,不幸的是,鄭川嫦罹患了骨癆,她的夢想也因此永遠實現的可能了[3]。《封鎖》中的吳翠遠要比川嫦幸運,她所在的家庭是具有宗教背景的新式家庭,父母努力將她培養成才,吳翠遠最終也在20多歲時成為當時女性的佼佼者,在大學里教書。然而,身為人之驕“女”的她只能做更高等男性的精神奴隸,逃脫不掉“食色男女”的現實框囿。“整個的上海打了個噸,做丁個不近情理的夢”。張愛玲冷眼注視著人生、從生中透視到死,從死中體悟到生,極盡筆地小了都市人那種死去活來的生存狀態。美好的夢想化為泡影,正是“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給人強烈的警醒和震撼。
2.4 無奈/墮落中的女性
《沉香網·第一爐香》中的葛藏龍,因上海戰事舉家到香港港避難,生活費用天天上漲,追于生計、學業和無奈,她偷偷去求助斷絕親戚關系且名聲不好的姑媽。在這個時候,葛薇龍也預感到之后的命運境況,內心也有矛盾和動搖。但涉世未深的她,就像只嘗試啄食的鳥兒,一步步進入到了華麗的籠子,最終卻是展翅也舍不得逃出了。她甘愿賣淫養夫以求嫁給喬琪,但和喬琪的婚煙換來的卻是絕望、觀敗、黑暗、寒冷。葛薇龍的墮落,是環境通迫,也是她沉于物質享受、意志薄弱、缺乏勇氣的弱點所致。張愛玲小說中描繪的是一個形的社會環境,女性的無奈/墮落與現實社會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女性的這種無奈/墮落也絕非偶然,而是當時社會中的普遍和必然現象。
3.小說中女性悲劇形成的原因
張愛玲的作品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她站在女性立場上,以女性獨特的眼光來審視女性自我,不僅關注女性的悲苦命運,而且將筆觸深入到女性內心深處,對女性自身的精神弱點進行審視和解剖。在看似波瀾不驚的敘述中,是她對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憫和同情。
3.1特殊時代
張愛玲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這種特殊年
代中,讓她筆下的女性不斷做出讓人驚嘆的選擇。比如《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
挺身走險,把自己押入一場愛情的賭局。張愛玲玲筆下的這些人物為了不斷膨脹
的物欲,可以出賣肉體,出賣靈魂,甚至出賣幸福,她們對物質的需要已達到一種異化的物欲,不幸的是,時代并沒給她們大貴的命運,她們得到更多的是一個悲慘的結局。物欲橫流最終吞沒了她們,使她們走向了人生的不歸路。因此當“似睡非睡”的七巧回憶起“十八九歲姑娘的時候……喜歡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們中的一個,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時,這些只能和著她臉上的兩滴淚珠,永遠地埋進了她的墳墓;霓喜在一次又一次被拋棄后,最終也成為一點人氣也沒有的“外頭人”;香港的淪陷雖成全了白流蘇的“愛情”但她心中的悲涼卻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半生緣》中的曼楨和世鉤是張愛玲小說唯一對有真情的情侶,但最后還是陰差陽錯的分開了。終是沒有選脫張愛玲小說中的灰暗和、虛無的氛圍[4]。
3.2個人性格的原因
生活環境對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不是出身于下
流社會,就是已衰敗的貴族,即使屬于中產家庭,生活也是相當拮據。所以對金
錢的渴望和對物質的享受成為她們與生俱來的天性。曹七巧出身于貧寒,小商販
精明的性格自然在她身上有所表現,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她嫁給了名門望族,甘愿去伺候一個殘廢的男人。低賤的出身與生活的環境,形成她自卑而又不甘的心理,一味地對金錢的追求成為她想把握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嫁到姜家目的就是為了錢,這個目的她達到了,但她畢竟出身于低賤,不可能有淑女風范,潑辣、刁鉆、善于調情的生活習性都是市井生活在她身上種下的痕跡,這也是情欲在她心中囂張的原因。這種“欲求不滿”使她從個曾有青春回憶的姑娘變成了一個陰險、兇狠、殘酷的近乎精神分裂的姜老太太,情欲就是這樣折磨著她。“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鎖,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張愛玲執著于人性的探索,人性的真實,人性的畸形、扭曲、變態也盡收眼底,她小說中展現的都是人類性格中的劣性,自私、虛偽、貪婪、軟弱就是她所塑造的人物的特性。尤其是女件,有人說女人生來就是弱者,但弱者背后好似有無窮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自我拯救而是毀滅。女人大多數的嫉妒心里很嚴重。古希臘戲劇中的美狄亞正是因為嫉妒,瘋狂到殺死自己的孩子。不能說張愛玲受到希臘戲劇的影響,但嫉妒確實是她筆下女性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5]。
3.3女性的社會地位
在以男性權力為標志的社會里,男人本身只把女人作為可以隨意擺弄的物品,當作一種附庸。女人對自己的處境和表現只能無能為力甚至無動于,好似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再反抗也是徒勞。即使有過反抗也一樣悲劇收尾。白流蘇勇敢的脫離婚煙的桎格,為了生存還是又一次走進婚煙的圍城。曹七巧不依賴于男入把黃金作為她最大的寄托,為了財產混滅了自己的情欲,轉過頭來又以封殺別人和兒女的情欲來作為自己情欲的補償,從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劇最根本的原因是經濟上不獨立,在沒有錢的基礎上只有依靠男性而生存。女性與男性永無體止的“斗爭”是她們的生存哲學。這種“斗爭”只是女性生存的追切需求。所以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意識便是一種迫切的生存意識。在曼橫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第一批職業女性的影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心酸和無奈。就是在現代,社會雖然給了女性自強自立的條件,但仍會從內心不自覺的依靠于男性的女性,或許幾千年的傳統思想已經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6]。
4.結束語
本文從分析因封建制度及男權社會壓榨導致的女性悲劇、因追求享樂的欲望過度導致的女性悲劇、因克制或缺失情欲導致的女性悲劇這三個方面。張愛玲小說女性形象的簡單分 類進行分析不足以真正從本質上把握張愛玲小說人物的內涵,必須從背景、表現力、主題等各個方面重新審視張愛玲小說的內在意蘊及其角度。由此可見,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悲劇命運的成因不是個人的,也深深烙上了時代的印記,是特殊時代造成的。
參考文獻:
[1]胡格軒:論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析[J]。新華網,2014-08-14:31-32.
[2]元暉:如何看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析[J]. 赤峰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 2015(10):51-52.
[3]沈燕: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J].大連民族大學學報.2015(5):10-11.
[4]王宇: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析[J].中國文學報.2014:24-25.
[5]孫海:論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析研究[J].大連海事學報.2016(5):6-8.
[6]王媛: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探析[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5):17-18.
作者簡介:Rehab Mahmoud Ahmed (1969年10月),女,埃及人,博士,教授,開羅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研究方向:漢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