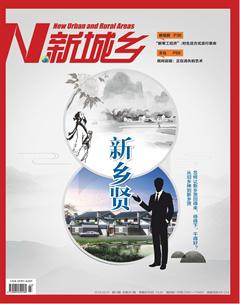當游戲改變教育
南橋
《游戲改變教育:數字游戲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更聰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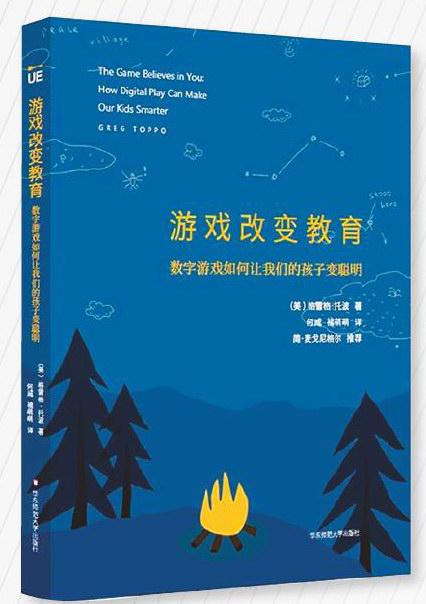
作者:[關]格雷格·托波
最近,我女兒所在的學校,一所側重數理化教育和項目式學習的學校,讓學生所做的作業顛覆了我的三觀。比如學校舉辦紙板船邀請賽:參賽學生只用紙板、膠布和膠水,制作紙板船。制作完畢后,該學校和附近初高中的同學,到大學的游泳池里去劃船比賽。這種劃船比賽,比不上劍橋牛津、耶魯哈佛那些賽船,但是小孩子們能設計出這種紙板船,讓其下水,里面坐三個人來回劃,也讓學生、家長和老師樂翻天。后來我女兒的物理課老師,又讓學生設計一種發射器,要能發射一個餡餅砸到老師臉上。學生三四人一組,設計了各種各樣的發射器,讓我們家長大開眼界。和我們當年的題海戰術不同,不知這種學習的“干貨”多少,但是所有這一切做起來都還頗有挑戰性。
教育中增加一些游戲的成分,對于人的健康成長是有好處的。《游戲改變教育》一書,譯自《游戲相信你:電子游戲如何讓孩子們更聰明》一書,生動地向我們介紹了教育和游戲相生相克的關系。
我對于此書的興趣來自自己的兩個孩子。我女兒上高中,學習中經常有上述制作游戲。我兒子上初中,和同齡人一樣,他經常玩《我的世界》這一款電子游戲。該游戲由于教人建造,而非拆毀,頗被教育界追捧。作為家長,我們總是怕這些游戲影響他們學習,可是如果游戲本身富含英語、數學、物理、歷史等各種教育維生素呢?
教育和游戲的分離,學習和玩耍的分割,是當代教育界一大悲劇。作為人類活動之一,教育其實本來就是一個游戲的過程。人類任何游戲,都有規則,有懲罰,有錯誤,有反饋,有改進。只不過后來,普魯斯式的規模化教學,和繁瑣的教育法律,使得學習不再是一個滋潤心靈、培育思維的活動。工業化使得教育的目標變成批量生產有同類技能、馴服聽話的職工,不需要太多能動性和創新性。現在機器人開始取代人工管理流水線,還向工業時代那樣訓練他們,他們以后怎么辦?
《游戲改變教育》要我們對于教育“不忘初心”。單純的文本閱讀能提供的意義,有時候經由其他感官得來,也一樣有效。電子游戲中的刺激有圖像也有音效,是多感官的。如果教育也能將其整合進來,那會造成閱讀成效的改變。
書中介紹,一款《龍箱》游戲,含有代數和幾何,在華盛頓州的測試中,學生僅僅用90分鐘玩游戲的時間,就掌握了預定學習的所有知識點。該游戲宣傳開來,參與也是驚人的:2014年,全挪威學生在它上面解出了近800萬個方程式。更多的游戲則是跨學科的,比如芬蘭的一家公司,設計了《憤怒的小鳥游樂場》,學習內容包括“數學、科學、語言、音樂、體育、藝術和手工”,并且提供“在休息、玩耍和學習之間的健康的平衡”。這年頭大家都在觀察挪威、芬蘭等北歐國家出色的教育成果,不少研究者是從課堂教學的效率和效果上思考,沒想到秘訣竟包括游戲的設計。
當然,更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書中提到了游戲在治療自閉、多動、注意力缺失等多方面的效果。游戲給人帶來愉悅,而愉悅本身是花錢或者學習都得不到的。或許我們不能老是想:應該怎樣向游戲學習,把教育搞得更好?而應這樣去問:我們怎樣通過廣義的大教育,讓青少年身心健康地成長?任天堂《超級馬里奧》的設計師宮本茂在孩子們索要簽名時總這么寫:“如果是晴天,請去戶外玩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