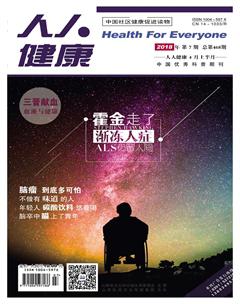三位醫生的慢性病防控經驗
胡大一
應對慢病的嚴峻挑戰,需要彌合臨床醫學、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裂痕,實現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的偉大轉折。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更多的醫生能改變理念和行為,和疾控中心、預防醫學、公共衛生的“戰友們”并肩戰斗在慢病預防控制的最前線。在這里,我想給大家講講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三位醫生的故事。
第一位是吳英愷教授。吳英愷年輕時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解放后相繼創辦了解放軍胸科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安貞醫院。改革開放后,有一次吳老帶醫學代表團出國訪問了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隨團的劉力生教授在回國途中問吳老:“回國后,應該干什么?”劉力生預想吳老的回答可能是發展心臟搭橋技術,因為中國當時心臟搭橋術非常落后,而吳老是胸心外科專家。可她沒有料想到吳英愷教授給出了非常簡明的一句話:中國心血管病的唯一出路是預防。
這不但照亮了劉力生的職業人生,而且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代代心血管醫生的職業發展和奮斗方向。在開拓我國心血管預防康復的新征程中,我們深切緬懷吳英愷等老一輩專家,是他們給我們后來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比如率先研究心血管流行病學及人群防治,比如當年的首鋼模式等。
第二位是創造芬蘭北卡曙光的心血管病專家PUSKAI醫生。在上世紀,芬蘭曾經是心血管發病率、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心血管病專家PUSKAI在認識到慢病只治不防、走不出困境的問題之后,開始全身心投入預防,在北卡省做示范區,最終實現患病死亡率下降80%、總死亡率下降50%、芬蘭人均壽命延長10歲的目標。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不是得益于支架和搭橋等生物技術,而是來源于全民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更為難得的是,在PUSKAI醫生的感召下,芬蘭政府改變了食品稅收和物價政策,讓不富裕的人也能吃到健康食品,而對煙草課以重稅,從而實現了健康芬蘭,并創造了全世界一級預防的經典模式。
第三位醫生是美國的COOPER醫生。他和我是老朋友,他因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而認識到自身的健康問題,也認識到醫療體制的問題,于是辭職,到哈佛公共衛生學院讀了公共衛生碩士,并和夫人一道建立了COOPER診所。這個診所雖是醫療機構,但只做病前的預防和病后的康復管理。1968年COOPER提出有氧運動,把有氧運動融入醫學,用運動的方式,用非醫療的干預手段實現慢病的防控。
這三位醫生的轉變,對中國和全世界的慢病防控事業都產生了重要的帶動和影響。希望有越來越多有影響力的醫學專家站出來,用自身的行動來彌合防和治的裂痕。也希望有更多的醫療機構站出來,徹底改變只治不防、越治越忙的現狀,修復斷裂的醫療服務鏈。只有把這些資源都發動起來,形成合力,慢病防控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