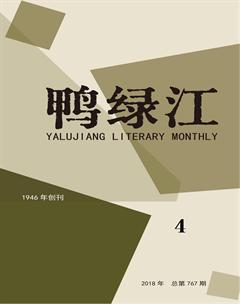雪
夏商
過了橋,從“綠化山”右繞二百米,菜市場隱匿在一摞破敗老宅里,保存室內(nèi)溫度的塑料垂簾如同一條條冰掛,本是透明的,卻被摸得很臟,能粘住蔬菜的草腥和魚蝦的臭腥,丁德耀每次撩都皺眉,他討厭縮頭縮腦的冬天,手勢僵硬,常被掀動(dòng)的垂簾擊中臉龐或耳垂。春天來臨的時(shí)候,垂簾被卸掉,可以長驅(qū)直入,他目標(biāo)明確,直奔常去的那幾個(gè)菜攤。他喜歡吃魚蝦,討厭吃羊肉和豆制品,倪愛梅喜歡后兩樣,所以也得買一點(diǎn)。
他們有分工,他買菜,倪愛梅下廚,飯后他洗碗。婚姻就是這樣冗長無趣,又無法省略任何步驟,變化在于,周末他們會(huì)一起逛菜場,結(jié)婚七年,還能一起逛菜場,說明是一對(duì)恩愛夫妻。至少,還沒有完全相厭。
為扭轉(zhuǎn)他對(duì)羊肉的成見,倪愛梅做過幾次魚羊煲,讓他買那種產(chǎn)自遠(yuǎn)郊的少膻味的山羊肉,用不同的魚燴制,有時(shí)海鮮,有時(shí)河鮮,雖頗費(fèi)苦心,他并不覺得好吃,還得裝出夸張的口吻說,魚加羊不就是鮮字么,味道好極了。
“味道好極了”是電視里的咖啡廣告語,當(dāng)他洗碗時(shí),倪愛梅守在彩電前,看那些永遠(yuǎn)也放不完的電視劇。
此刻,丁德耀站在常來的魚攤前,讓小攤主潘冬子稱三兩蝦仁,倪愛梅準(zhǔn)備配上臭豆腐加剁椒,做一道新學(xué)的菜。設(shè)法將丈夫的忌口與自己的喜好融進(jìn)一只菜盤,是她看電視劇之余的最大愛好。丁德耀有時(shí)想,養(yǎng)個(gè)孩子費(fèi)錢又操心,兩個(gè)人過日子其實(shí)也挺好。不過,每當(dāng)看到這個(gè)同學(xué)的兒子會(huì)打醬油了,那個(gè)同事的女兒會(huì)唱兒歌了,心就癢癢了。
這個(gè)七歲的小男孩潘冬子也讓他心癢,他跟母親一起擺攤,父親老潘是清洗大樓外墻的蜘蛛人,這個(gè)總是抽劣質(zhì)煙的小個(gè)子男人肯定是電影《閃閃的紅星》的擁躉,要不然也不會(huì)給兒子取這個(gè)名字。丁德耀喜歡愣頭愣腦的潘冬子,別說,還真酷肖那個(gè)小游擊隊(duì)員,圓臉,大眼睛里全是機(jī)靈。說話像含糖,看到他就叫丁叔叔好,也會(huì)做生意,把魚蝦挑好,倒置馬甲袋將水分潷干,再放到臺(tái)秤上,磅完了往袋里多扔一條小黃魚,或一只蝦,再遞給主顧。他媽媽看著兒子完成這一切,眼睛瞇起來,慈祥地微抿嘴角。
丁德耀卻要去掃她的興,你應(yīng)該送潘冬子去讀書,這么聰明的孩子不上學(xué),可惜了。
他媽媽不生氣,還是微笑:“自己孩子自己知道,做別的還可以,讀書肯定是聰明面孔笨肚腸,黃魚賣多了,腦袋也是黃魚腦袋,賣賣魚挺好的。”
丁德耀嘆口氣,知道多說無益,悻悻然走了。
有一次,趁潘冬子母親不在,他問小男孩,你自己想讀書么?
潘冬子說,不想,我爸媽說讀書沒什么用,又不當(dāng)飯吃。
丁德耀說,那你不讀書,有什么理想?
潘冬子說,有啊,現(xiàn)在每天賣幾十斤魚蝦,最好每天能賣兩百斤,那樣我爸就可以不用高空擦玻璃了。
丁德耀道,那長大后呢,長大后的理想是什么?
潘冬子說,長大后每天賣五百斤,討個(gè)老婆生一對(duì)雙胞胎,老婆孩子熱炕頭。
丁德耀說,為什么要生雙胞胎?
潘冬子說,雙胞胎比較好,最好是龍鳳胎,一男一女湊個(gè)好字。
丁德耀說,你不上學(xué),怎么知道一男一女湊個(gè)好字?
潘冬子說,聽大人說的。
丁德耀說,不是一男一女湊個(gè)好字,是一個(gè)女字一個(gè)子字湊個(gè)好字,你看,上學(xué)還是很有用的。
潘冬子說,上學(xué)也是老婆孩子熱炕頭,不上學(xué)也是老婆孩子熱炕頭。
丁德耀無法反駁潘冬子的話,本質(zhì)上,這個(gè)孩子的理想和他是一樣的,跟絕大多數(shù)人也是一樣的,賣更多的魚,賺更多的錢,結(jié)婚生娃過小日子,他甚至無法否認(rèn)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便不讀書,潘冬子的理想,或者說他父母賦予他的理想,確實(shí)也是可能實(shí)現(xiàn)的,即便賣不了五百斤魚,賣三四百斤還是可能的,甚至運(yùn)氣好的話,做更大的生意也是可能的。所以,他對(duì)潘冬子的規(guī)勸并無說服力,他只是覺得有點(diǎn)莫名的惆悵,學(xué)齡不去讀書,跟著大人擺攤,太可惜了,要是自己兒子,肯定找最好的學(xué)校,把他培養(yǎng)進(jìn)北大清華。
倪愛梅去過婦產(chǎn)科很多次,說是輸卵管粘連,也就是說,射程到不了目的地。倪愛梅的問題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丁德耀也存在精子活性不足。理論上,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不過丁母堅(jiān)持認(rèn)為,兒子的問題是次要的,倪愛梅更理虧一些。
生兒育女,再天經(jīng)地義不過,求子不得,不是夫妻雙方的事,而是兩個(gè)大家庭的事。幸好這對(duì)小夫妻獨(dú)立居住,住所雖不大,距市中心也偏遠(yuǎn),但不跟父母同住的好處顯而易見,至少嘮叨不會(huì)隨時(shí)響起。倪愛梅慶幸領(lǐng)證前共同按揭買下這套小戶型,可以免于和公婆一起住,若不然肯定被婆婆煩死,她的小姐妹丁紅和老公離婚的很大因素就是受不了婆婆的碎碎念。
世事就是氣人,有些人并不想要孩子,或者說并沒有做好當(dāng)?shù)鶍尩臏?zhǔn)備,偏偏觀音娘娘就送子來了。遠(yuǎn)的不說,丁德耀二舅的兒子小帆,還是大二學(xué)生,談戀愛把同校女同學(xué)肚子搞大了,小姑娘私自去流產(chǎn),病歷卡沒藏好,被父母發(fā)現(xiàn)了,一般情況下,為了女兒名聲,會(huì)選擇啞巴吃黃連,這家父母耿直,找到丁德耀二舅家理論,丁德耀二舅媽是有名的母老虎,一言不合就吵起來了,吵得整幢樓地動(dòng)山搖,玻璃窗都快裂開了。
還有倪愛梅的那個(gè)小姐妹丁紅,和她老公曹原群是堅(jiān)定的丁克主義者,堅(jiān)定到什么程度?倪愛梅和丁紅喝閨密下午茶,聊起男女情事,丁紅說為了避孕,非戴套不做愛。倪愛梅問每次都戴?丁紅說每次都戴,一次都不落下。倪愛梅將信將疑:“照你這樣說,肉從來沒碰到過肉啊。”
丁紅沒反應(yīng)過來,什么意思?倪愛梅說,每次戴套,隔一層硅膠,肉怎么碰到肉呢?丁紅捶了倪愛梅一拳,好你個(gè)女流氓,什么下流話都敢說。
丁紅和曹原群肉從來沒碰到過肉,感情卻很好,因?yàn)闆]準(zhǔn)備要孩子,就沒存錢的打算,經(jīng)常下館子看電影,攢年假出去旅游,美中不足的是,當(dāng)初沒按揭買房,辦完婚宴后和公婆一起住,公公不怎么管事,婆婆想抱孫子,看媳婦肚子一直沒動(dòng)靜,一開始指桑罵槐,后來就直接罵桑了,丁紅想搬出去,房價(jià)已漲到連貸款的勇氣也沒了。小兩口起念外出租房,曹原群剛一提,曹母張嘴就罵,曹原群性情怯懦,從不和母親頂嘴,丁紅卻不是省油的燈,和婆婆頂嘴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聲調(diào)越來越高亢,曹原群三夾板兩頭受氣,有一次沒忍住,推了一下丁紅,丁紅反手就是一記耳光。小兩口就這么完了。從民政局領(lǐng)完離婚證,裝新潮吃分手宴,兩個(gè)酒量平平的人,喝了一大瓶加了冰塊的威士忌,想起過往的愛情,哭得泣不成聲,東倒西歪坐進(jìn)兩人合伙買的而今劃歸丁紅名下的國產(chǎn)SUV,做戲做全套,玩起了車震,曹原群去取避孕套,被丁紅阻止了,那一刻,她想起了倪愛梅的話,心想在一起那么多年,一直采取措施,這最后一次,無論如何要水乳交融,于是,這對(duì)離婚夫婦做了一次無套之愛。
不想僅這一次破戒,便在丁紅身體里播下了一粒不該發(fā)芽的種子,她約倪愛梅喝下午茶,告訴了自己懷孕的消息。倪愛梅驚詫地望著她,以為她這么快就有了新歡,當(dāng)?shù)弥歉茉焊鎰e演出造成的結(jié)果,不知說什么好。丁紅倒也灑脫,說,還不是你那句話刺痛我了。倪愛梅問她打算怎么處理腹中的孩子。丁紅說,我是丁克,不會(huì)要孩子的,這次身體要吃苦頭了,不過和曹原群感情一場,我不后悔。
倪愛梅本不想把丁紅打胎的事告訴丈夫聽,丁德耀肯定會(huì)說,生下來送給我也好啊。
她知道他肯定這副德行,就忍了兩天,到了第三天臨睡前,頭枕靠墊沒忍住,就說了,一說完就后悔,誠如她所料,丁德耀立刻從被子里坐起來:“干嗎打掉,生下來給我嘛。”
看著丈夫痛心疾首的樣子,就知道又要說他的祖母外祖母了——話說回來,讓她反悔一次,她還是做不到守口如瓶,還是會(huì)說給丈夫聽,這是她的秉性所決定的,夫婦之間不該有秘密,她不喜歡隱瞞,她喜歡和丈夫分享家長里短,雖然有時(shí)會(huì)顧慮引火燒身而暫時(shí)不說,最終還是會(huì)按捺不住——他已說了不下一百次,但不妨礙說第一百零一次:“你說,現(xiàn)在的女人生個(gè)孩子怎么這么難,我奶奶生了七個(gè),外婆生了十一個(gè),跟母雞生小雞似的,一生一大窩,現(xiàn)在的女人可好,生一個(gè)都難……”
見老婆沉下臉,丁德耀知道又說錯(cuò)話了,忙解釋:“不是說你,現(xiàn)在的女人普遍這樣,每次陪你去婦產(chǎn)科醫(yī)院,都是一大堆不能生娃的女人在掛門診。”
倪愛梅說,你是沒說我,可我也是其中一員,我沒用好了吧。
丁德耀知道老婆不開心了,觍著臉賠笑道,生孩子太麻煩了,實(shí)在不行,我們?nèi)ヮI(lǐng)養(yǎng)一個(gè)現(xiàn)成的吧。
倪愛梅說,去哪兒領(lǐng)養(yǎng),你以為領(lǐng)養(yǎng)那么容易呀。
丁德耀說,領(lǐng)養(yǎng)當(dāng)然去孤兒院。
倪愛梅說,健康漂亮的孤兒哪輪得到我們,早被有權(quán)有勢的人家走后門了。
丁德耀說,那我們?nèi)シ侵揞I(lǐng)養(yǎng)一個(gè)小男孩,再去俄羅斯領(lǐng)養(yǎng)一個(gè)女孩,一黑一白,可拉風(fēng)了。
倪愛梅笑出小虎牙,我不反對(duì)。
丁德耀說,一家四口走在路上,就是小聯(lián)合國。
倪愛梅說,聽說領(lǐng)養(yǎng)小孩夫妻都要三十歲以上,我們年齡倒是夠了。
丁德耀說,你還真去孤兒院打聽了?
倪愛梅說,我連孤兒院在哪兒都不知道,上次你說要領(lǐng)養(yǎng),我就百度了一下。
丁德耀說,我開玩笑的,孩子還是得自己的,說著把倪愛梅扳過來,嘴巴湊近耳朵說,我來交公糧吧。
倪愛梅說,交了那么多年,交了也白交。
說雖那么說,等丁德耀翻身下來,她把雙腿高舉,屁股在上腦袋在下,腳掌頂住墻壁,這個(gè)動(dòng)作是婦科醫(yī)生教她的,精子更容易往身體深處游。
其實(shí),結(jié)婚第二年,她懷過一次孕,那時(shí)她對(duì)生育并不迫切,也不采取避孕,態(tài)度是順其自然,沒有不強(qiáng)求,有了就生。發(fā)現(xiàn)例假延遲,以為是沒休息好所致,大學(xué)畢業(yè)剛上班,舊同學(xué)新同事,業(yè)余活動(dòng)很豐富,丁紅就是這個(gè)時(shí)段認(rèn)識(shí)的朋友,她們在同一家城市銀行上班,過了兩年,丁紅跳槽去了一家日資保險(xiǎn)公司,友情保留了下來,至今還是最好的閨密。
等例假延遲了一個(gè)月,才意識(shí)到可能懷孕了。丁德耀陪她去婦產(chǎn)科醫(yī)院,檢查報(bào)告印證了猜測,醫(yī)生叮囑妊娠早期以靜養(yǎng)為主,忌冷忌辣增加營養(yǎng),她嘴里答應(yīng),仗著年輕沒當(dāng)回事,照樣嚼雪糕吃川菜,剛從鄰省旅游回來,聽說陳奕迅在開演唱會(huì),拽著丁德耀去體育場門口找黃牛,高價(jià)買了門票,這是她最喜歡的香港歌手,為了看現(xiàn)場,寧肯吃一星期方便面。
因?yàn)橛^眾的熱情,已揮手謝幕的歌手不斷返場,三小時(shí)演唱會(huì)延長了二十多分鐘,終于,舞臺(tái)燈光徹底暗淡下來,觀眾離場,倪愛梅挽著丁德耀去衛(wèi)生間,那兒站滿了膀胱憋上臉的人,丁德耀等了十分鐘,入廁解決了。倪愛梅候時(shí)更久,夾緊褲襠,快哭了。好不容易輪到,扭著屁股挪進(jìn)女廁,已不敢開胯。
過了片刻,慌里慌張出來:“奇怪,我大姨媽怎么來了。”
丁德耀說,不會(huì)吧,醫(yī)生明確說你懷孕了。
倪愛梅說,所以才奇怪啊,會(huì)不會(huì)誤診了。
丁德耀說,懷孕又不是疑難雜癥,怎么可能誤診。
倪愛梅啊呀一聲,那可能見紅了。
丁德耀說,什么是見紅?一驚一乍見鬼似的。
倪愛梅說,你們男人不懂,這時(shí)候見紅可能孩子就保不住了。
丁德耀也緊張起來,拉著老婆連夜去看急診,值班護(hù)士不讓掛號(hào),說見紅不屬于急診范疇,沒必要半夜跑來湊熱鬧,明天看門診吧。
次日一早又跑醫(yī)院,婦科醫(yī)生說,懷孕初期出血確實(shí)不是好現(xiàn)象,吃點(diǎn)黃體酮觀察一下。
丁德耀問怎么會(huì)產(chǎn)生這種情況。醫(yī)生說,可能是胎兒染色體異常,也可能是母體激素失調(diào)。倪愛梅說,對(duì)胎兒有什么影響?醫(yī)生說,說不好,有吃了黃體酮保胎生下健康胎兒的,也有早產(chǎn)兒畸形兒的,各種情況都有。
倪愛梅說,聽起來像冒險(xiǎn)。
醫(yī)生說,出血量大么?
倪愛梅說,蠻大的,懷孕了沒再用衛(wèi)生巾,流到大腿上了。
醫(yī)生說,血量這么大有點(diǎn)麻煩,一般的見紅也就是內(nèi)褲上沾點(diǎn)顏色。
丁德耀說,吃那個(gè)黃體酮有用么?
醫(yī)生一邊開藥方一邊說,看運(yùn)氣吧,醫(yī)學(xué)是模糊科學(xué),誰都不能保證結(jié)果。
夫婦倆領(lǐng)了藥,揣摩著醫(yī)生的話,越想越覺得風(fēng)險(xiǎn)大,商量了一星期,跑去醫(yī)院,還是上次那個(gè)醫(yī)生,丁德耀說,我們認(rèn)真考慮過了,放棄算了。
醫(yī)生也沒阻止,說了句,還在妊娠早期,做藥流吧,痛苦少一點(diǎn)。
倪愛梅去藥流室吃了藥,丁德耀扶她在病床躺下,自己坐在椅子上發(fā)愣。藥流痛苦比手術(shù)小,也不是沒痛苦,倪愛梅一會(huì)兒暈眩,一會(huì)兒干嘔,翻來倒去,臉色慘白,額頭滿是虛汗。
這次流產(chǎn)以后,就再?zèng)]懷上,有時(shí)候也會(huì)后悔,“如果當(dāng)時(shí)生下來,已經(jīng)上小學(xué)了。”倪愛梅嘆了口氣。
丁德耀安慰說,醫(yī)生說畸形兒可能性很大,萬一真是殘疾智障,豈不害人害己。
倪愛梅說,那也有百分之五十概率是健康孩子。
丁德耀說,誰敢冒這個(gè)險(xiǎn),還記得我們學(xué)校那個(gè)老魏么,生了個(gè)白癡兒子,被拖累那么多年,覺得日子沒奔頭,把傻兒子活活悶死,自己也自殺了。
倪愛梅吐出一串呸呸呸:“別拿這種晦氣事來對(duì)比,我們家孩子肯定健康聰明。”
丁德耀也跟著一串呸呸呸:“我們的孩子肯定健康聰明,菜場快打烊了,我去買菜了。”
倪愛梅說,快打烊了,綠葉菜最便宜,再買兩條帶魚。
丁德耀說,我去冬子家買,你說,這么機(jī)靈的孩子怎么就不投胎到我家呢,弄得書也沒的讀,真是可惜。
倪愛梅說,你這人真奇怪,對(duì)一個(gè)邋里邋遢的小魚販心心念念,身邊親戚朋友那么多小孩倒沒見你多提。
丁德耀說,還真別說,就是投緣,第一眼看到就喜歡,敦敦實(shí)實(shí)沒什么心眼,大眼睛里卻全是聰明。
倪愛梅說,你快去照照鏡子,說到冬子,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丁德耀配合著擦了下嘴角,冬子要是我兒子就好了,邋遢沒關(guān)系,洗個(gè)澡買幾套漂亮衣服一穿,就是小帥哥了。
倪愛梅說,你沒當(dāng)人家小孩面說讓他當(dāng)你兒子吧。
丁德耀說,說過啊,當(dāng)他媽媽面也說過,有一次他爸爸在,也說了。
倪愛梅說,人家要當(dāng)你人販子防著了。
丁德耀說,怎么可能,我這是變相夸他們兒子呢,他們開心還來不及。
倪愛梅說,要是別人這么夸我兒子,我肯定不愿意。對(duì)了,昨晚電視新聞里說,有個(gè)蜘蛛人摔死了。
丁德耀啊了一聲,但愿不是老潘,我去菜場了,除了帶魚,你還想吃什么?
倪愛梅說,買塊豆腐做麻婆豆腐吧,綠葉菜隨你,盡量挑新鮮的。
說這些話的時(shí)候,倪愛梅在看《中國式離婚》,丁德耀瞄了一眼,正好是他喜歡的女演員左小青——他平時(shí)喜歡讀閑書,很少看電視劇,有時(shí)倪愛梅叫他一起看,只好扔下書,摟著老婆看一會(huì)兒,這是丈夫的義務(wù)之一,美其名曰“陪伴是最好的長情”——就說了句,你看我們家小青,多好看。倪愛梅瞥他一眼,看著熒屏里出現(xiàn)的陳道明說,我們家道明才好看呢,帥死了。
丁德耀嘿嘿一笑,出了門,到了樓下給倪愛梅發(fā)了條短信,外面好像下雪了,收一下陽臺(tái)的衣服。
倪愛梅回了個(gè)哦字,去了陽臺(tái),天空中雨夾著冰粒,伸出手,冰粒在掌心跳一下,化了。
把收下的衣服攏在懷里,遠(yuǎn)眺陽臺(tái)外的黃昏,印象中,這個(gè)城市十年沒下雪了,當(dāng)然,現(xiàn)在還不是雪,只是雪的前奏,亦有可能,不會(huì)下一場真正的雪,即便下了,也未必會(huì)積起來,更不要奢望堆雪人打雪仗了。
朝下俯瞰,背有點(diǎn)微駝的丈夫出了小區(qū),羽絨服的附帽套在了腦袋上。她想叫一聲,讓他買兩只圓蘿卜。覺得可能聽不見,就咽回去,改成發(fā)一條短信。
丁德耀收到短信,回了“知道了”三字,折出小區(qū),往菜場方向走過去。
小區(qū)門外是一條被污染的河,前幾年還見人釣起過耐臟的黃顙魚,而今除了喂養(yǎng)金魚的水虱,恐怕沒什么活物了。
水虱最多時(shí)是初秋,河面邊緣染出一片鐵銹紅,撈水虱的網(wǎng)兜是自制的,網(wǎng)口蒙一層剛好讓水虱鉆過的細(xì)格紗,握著細(xì)長柄在岸邊走來走去,網(wǎng)兜像在擦洗一幅流動(dòng)的臟玻璃,鐵銹紅慢慢淡了,的確良材質(zhì)的網(wǎng)兜內(nèi),接近褐色的深紅透了出來。
過了橋,從“綠化山”右繞二百米,菜市場隱匿在一摞破敗老宅里,保存室內(nèi)溫度的塑料垂簾如同一條條冰掛,本是透明的,卻被摸得很臟,能粘住蔬菜的草腥和魚蝦的臭腥。丁德耀剛一撩垂簾,腳趾被人踩了一腳,剛要發(fā)作,發(fā)現(xiàn)正是老潘,想起老婆說昨天有蜘蛛人摔死了,情知不會(huì)那么巧是老潘,冷不防撞個(gè)滿懷,還是有點(diǎn)白天見鬼的感覺,一時(shí)說不出話來。
后面緊跟著潘冬子?jì)寢專〉乱徚丝跉猓瑔柕溃銈儍煽谧有募被琶θツ膬貉剑?/p>
老潘說,是丁老師啊,批發(fā)市場的哥們兒打電話來,說今晚有遠(yuǎn)洋漁船到岸,讓我早點(diǎn)過去挑點(diǎn)好的海鮮。
丁德耀說,天還沒完全黑呢,就趕啊。
潘冬子?jì)寢屨f,挺遠(yuǎn)的,騎黃魚車到碼頭要兩個(gè)多小時(shí)呢。
丁德耀說,冬子一個(gè)人守?cái)傃剑?/p>
潘冬子?jì)寢屨f,他自己會(huì)收攤回家,沒事的。
丁德耀說,那你們快去碼頭吧,我找冬子買兩條帶魚。
丁德耀撩開垂簾,把頭回一下,飄灑的雨絲間雜著冰粒,老潘的背影有點(diǎn)拖沓,潘冬子?jì)寢尩谋秤皠t沒有主見,丁德耀想象了一下蜘蛛人在半空中作業(yè)的畫面,進(jìn)了菜場。
潘冬子戴一頂雷鋒式帶護(hù)耳的棉帽,鼻孔一抽一抽,如同在泵兩只肥厚的氣泡。見丁德耀過來,忙把鼻涕擦在袖口上,丁德耀裝沒看見,天確實(shí)很冷,雖然門口掛了保溫的垂簾,也是聊勝于無的擺設(shè)。
他很少有和潘冬子獨(dú)處的機(jī)會(huì),多數(shù)情況下,他媽媽會(huì)在一旁,更多情況下,是他媽媽一個(gè)人守?cái)偅硕釉诟浇托∨笥驯寂苕音[——畢竟是小男孩,猴子屁股坐不住——最少的情況是一家三口都在,平日里,進(jìn)貨由老潘負(fù)責(zé),進(jìn)完貨送到菜場,還要做諸如敲冰塊等保鮮工作,然后吸幾口煙,再去當(dāng)蜘蛛人。所以,丁德耀在菜場見到老潘的次數(shù)不多,但老潘知道有這樣一個(gè)喜歡自己兒子經(jīng)常照顧自家生意的中學(xué)老師,每次見面,總憨厚地打個(gè)招呼,遞上一支煙。雖然是劣質(zhì)煙,丁德耀還是會(huì)接過來,點(diǎn)上抽幾口。
丁德耀看到有油帶魚,讓潘冬子抓了四條,心想多買兩條放冰箱里,油帶魚不常有的。
潘冬子說,我爸媽去碼頭進(jìn)貨了,丁叔叔下次多買點(diǎn)海鮮,快過年了,要備年貨了。
丁德耀說,我剛才在菜場門口碰到他們了。
他朝潘冬子的袖口看了眼,拉長的鼻涕像魚鱗發(fā)出銀光,男孩留意到他的眼神,按臺(tái)秤的手指羞澀了一下:“油帶魚煎著好吃,清蒸也好吃。”
丁德耀說,外面下冰粒了,今晚可能會(huì)下雪。
潘冬子說,真的么,我還沒見過雪呢,那我早點(diǎn)收攤?cè)タ囱?/p>
丁德耀說,我先去別的攤位轉(zhuǎn)轉(zhuǎn),你幫我把帶魚剪一下。
說著,去別的攤位買蘿卜豆腐和綠葉菜,潘家魚攤是進(jìn)出菜場的必經(jīng)之地,等他繞完一圈,潘冬子已在收攤,見他返來,興奮地說,丁叔叔,真的下雪了,我出門看過了。
丁德耀說,真的下雪啦,我也很多年沒看見雪了。
潘冬子說,我出生的那個(gè)冬天我媽說很冷,給我起名冬子,可我連雪都沒見過,還叫什么冬子。
丁德耀說,要是下一個(gè)晚上,雪就能積起來,望出去一片白皚皚,可漂亮了。
潘冬子說,要是真積起來,丁叔叔陪我堆雪人吧。
丁德耀說,怎么不讓你爸爸陪你堆雪人呀?
潘冬子說,爸爸去碼頭進(jìn)貨,不知道什么回來呢,再說,我們關(guān)系好嘛。
我們關(guān)系好,這個(gè)理由好,丁德耀笑了,明天雪要是積起來,一早找你堆雪人。
潘冬子笑起來很像小游擊隊(duì)員潘冬子,說,謝謝丁叔叔。
下雪的消息很快成為電視臺(tái)的熱點(diǎn)新聞,晚餐時(shí)間,廚房里的油煙味尚未散盡,小餐桌旁的丁德耀吃著香煎油帶魚,臥室里的電視傳出一句“市民喜迎十年以來的第一場春雪……”
他吐出一段魚骨,捧著飯碗去陽臺(tái),張望之處,皆覆了一層灰白,回到餐桌坐下,對(duì)老婆說,看樣子雪不會(huì)停,明早要是積厚了,我找冬子堆雪人去。
正用調(diào)羹舀麻婆豆腐的倪愛梅看了眼丈夫:“真把冬子當(dāng)兒子了?人家爸爸不會(huì)陪他?要你陪。”
丁德耀說,冬子說我們關(guān)系好,我就答應(yīng)他了。
倪愛梅說,讓你看場電影半年都沒空,倒有時(shí)間陪人家小孩堆雪人。
丁德耀說,早上堆雪人,下午請(qǐng)你看電影。
倪愛梅把一勺麻婆豆腐放進(jìn)嘴里:“這么不誠心,誰稀罕你的電影。”
次日早晨,丁德耀光腿爬出被窩,跑到陽臺(tái)上,戶外已是銀裝素裹,忙又跑回來,鉆進(jìn)被窩,被倪愛梅手肘一頂:“要死,冰棍一根抱住我。”
他嬉皮笑臉道,你半夜撒完尿不也冰棍一根抱住我。
倪愛梅說,只有老公給老婆暖被子的,哪有反過來的。
丁德耀說,外面雪積起來了,我起床去堆雪人了。
倪愛梅說,這事倒記得牢,你愛去不去,我睡個(gè)回籠覺。
丁德耀說,也不單單去堆雪人,昨晚冬子爸媽去碼頭進(jìn)海鮮,我去挑點(diǎn)好的,快過年了,該備年貨了。
倪愛梅說,那你別只買海鮮,也買只雞買只鴨,再買只蹄膀,總要把冰箱塞滿。
丁德耀說,喲,老婆大手筆。
倪愛梅說,貧嘴,對(duì)了,下午看電影真的假的?
丁德耀說,當(dāng)然真的,大丈夫一言駟馬難追。
倪愛梅說,還駟馬難追,你這是瘸腿馬吧,沒結(jié)婚就說帶我去新馬泰,到今天還是空心湯團(tuán),你這騙子。
丁德耀說,明年是我們結(jié)婚十周年,保證帶你去新馬泰。
倪愛梅說,還記得結(jié)婚快十年了呀,不容易。
丁德耀說,我記得結(jié)婚前一年,就是認(rèn)識(shí)你的那年冬天,下過一場雪,后來再也沒下過雪。
倪愛梅說,那場雪挺大的。
翻了個(gè)身,開始睡回籠覺。
丁德耀起床,刷牙洗臉。十分鐘后出了門,戶外很冷,卻沒有室內(nèi)想象的那么冷,小區(qū)空地有不少人,一看就是來賞雪的,有些撐傘,有些跟丁德耀一樣,只是戴著羽絨服的附帽。綠化帶旁有大人帶著孩子在堆雪人,并且堆好了一個(gè)。社區(qū)里所有的小孩可能都出來了,他們應(yīng)該都是第一次邂逅雪,也是第一次打雪仗,捏了雪塊砸小伙伴的同時(shí),也順便砸湊熱鬧的狗貓,把它們嚇得四處逃竄。
顯然,這場久違的春雪被賦予了節(jié)日的意味。十年一遇的天象宛如月全食一樣珍貴,丁德耀心想,整個(gè)城市應(yīng)該陷入了狂歡。
從河邊經(jīng)過,靠近岸邊的河面結(jié)冰了,把漂浮的垃圾封住,河中央有反光的薄冰,偶爾駛過的小船像犁剖開水面,將薄冰卷入河水。
過了橋,丁德耀買了兩只香菇菜包、兩只肉包,菜餡是自己吃的,肉餡是帶給潘冬子的。剛出爐的包子,放進(jìn)嘴里皮已微涼,餡是熱的,丁德耀咽得急,有點(diǎn)噎住,以至于碰到潘冬子時(shí),還在打嗝。
撩開如同冰掛的塑料垂簾,蔬菜的草腥和魚蝦的臭腥令丁德耀皺了下眉,他手勢僵硬,被掀動(dòng)的垂簾擊中了耳垂。菜場門口可以望見潘家魚攤,老潘一家三口都在,潘冬子和父母一起理貨,一邊理一邊朝門口方向張望,看見丁德耀出現(xiàn),樂滋滋跑過來,丁德耀忙擺手:“不要跑,地上滑。”
話音剛落,小男孩被流淌的冰撂倒了,他立刻翻身起來,動(dòng)作流暢,如同完成一個(gè)雜技。
丁德耀已走到跟前,把肉包遞給他,潘冬子接住,往嘴里塞,丁德耀知道肉包已完全冷了,小男孩吃得很香,一邊吃一邊說,我早上吃過了,不過我又餓了。
丁德耀說,小孩子長,長身體,容,容易餓。
潘冬子笑了,丁叔叔打嗝了。
丁德耀說,是啊,吃包子吃快了。
在砸冰塊的老潘直起腰來,丁老師這么客氣,還買包子給冬子吃。
丁德耀說,看你們眼睛都是血絲,昨晚沒怎么好好休息吧。
老潘說,春節(jié)前最后一艘遠(yuǎn)洋漁船,拿貨的人很多,像搶一樣,我們也是剛回到菜場。
說著拿出一包中華煙,遞給丁德耀一支:“為拿點(diǎn)好貨,買了兩包高檔煙,一包送掉了,這包還剩幾支沒發(fā)完。”
丁德耀接過煙,看看泡沫盒子里的海鮮,給我挑點(diǎn)吧,大黃魚大明蝦烏賊魚都挑,挑一些,準(zhǔn)備過年了。
潘冬子說,我來挑,給丁叔叔挑最好的。
丁德耀說,我再去買,買點(diǎn)別的,待會(huì)兒去堆雪人。
潘冬子?jì)寢屨f,丁老師要帶冬子去堆雪人呀,比親叔叔都好。
丁德耀說,冬子說他是第一次見到雪。
潘冬子?jì)寢屨f,我們老家倒是每年下雪,冬子生在這里,出生以后就沒下過雪。
丁德耀說,是啊,十年沒下過雪了。
潘冬子咽下最后一口包子:“等我長大了,開個(gè)包子店,用魚蝦的肉做餡,肯定生意好。”
丁德耀看一眼潘冬子,覺得這孩子開悟早,會(huì)動(dòng)腦筋,雖沒讀過書,長大未必沒出息,很多大老板也是文盲,所謂的草莽英雄。但他還是有點(diǎn)遺憾,要是能讀點(diǎn)書,總是錦上添花的,可惜他說服不了潘冬子父母。
等他買完雞鴨蹄膀,潘冬子已把魚蝦挑好,分別裝在馬甲袋里。他把錢付完,食材寄存在魚攤,帶著潘冬子出了菜場。
“綠化山”同樣聚集了很多賞雪的人,雪地上踩滿了腳印,打雪仗的小孩在追逐,成年人沿著被白雪遮蔽的草坪行走。
綠化山是俗稱,學(xué)名刻在山腳下的銅牌上:“固體廢棄物封閉處理中心”,其實(shí)這是一座環(huán)保式垃圾處理站,只不過穿了個(gè)綠樹成蔭的外套。說是山,不過是個(gè)土丘,順著石階上去,三四分鐘就到頂了。
我們上去堆雪人吧,丁德耀說,上面的雪應(yīng)該厚一些。
潘冬子說,堆好雪人,我要回去守?cái)偅尠謰尰丶宜粫?huì)兒。
丁德耀說,進(jìn)個(gè)貨,怎么進(jìn)了一個(gè)通宵?
潘冬子說,說是下雪了風(fēng)大,漁船好不容易才靠上碼頭。
丁德耀說,你爸媽很辛苦。
潘冬子說,勞動(dòng)人民哪有不辛苦的。
聽到“勞動(dòng)人民”四字,丁德耀一愣:“你哪兒聽來的勞動(dòng)人民?”
潘冬子說,我爸常說自己是勞動(dòng)人民,等我再長大點(diǎn),他們就不辛苦了。
丁德耀說,你還是應(yīng)該去讀書。
潘冬子說,丁叔叔,告訴你一個(gè)秘密,其實(shí)我很想讀書的,但那樣我爸媽就更辛苦了。
丁德耀說,你想讀書我跟你爸媽去說呀。
潘冬子說,你別說,說了我也不承認(rèn)。
丁德耀鼻子一酸,覺得要流鼻涕了,天氣確實(shí)很冷,土丘頂上比地面更冷一些,一塊平坦的雪地呈現(xiàn)在眼前,只有一個(gè)老頭在打太極拳,很多樹被雪壓得直不起腰來了。
潘冬子說,丁叔叔你堆過雪人么,我不會(huì)堆。
“很容易,我來教你。”丁德耀揭起一片雪,雪厚半寸,慢慢往前滾,說也奇怪,竟蛋卷般卷了起來,草坪露出一長條青黃,丁德耀把雪柱豎起來,摘去附在表面的草葉和細(xì)枝,潘冬子很興奮:“我也要卷一個(gè)。”
俯身學(xué)著丁德耀的手勢,如法炮制了一個(gè)雪柱,也把草葉和細(xì)枝摘去,丁德耀說,你這個(gè)小一點(diǎn),把它捏成圓的,當(dāng)腦袋吧。
潘冬子又拍又捏,要把雪柱弄成圓球,卻怎么也弄不圓,雪看似綿軟,很難塑形,稍用力就僵住,接近冰的硬度,要巧勁輕拍,不是猛捏。
不管怎么樣,一刻鐘后,雪人做好了,樣子并不美觀,丁德耀摘下眼鏡給它帶上,讓它叼了支煙,潘冬子取下帶護(hù)耳的雷鋒式棉帽,給它戴上。
丁德耀說,別脫帽子,著涼了頭疼。
潘冬子說,戴一會(huì)兒,它戴著挺好。
雪花越來越大,沒有停的意思。潘冬子一激靈,連打了兩個(gè)噴嚏,兩只手倔強(qiáng)地掛在身體兩側(cè),而不是插進(jìn)褲兜里,臉龐發(fā)皴,眼睛和鼻子也凍紅了。
丁德耀把雷鋒式棉帽取下來,戴在小男孩腦袋上:“雪人堆完了,你回去守?cái)偘伞!?/p>
潘冬子說,要是有個(gè)照相機(jī)拍下來就好了,這是我堆的第一個(gè)雪人。
丁德耀說,叔叔倒是有個(gè)照相機(jī),忘記帶了。
潘冬子說,算了,我堆過雪人了,我用眼睛把它拍下來了,記在腦子里了。
丁德耀把眼鏡取回,重新戴在鼻梁上,潘冬子回頭注視,發(fā)現(xiàn)多了一個(gè)雪人,打太極拳的老頭也變成雪人了。
潘冬子說,丁叔叔,雪好像變大了。
丁德耀說,我也發(fā)現(xiàn)了,我們回去吧。
石階已看不出原有的大理石顏色,一格一格的輪廓消失了,變成了一個(gè)坡度。丁德耀眼鏡和鼻子上沾滿了雪,潘冬子睫毛上也是雪,眼睛快睜不開了。
丁德耀牽著小男孩,打太極拳的老頭尾隨在后面。
由于石階不再明晰,視覺的作用已經(jīng)不大,只能依靠腳的觸感,所以往下走的速度很慢,好不容易來到“山腳”,發(fā)現(xiàn)馬路上的人都消失了,鞋子踩下去剛提起來,鞋印就被雪吃掉了。
有個(gè)老婦走不動(dòng)了,像固定在座基上的雕像,想呼救卻發(fā)不出聲。丁德耀留意到小男孩在看自己,眼神里有點(diǎn)驚慌。
當(dāng)他把潘冬子送回菜場,透明的塑料垂簾一撩就斷了,他取回裝著食材的兩只馬甲袋,跟老潘夫婦匆匆道了別,就往家里趕。
手完全凍僵了,緊握的掌心仿佛和馬甲袋長在了一起。走到橋堍時(shí),雪的厚度已沒過了腳踝,丁德耀擔(dān)心按這個(gè)速度,很快會(huì)齊到小腿,回到家時(shí),膝蓋說不定都拔不出來了。
走到橋中央朝河面看,一只過境的小船被凍在了漫天大雪里。回望菜場那邊,一間老舊的瓦房被積雪壓斜,猛地匍匐在地,揚(yáng)起了一團(tuán)塵土。這場雪宛如積攢了十年的仇恨,要完成一次復(fù)仇。他也從迎接一場春雪的歡喜,變成了對(duì)雪的恐懼,他覺得有點(diǎn)對(duì)不起倪愛梅,心里說,老婆對(duì)不起,今天電影又看不成了。
他終于走進(jìn)了小區(qū),一棵老樟樹歪在門洞之側(cè),肥厚的雪從樹冠上塌下來,砸得他滿頭滿臉,順著羽絨服的附帽落到背上,他像水獺一樣抖一抖,把雪抖掉了。
【責(zé)任編輯】 于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