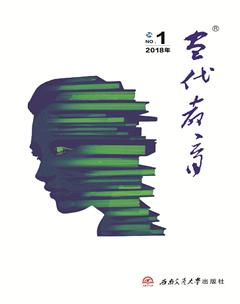追逐地平線
肖光豁
二月,和風送暖,收到好友岳德彬先生郵來他的詩文選《今生有約》。
他的詩集《行吟都柳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版了。那時的他,遠離故土,在黔東南的一個縣打拼,是一個真正的行吟者。
我和德彬交往多年,知之較深。年輕時,他讀高一,我讀初中,他高我兩級;文革突來,我們便都輟學了。之后,我們顛沛流離,各自東西。1970年,我們一起上了湘黔鐵路當民工。不同的是,他文質彬彬,被干部們看中,專事宣傳工作;而我,不修邊幅,只能老老實實地下苦力。
為此,我曾經調侃過:德彬在文人眼中是文人,在文盲眼中還是文人;我呢?在文人眼中是文人,在文盲眼中就是文盲。
十年文革,我認認真真地學了好多種手藝;德彬則不同,一直認認真真地在文學路上追逐著。在當時,那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我以為,那是在追逐地平線,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的地平線。
吃著素菜南瓜糙米飯,穿著薄衣單褲破膠鞋,追逐著朝暉落霞白云蒼狗,尋找著智慧禪機菩提樹。他沒有放棄過文學。
西邊的地平線,是以往;東邊的地平線,是未來。那時的德彬,對于文學,應該是一種出自天然愛好的追逐,他在努力地追。
終于,1978年,他的第一首詩歌《金秋賦》被刊載在《貴州日報》上。那時,他依然是一個食不果腹的代課教師。
后來,我高考成功進入高校,有了穩(wěn)定的工作,德彬卻還在艱難中。我們都不安分,八十年代初,我離開了故土來到安順,他也離開了故土去了黔東南,然后又于九十年代來到安順,我們又在安順重逢。
他當過縣文聯(lián)主席、當過記者、當過報刊編輯,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
讀著他的詩歌,你可以讀得到字句間豐滿地浸潤著的古文功底,請看他的《金秋賦》里的兩句:
鋤禾,禾苗在咱心上綠
抗旱,河水在咱肩上流
讀他的詩歌,你便讀得到蠕動于作品中的靈魂,或張揚奔放,或深沉思考,或熱情歌唱,或輕聲悲吟……
再看看他的《雨夜憶亡母》:
一層薄土
兩個世界
從此母子相隔
唐
宋
元
明
清
不知詩人出于何種考慮,這兩首詩都沒有選入本集子中,只是,我永遠記得。前一首給我的感覺是美麗,后一首給我的感覺是震撼。
作為詩人,思維可以上天入地、可以追索洪荒,也可以匯入人群、可以宏觀天下,也可以微觀毫末。
請看《翠翠》,詩人將沈從文筆下的人物翠翠錄入詩中,關注其命運走向,只是時代變了,翠翠的渡船也變成了中巴,工具不同,命運卻相似——
山南海北的游客
站在爺爺翠翠和狗的小小渡口
癡癡迷迷地遙想遠遠的那個翠翠
卻不認得站在眼前的翠翠
是誰
散文詩《探秘都柳江》中的“都柳江,因你岸邊那不屈不撓的根,因你熬著漫長等待的沙灘,因你預埋風險的流程和推動木筏的白浪,還有播種愛恨情仇的山歌,我深深摯愛你”——將大自然、大環(huán)境與人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解讀。
《落日》一詩中“在最后一抹殘紅泯滅的剎那/不管算起點還是算終點/都是我的一場血祭”;《空椅》感慨人生:“償還由來已久的宿愿/有一種情結/在時間和空間的化境里心無旁騖”、“忘記才好/既在紅塵之中/又在紅塵之外/空即是有/人眼中的不存在便是你的存在”——將佛學境界化而入詩,更賦以新意,寫出了生命體悟和靈魂色彩,內涵深,張力大,語言優(yōu)美,遠非那種辭藻華麗的無病呻吟可比。
書中還有幾篇德彬寫的文學評論,都很精彩,切合所評作品的實際,因為評論者就是詩人。“內行看門道”,那些詩評本身就是一篇篇美文。
無論是詩詞歌賦還是散文小說,最要緊的不是字句的華麗洗煉,而是作品的靈魂。而作品的靈魂則不是輕易可得的,我以為,真正的佳品,只能在冰與火中方能拾掇得到。
有句話說得好:苦難是一種財富。德彬富有這種財富,曾經酸甜苦辣,曾經走投無路……
當然,有了這種財富,也不一定能夠成為詩人,在這個問題上,我比較贊同清代詩人袁枚的“性靈說”。袁枚認為詩人須有靈性,德彬就具有這種靈性。
我們需要在德彬身上學習的,是他的勤奮與努力;我們需要追比的,是我們的同行者的勤奮與努力。
如今,德彬已經退休,作為一個詩人,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追逐著,追逐那一道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的地平線,這也許是一個詩人的宿命。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詩人在追逐,當今的詩人們也在追逐,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追逐,正是這種一代代的接力追逐,造就了中國詩歌的偉大殿堂。
追在最前面的人,不經意間,成為了后面追逐者的地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