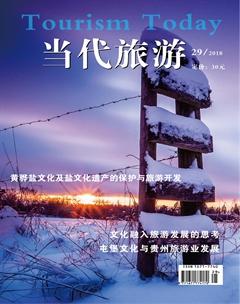從傳播學視角淺析武漢科技館新館科普工作
連瑛
摘要:科技館發揮科普陣地作用的過程,也是大眾傳播的過程,在這個傳播系統中,科技館是傳播主體,文字、圖片、語音導覽、展品等組成媒介,傳播內容為科學知識,受眾即為參觀觀眾。武漢科技館新館展陳設計符合議程設置,微信作為新媒介也運用到科普工作中,通過受眾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有針對性的開展科普活動。
關鍵詞:傳播學;武漢科技館新館;展陳設計;議程設置;微信;使用與滿足;科普活動
傳播學對于傳播的定義是,傳播即社會信息的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人類社會傳播是一種信息共享活動;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進行的,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是一種雙向的社會互動行為;傳播是一種行為,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系統。
科技館是面向公眾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思想和方法、倡導科學精神,提升公眾求知、探索和創造的能力以及增強科技進步意識的重要教育場所,在傳播活動中是傳播主體,其受眾為廣大入館參觀的觀眾。在科技館傳播活動中,文字、圖片、電子屏、展品……組成了復雜而多樣的媒介系統,傳播內容則是豐富多彩的科學知識。
武漢科技館新館(以下簡稱新館)2015年12月28日建成開館,設有交通、數學、信息、光、兒童、宇宙、生命和水八大展廳,共有500余件(套)展品。通過常設展覽、臨時展覽、科普劇表演、科普講座等各類科普活動,共接待觀眾近400萬人次,形成一套完整、復雜、豐富的傳播系統。
一、展陳設計中的“議程設置”
議程設置理論來源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對選舉中媒介作用的研究,基于兩個觀點:第一,各種媒介是報道世界上重大事事件不可少的“把關人”;第二,人們需要由“把關人”幫助決定那些超出他們感受的哪些事件和問題是值得關心和注意的。即大眾傳媒不能決定人們如何想,但可以左右人們想什么。
科學知識上至浩瀚星空、下至汪洋大海,古往盤古開天,新至高新尖端……如何在知識的汪洋中選取具有傳播價值、易于受眾接受的重點知識,形成各展廳系統?多位院士、專家、學者組成的專家組在新館展陳設計之初,成為“把關人”,把關篩選展示內容,最終形成基礎學科、前沿科技與武漢地域特色、產業特點相結合的展陳格局。
觀眾一走進新館,序廳一棵高達18米的“天問之樹”馬上成為其關注的焦點。“天問之樹”設置成楚文化圖騰形象——展翅鳳凰,隱喻人類自古以來對自然宇宙的探索求知精神;新館比鄰長江,水展廳是國內科技館中獨一無二的特色展廳,通過議程設置,既體現了武漢這座江城的城市特色,又傳播了水作為生命之源的諸多科學知識;交通展廳將人類水、陸、空交通發展軌跡與武漢“九省通衢”成果相結合,展項“汽車的構造”是一輛拆解的東風雪鐵龍轎車,既能讓觀眾獲得汽車相關知識,又能宣傳武漢重點產業。
議程設置使科學知識和武漢特色成為觀眾學習、研究、關注的焦點。
二、微信是科普傳播的新媒介
微信已成為國內覆蓋面最廣的通訊介質。與碎片化、私人化的微博傳播相比,官方微信號更強調專業性和公共性。新館微信公眾號是場館展覽、教育活動的一種延伸和拓展,是在場館外、在線上拉近觀眾與新館距離的新媒介。
新館微信公眾號主要推送以下三種類型消息:第一類是近期活動推介,如“探究式教育活動‘小小建橋師開始報名啦!”、“科學秀《大力士‘帕斯卡》開演”等,這些活動消息一經傳播,馬上獲得不少觀眾留言報名,大大提高觀眾的互動性和參與性;第二類是最新科技資訊,如“美國重奪超算TOP500第一,中國還有反超機會嗎?”緊跟前沿消息,進行權威解讀;第三類是趣味性強的科普文章,如“全國首份蚊子預警地圖:今晚這些地方或將陷入‘人蚊大戰”,這些文章兼具趣味性和科學性,引發觀眾留言討論。
三、觀眾的“使用與滿足”
“使用與滿足”理論研究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是把受眾看做有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是基于特定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該理論從受眾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受眾接觸媒介的動機及接觸后滿足了什么需求,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
新館開館以來,三年多的時間共接待觀眾400余萬人次,觀眾重復率達到13%以上。觀眾們反復多次來到新館,為滿足求知、娛樂的需求,在調查中發現,不少學生觀眾來新館參觀次數多達7、8次,將新館作為“第二課堂”,成為學校學習的一種有益補充。觀眾意見調查還發現,宇宙展廳是最受觀眾歡迎的展廳之一,據此,新館在宇宙展廳開發“宇宙小課堂”科普活動,以“萬維望遠鏡”展項為介質,傳播更有深度的天文知識,有針對性的滿足對天文十分熱愛的觀眾的深層次需求。
2018年,中國科普研究所對湖北省科學素質調查結果顯示,武漢市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達11.8%,位于全國同類城市前列。新館為推動武漢科普事業發展發揮巨大作用。作為傳播主體,新館要進一步研究受眾的更深層次需求,采用多種媒介,有針對性地開發更多科普活動,使得新館這一套傳播系統更加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J],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楊志斌,從傳播學視角淺析合肥市科技館天文活動的成功要素,中國科普理論與實踐探索[M],451-457.
[3]許艷、曾川寧,對科技館的“使用與滿足”研究——以江蘇科技館“引力波”主題活動為例[J],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2016年第3期,28-32.
[4]彭思雅,微信:科技館科普教育傳播的新渠道[M],中國科普理論與實踐探索[D],389-395.
[5]林堅,科技傳播中的信息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