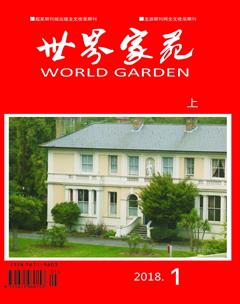淺議沈家本輕刑思想之來源
摘 要:沈家本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學家,是我國法律現代化的奠基人。沈先生博聞強記,遍覽歷代法制典章,刑獄檔案,對中國古代法律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對中國古代法制發展的源流和利弊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他悉心研究法律之時,正是中華民族危難之際。其輕刑思想是晚清律法變革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借鑒各國先進立法的結果。
關鍵詞:沈家本;輕刑思想
一、愛國情懷
沈家本專心研究法律之時,正式中華民族內憂外患,危機加深之際。1884年,法國侵略者在越南、臺灣屢次挑起戰端,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對法宣戰。對這次戰爭,他深為憂慮,曾寫詩明志:“時危競上平戎策,戰苦難擎飲至杯;九省兵戈方未艾,籌邊慎莫付庸材。”可以說,這種愛國之情、憂國之心正是沈家本窮究法律的精神動力所在。也是他極力主張輕刑的根本出發點。
二、參照援引古法
沈家本在修訂《大清新刑律》,對刑法進行革新,特別是在改革刑罰的過程中常常回顧前朝之法,參考前人之說,重新探究古之律法。他對于刑罰的看法也來自于此的研究,認為慎刑自古就有。“夫刑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不慎。”[1]
對秦的苛法是極其反對,無疑是使之滅亡的原因。
對漢律的平恕和嚴苛時期做了總結評價,認為平恕時期人俗和平,屢有嘉瑞。而嚴苛時期則是冤案較多,漢代最終滅亡也不免于嚴苛的律法有關。他在《漢律摭遺》中寫道:“漢初除秦苛法,秦人喜悅。其后參用秦法,亦尚因乎時之宜。而孝惠除挾書律,除三族罪、妖言令。孝文除收孥相坐律,除誹謗訞言法,除秘祝,而除肉刑一事,尤為古今刑法之一大關鍵。孝景之世,亦務在寬。故其時禁網疏闊,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此為漢法最平恕之時。其時用法者,張釋之、張驅諸人也。洎乎孝武之世,公孫弘以《春秋》繩臣下,主父偃、郭解之獄,其罪重至于族,并不知于律為何條? 張湯、趙禹之徒,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寢密。用法之吏,唯以武健嚴酷為能,久之遂成為風氣。此漢法最苛急之時也。孝昭時,霍光輔政,與民休息,而用法仍嚴,蓋習見武帝時之苛急,而不知其非,徐仁、王平之獄,尤為失當。孝宣時,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獄刑號為平,然趙、韓、楊、蓋諸獄,人尚冤之。孝元有蠲除輕減之詔,孝成 有議減死刑之詔。孝哀有除誹謗詆欺法之詔,其時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光武中興,議省刑法...明帝用法苛切。章帝納陳寵之言,除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是后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和帝時郭躬、陳寵相繼為廷尉,用法務存寬厚。此又漢法平恕之時也。安、順以后,政治日非,黨錮獄興,誅鉏正士,用法之權,操之閹寺,而漢亡矣。”[2]采信漢文帝的看法,認為不正之法,反害于民。又如“漢承秦苛法之后,慎獄恤刑,與民更治,高景之詔,尤于疑獄鄭重言之,而以寬為先務。文景之時,幾于刑措。”[3]
在對于先代律法的研究,以唐律為尤。先生對于唐律大部分是贊同的,對唐律的體系,刑罰的輕緩程度也是認可的。故在多本著作中屢次提到唐律。在修訂《大清新刑律》的過程中,認為刑罰應該與唐律相當。在《刪除律例內重法折》中強調“且刑律以唐為得中,而唐律并無凌遲、梟首、戮尸諸法。”[4]還有“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三十九人。刑輕而犯者少,何其盛也?”[5]認為唐代的興盛,犯罪減少無不與輕緩刑罰的做法有關。又用遼的律法的殘暴與之作了對比,“遼起朔方,以用武立國。太祖之世,刑多酷慘,穆宗性尤好殺,天祚荒暴,遂至于亡。與唐代相考鏡,其仁與暴何適相反也。....后之監古者,當如唐之仁,毋若遼之暴,斯可矣。”[6]對遼律法的殘暴進行了批評。
三、參考外國之法,世界趨勢
沈家本除了探究先代律法之外,還潛心研究外國的法律。在研究各國法律時發現“復詳加考核歐美、日本各國死刑,從前極為慘虐,今年則日從輕減,大約少者止數項,多亦不過二、三十項。”[7],得出這樣的結論:“方今環球各國,刑法日趨于輕,廢除死刑者已若干國,其死刑未除之國,科目亦無多。此其故,出于講學家之論說者半,出于刑官之經驗者半,亦時為之也。今刑之重者,獨中國耳。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其優絀之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8]說明海禁大開以后的中國,萬難固守祖宗成法而不變。在各國刑罰已經逐步輕緩化,去除了嚴苛殘忍的刑罰之時,中國卻仍然存有大部分苛罰,與當時世界的發展趨勢不相符合,也無法以一國之力來抗衡這樣的趨勢。“中國人同此稟賦,不應獨異。”[9]所以應當“大率于新法未布,設單行法,或淘汰舊法之太甚者,或參考外國之可行者,先布告國中,以新耳目。是以略采其意,請將重法數端,先行刪除,以明示天下宗旨之所在。”[10]對嚴厲的刑罰進行改革,以適應世界的趨勢。中國應該“規時勢,度本末,幡然改計,發憤為雄,將必取人之長以補吾之短。”[11]
他還把中國與日本相比較,“近日日本明治維新,亦以改律為基礎,新律未頒,即將磔罪,梟首,籍沒,墨刑先后廢止,卒至民風丕變,國勢駁駁日盛,今且為亞東之強國矣。”[12]先指出日本經減緩刑罰的改革后,國力興盛,后又指出“中,日兩國,政教同,文字同,風俗習尚同,借鑒而觀,正可無庸疑慮也。”[13]這也是中國改革刑罰可參考日本的原因。
在順應世界趨勢,參照他國法律的同時,他指出:法律應該伴隨今昔形勢的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應該把中國置于世界的范圍以內,進行考察。引進西方法律時,反對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法律,他說:中國“禮教風俗不與歐美同,即日本為同洲之國,而亦不能盡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14],將會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會而能之,以推行于世”。[15]所以當岡田朝太郎博士認為“各國之中廢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廢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種之執行方法。今中國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猶認斬絞二種,以抗世界之大勢,使他日刑法告成,外人讀此律者,必以為依然野蠻未開之法。”[16]之時,沈家本完全沒有贊同,而是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四、知民眾之疾苦
若僅僅只是參考古今,博稽中外,還是不夠的。因為刑罰的適用者絕大多數是黎明百姓,苛刑的直接受害者也是他們,一個國家的根基還是在于他們。所以國家應該“斯民罕觀慘苦情狀,足以養其仁愛之心”[17]。減緩刑罰,使受刑者不遭受殘忍的刑罰,民眾看不到這樣的酷刑,以此來促成他們的仁愛之心,那么國家就會穩定,犯罪自然就會減少了。
五、結語
清末刑法變革的目的是為了自強救國,但是此思想的內涵也體現出清末法律變革不可避免的順應著歷史發展的潮流向現代化演進。雖舊朝已逝,但對今之刑法的發展研究仍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2]、[3] 沈家本:《漢律摭遺》,載《歷代刑法考(三)》,中華書局1985年版。
[4]、[7]、[8]、[10]、[11]、[12]、[13]、[14]、[16]、[17]沈家本:《寄簃文存》,載《歷代刑法考(四)》,中華書局1985年版。
[5]、[6]沈家本:《歷代刑法考(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
[9]《修訂法律大臣奏請變通現行律例內重法數端折》,《大清法規大全 法律部》卷三。
[15]沈家本:“薛大司寇遺稿序”,《歷代刑法考(四)》,中華書局1985年版。
作者簡介
吳兆熙(1993-),女,江蘇南京人,北京市中銀(南京)律師事務所律師,本科學歷,主要從事刑事辯護業務。
(作者單位:北京市中銀(南京)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