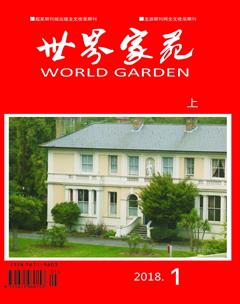論黃公望淺絳山水畫的生命意識
黃舒婷
摘 要:黃公望是元代四大家之首,他的山水畫可以分為水墨山水畫和淺絳山水畫。其中淺絳山水畫的設色技巧主要是在水墨勾皴點染的基礎之上再施以朱紅色為主的淡彩,這樣的畫法設計使得淺絳山水畫呈現出一種素雅高潔又不失明亮透徹的畫境。淺絳山水畫的發展傳到黃公望時期,又有了新的創新,本文選取了黃公望幾幅淺絳山水畫代表作來論述其中的生命意識。
關鍵詞:黃公望;淺絳山水;生命意識
中國傳統哲學強調對真、善、美的追求,受其影響中國傳統美學也講求對生命本質的探尋,重視對“人”的主體追問,推崇并追求“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本真”存在的審美領域。這里的“本真”突出地呈現出一種個體性、真實性。而這種個體的真實也正是中國傳統美學所推崇的最內在的特性。黃公望強調畫作要力求自然之美,堅決抵制矯揉造作。在《寫山水訣》中也有提到去邪甜俗賴。在董其昌1596年《富春山居圖》的題跋中寫到:“唯此卷規摹董巨,天真爛漫,復極精能,與摩詰《雪江》共相映發”。黃公望的山水畫作分為淺絳山水與水墨山水,在創作中,他將這種對自然美的追求突出地體現在對生命精神的訴求與對“本真”生命域的推崇中。淺絳山水畫的畫法素雅清單,明快透徹。在添加了足夠的墨色以后,稍微施加一點清麗的色彩,使得畫面的色調單純又融合統一,這樣的處理減輕了輕重和濃淡的層次變化,而這種色彩的處理尤其適用于表現江南地區特有的秀麗明快的景色,同樣也和大多數所追求的簡單的審美情趣相吻合。
隋唐以來,山水畫的用色向來濃郁艷麗,表現的形式分青綠和水墨。自唐代王維創立了水墨法以來,水墨的發展變化使得山水畫有了更長遠的進步,尤其是到了元代,水墨的因素更是被畫家們發揮到了極致。由于時代的發展、審美標準的轉變等多種因素,青綠山水的畫法在狀法、抒情和傳達意趣等方面受到了較多的束縛,因此淺絳山水運用與發展就得以推廣。淺絳山水畫是先以水墨勾皴點染,再敷上以赭石為主的淡彩山水畫,這類的手法主要用于表現南方山水的土石山峰。
《天池石壁圖》是黃公望淺絳山水畫的代表作,是黃公望在73歲時所作的畫。畫面描繪的是蘇州以西30里的天池山勝景。畫面的左邊有三棵巨大的松樹聳立在一旁,旁邊間有些許雜樹,隱約可見遠處的茅屋。畫面的主體部分一大山層層盤桓而上,石壁陡立在池水右側,池中有一座小橋閣,飛流直下的瀑布似從云煙中傾瀉而出,浩浩蕩蕩來到畫面之上。整幅畫面的線條和皴筆極其簡約,但畫面的構圖卻看似繁復。山岳的主體部分以赭石打底,墨青、墨綠著筆,層層渲染,烘托出高低、遠近的層次。畫中描繪重巒疊嶂的山川景色、山巒起伏,山峰雄渾華滋,充分展現了黃公望獨具匠心的大家風范。張庚在《圖畫精意識》中形容此圖為“混淪雄厚,嵐氣溢幅,實屬壯觀”。歷經百年的山巒,每一座山巔都有自己獨特的樣貌;幾十處的茂林,每一棵樹木都別具特色,富有山石樹林的形式神態。黃公望作畫一般不采用濃郁的顏色,也不應用大幅的潑墨,罕有剛毅的線條。畫面中的圓松多采用線條勾勒,著墨也多用干枯的筆墨,呈現出一種明亮秀麗、溫潤平和的氣象,展現了黃公望變化多端的筆法技巧,寄托了作者對寄情林泉生活的神往。在此處畫家將山川、樹石作為自己遣興抒懷的客觀對象,不將描摹實際山水作為畫作的主要部分,映照出黃公望對現實的世俗生活恬淡、隱逸的態度,這也折射了元代山水畫家群體的審美傾向。
《九峰雪霽圖》也是黃公望淺絳山水畫的代表,是黃公望八十一歲高齡的作品。畫作描繪的是江南松江一帶的九座道教名山,是作者崇拜道教全真教的體現。畫中景秀時值正月初雪,寒意微上,畫意莊穆靜謐。其中中景、近景用干枯筆法勾勒出疊石的輪廓,山坡邊緣微微點染赭黃色彩,遠景的九座雪峰留白處理,用淺墨淡出靜謐的雪山,是黃公望雪景山水的珍品之作。
畫面山巒、斷崖、雪峰參差錯落,層層疊疊,純潔、幽凈,好似神仙居住的場所。畫面丘壑奇特,枯樹疏落相見,整個氣氛既嚴寒冷酷又清新颯爽。畫家吸取了荊浩、關仝和李成的傳統筆法,并兼從己法而成,用筆大氣,皴染簡練,淡墨烘染而出的群峰和濃厚的畫底色相互輝映,恰當地表現出寒冬季節雪山寒林的蕭索氣氛,富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為了表現雪景的質感,作者在描繪時很少用皴法,而是大篇幅地采用皴染。畫面中豐富層疊的墨筆,將山巒的起伏十分生動地表現出來,末尾的山頭上施加些許焦墨點,這樣強烈的黑白對比,加強了山頭白雪的質感。畫上自題:“至正九年春,為彥功作雪山,次春雪大作,凡兩三次直至畢工方止,亦奇事也。大癡道人,時年八十有一,書此以記歲月云。”“借地為雪,薄粉施于山頭”寒林蕭疏之感躍然紙上,表現出峰巒峻拔的氣勢以及雪中高嶺的嚴寒景象。
《丹崖玉樹圖》也是黃公望的晚年的作品。圖中山巒的布置層次繁多,峻峭的松木與雜木從密布在窠石坡岸的上方,山石和林木之中若隱若現地掩映著一座寺廟仙觀。山巒之下是郁郁蔥蔥的的林木,有一位老翁正拄著拐杖慢慢前行,溪水之上一座小橋橫臥,橋下的溪水清澈干凈,溪流深邃,遠遠望去就是一派幽遠渾融的景象。整幅畫中群山積翠,層巒疊嶂,頗有元代文人畫宏大的氣勢。近景處黃公望用長線條勾勒出長松的輪廓,其余的雜樹或圈或點,用筆溫潤柔和,沒有過于奇峭的筆法和強悍的氣勢。山體的構造也呈現圓渾平緩的輪廓,長短披麻皴兼施并用,淡墨先勾皴而出,后用濃墨點染青苔,層次變化多端。隨著畫面的景色逐漸向后移動,映入眼簾我們的是連綿不斷的丘壑山峰,遠樹含煙。整幅畫面的用色清新淡雅,風格渾厚蒼秀,體現了畫家寄情于景、寄樂于畫的藝術追求。
從構圖來看,《丹崖玉樹圖》相對復繁,但其實用筆極其簡約。畫面下方留有大部分空白的地方,山石基本不使用皴筆,更加彰顯出畫面的空靈飄逸。設色方面多用淺絳,淡冶秀雅。在筆法方面,黃公望變宋人的繁復縝密的風格為簡約松秀,從而大大地削弱了水墨濃郁的刻畫表現,改以勾皴為主,略加渲染便生動地表現出江南山巒質地松軟的特點。正如清代畫家惲壽平所說:"其皴點多而墨不費。"這種淺絳山水畫法不僅發展了董源、巨然的山水畫傳統,表現出江南清麗明潔的山色特點,也符合元人灑脫超逸的審美觀,為后世所崇尚和發揚。
《剡西訪戴圖》是云南省博物館的一件鎮館之寶,取材于一個歷史人物故事,描繪的是東晉時期著名的書法家王徽之訪問朋友戴逵的一件趣事。相傳一天晚上王徽之賦閑在家誦讀詩書。他推開窗,發現外面一片白雪茫茫。此情此景令他心中有所觸動,頓時想約上好友戴奎一起飲酒賞雪。于是他帶上清酒瓊漿,乘坐小舟,溯江而上,前往住在剡溪的戴逵家中。一路上小船在水中緩緩前行,沿途的剡溪山水美麗動人,月光折射地河面波光粼粼,白雪覆蓋在山巒和樹杈更顯現出別樣的氣韻。王徽之一邊飲酒一邊賞景,有如進入仙境。小船一路前行至戴奎住處,眼看就要見到友人了,然而王徽之卻要求船夫掉頭折返。船夫詢問其故,王徽之這樣說:“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原來王徽之趁著興致決定去拜訪好友,但是沿途的美景已經足以讓自己抒懷盡興,此時對于王徽之而言見不見戴逵已經無所謂了。更而言如果見到戴逵之后,兩人四目相對,興味索然,這才是真的辜負了這般雅興。王徽之乘興訪友的美景雅趣在黃公望筆下被描繪地惟妙惟肖,畫面之中山嶺高聳,山巖層疊,凍樹蕭瑟,端坐在扁舟中的王徽之雙手攏袖御寒,以酒后微醺的姿態沉醉在山河壯麗的美景當中。畫中雖然沒有高懸的明月,但被月光映照下人物的情感變化都展現得淋漓盡致。
圖的右上方有黃公望自題的字體:“至正九年正月王賢畫,二十五日題。大癡道人時年八十有”,在畫面的上方描繪的是萬壑綿延的崇山峻嶺,山的一旁村舍錯落有致,但村中卻空無一人。畫面下方是蜿蜒逶迤的剡溪。溪中畫有一葉扁舟,扁舟上一人正端坐著觀賞風景,船夫戴笠劃槳,船行的方向是要遠離村莊。整幅畫面給人感覺蕭索冷落,寒氣凌冽。畫中枯黃的樹杈以留白處理,表現出剡溪山水將融未融的雪景。山石堆積疊起,結構復繁,但用筆簡約,黃公望在石根處稍稍施加些許筆墨,讓畫面顯得空靈瀟灑。總體來看這幅畫上雖然著墨不多,但是畫面中層層疊疊的山峰,又使得畫面呈現出飽滿之感。盡管畫面中的船和遠處的村莊屋舍都采用了寫實的手法,但是空間與內容的處理卻顯得非常的豐富。這恰恰體現了黃公望繪畫技藝的高超過人。畫作運用接地為雪的藝術手法,將白雪與地面銜接地十分自然,以簡單幾筆的水墨勾勒出層層疊疊的遠山,并且以淡墨烘染的背景作為襯托,寥寥數筆便把大雪之后粉妝銀琢、群山環繞氣勢雄偉的景色展現地躍然紙上。
《剡溪訪戴圖》
黃公望的山水畫常常將中鋒與側峰,尖筆與禿筆,干濕甚至飛白相結合,筆法精湛多變,錯落有致,似柔而剛,松秀靈動,蒼茫中見秀勁,簡潔中渾厚,把北宋以來的文人畫發展到了詩書畫相結合的自由程度,對后世的山水文人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中國傳統美學之生命意識與“本真”訴求 李天道 《社會科學研究》
[2]元代寒林題材山水畫研究 賈超男 渤海大學碩士論文
[3]黃公望“高遠”式構圖法賞析 謝凌凌 《大眾科技》
[4]黃公望《天池石壁圖》——淺絳山水畫 http://www.360doc.co
(作者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