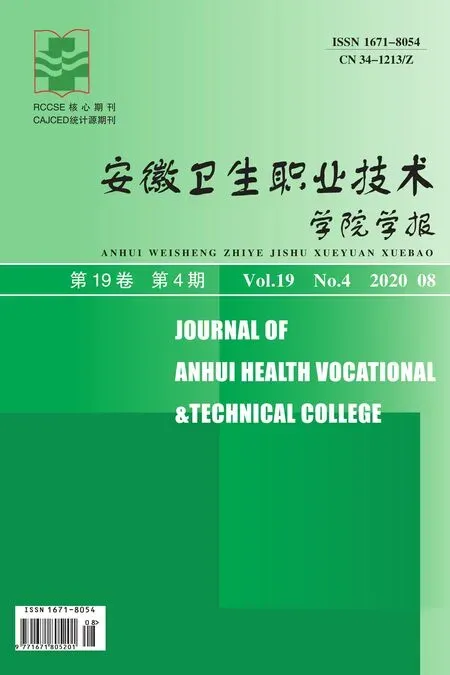全程個性化心理護理干預對工傷患者的康復影響
劉 丹 喻春梅 劉齊芳
意外工傷給工傷患者帶來沉重打擊,給其家庭、社會帶來很大影響,患者的心理情緒問題是康復預后的最大障礙。本研究對醫院收治的工傷患者予以常規康復治療和一般性的健康教育,并嘗試在此基礎上給予全程個性化心理護理,效果較好。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從2018年4月-6月本醫院收治的工傷患者中抽選90例,根據患者入院時間的不同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各45例;實驗組男性患者28例,女性患者17例,平均年齡(41.87±2.32)歲;對照組男性患者25例,女性患者20例,平均年齡(44.57±1.72)歲;在受傷部位上,實驗組中手足外傷13例,腦外傷17例,脊髓損傷11例,燒傷4例;對照組中手足外傷15例,腦外傷12例,脊髓損傷13例,燒傷5例;在文化程度上,實驗組大專以上學歷15例,高中19例,初中7例,小學以下4例;對照組大專以上學歷17例,高中15例,初中9例,小學以下4例。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及受傷部位等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兩組患者入院后均行康復評定,制定康復計劃,進行康復治療。
1.2.1 對照組 對患者進行常規的康復治療與一般性的健康知識教育。
1.2.2 實驗組 患者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實施為期2周的個性化心理護理干預:①科室成立心理護理干預小組,由專職心理醫生指導,護士長總負責,2名主管護師分別帶領5名護士,每名護士負責4例患者,包括制定個性化心理護理計劃及完善護理總結。②對每位新入院患者進行常規介紹,如醫生、護士、治療師以及病房環境等。建立醫患聯系卡,卡將各自的醫生、治療師、護士的聯系方式寫于卡片上及時和患者有效溝通。③每名護士對自己所負責的4例患者進行心理干預,每天30 min做到多聽患者及其家屬的傾述,讓患者把擔心的事說出來,比如住院期間單位能否發基本工資,還有營養費、生活費、家屬陪伴費等問題。小組成員必須耐心解釋回答患者所提問題。④堅持以患者為中心,病區里設有涂鴉墻、許愿樹及今日壽星牌等。⑤營造溫馨的病區環境,溯造一個家的感覺,設置一個小型廚房,方便患者及時補充營養,確保康復訓練正常進行。⑥針對患者不同的負性情緒開展心理護理干預,進行一對一的干預,通過發放自制的健康知識小冊子,盡量單獨進行心理疏導,實施親情護理,改善患者不良情緒。
1.3 評價指標
1.3.1 干預前及干預2周后采用HAMA和HAMD評定情緒改變情況 HAMA評估焦慮癥狀的嚴重程度,總分超29分為嚴重焦慮,超21分為明顯焦慮,超14分為焦慮,超7分為可能有焦慮,小于7分為無焦慮癥狀。HAMD評估抑郁癥狀的嚴重程度,總分超31分為嚴重抑郁,超20分為輕、中度抑郁,超8分為可能抑郁,小于8分為無抑郁癥[1]。
1.3.2 治療依從性 患者自住院至1個月隨訪時的遵醫行為,患者無1次不按醫囑行為發生,為治療依從性好,否則為差。
1.4 統計學方法 將數據錄入Excel,采用 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x ±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的HAMA和HAMD評分比較 干預前兩組患者的HAMA和HAMD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實驗組患者HAMA和HAMD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的HAMA和HAMD評分比較(±s,分)

表1 兩組患者的HAMA和HAMD評分比較(±s,分)
組別 n HAMA HAMD干預前 干預后 干預前 干預后對照組 45 18.97±1.2316.58±1.55 21.57±1.7213.79±1.52實驗組 45 19.07±1.1911.28±0.73 22.48±1.21 6.08±1.01 t 0.571 2.727 0.591 2.568 P 0.528 0.011 0.540 0.015
2.2 兩組患者的康復治療依從性比較 實驗組患者治療依從性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的康復治療依從性比較 例(%)
3 討 論
3.1 焦慮和抑郁是工傷患者最容易產生的負面情緒 造成工傷患者負面心理壓力的原因[2]有:①住院期間單位有無基本工資、營養費、生活費、家屬陪伴費等。②終身疾病擔心出院后生活困難。③農民工出院后可能面臨失業。④多數工傷病人是農民工,文化低,對工傷政策不夠了解。⑤多數較重的患者認為自己是工傷,想終身住在醫院療養。⑥角色的改變,原來是頂梁柱現在變成殘疾人。⑦批一個工傷很難,單位上的人不理睬,層層找人批。⑧有些工傷患者住院期間單位仍要求上班。
3.2 負面心理壓力影響工傷患者的性格 ①喪失感:患病使患者脫離了原來的角色,也同時失去了相應的一些權益。②羞愧感:患病使人的工作、生活能力下降,甚至不能生活自理,需人照顧,使得性格要強的患者認為自己無用而感到羞愧。③自卑感:有些嚴重工傷,如脊髓損傷致截癱患者,大小便不能自控,身上時常會有異味,受到社會偏見,人們往往近而遠之,這種患者往往有很深的自卑感[3]。
3.3 個性化心理護理干預可以提高工傷患者的康復效果 工傷患者這些負面心理壓力和性格直接影響患者康復效果,作為心理護理干預小組的成員,應對心理疏導的對象所產生的負面情緒給予全面且個性化的系統心理護理[4]。加強護患溝通技巧的學習,護理人員要主動、及時的與患者溝通,根據患者知識水平、理解能力、性格特征、心情處境以及不同時間、場合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有計劃性的選擇患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內容進行交流溝通。避免使用刺激對方情緒的語氣、詞調、語句,避免壓抑對方情緒,刻意改變對方觀點,避免過多使用對方不易聽懂的專業詞匯,避免強求對方立即接受醫護人員的建議和事實。在非語言性溝通時護士應目光平視、面帶微笑、儀表端莊大方,提高患者可信程度,使患者們以積極的心態配合治療,從而提高康復效果,盡最大能力讓患者回歸家庭,回歸社會,重返工作崗位。
綜上所述,對工傷患者實施全面個性化的心理護理干預,做好健康知識教育,教育患者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正確對待自身疾病,可以促進患者充分利用殘存功能去代償致殘部分,盡最大努力去獨立完成各項生活活動,以達到早日回歸家庭、回歸社會、重返工作崗位的目的。